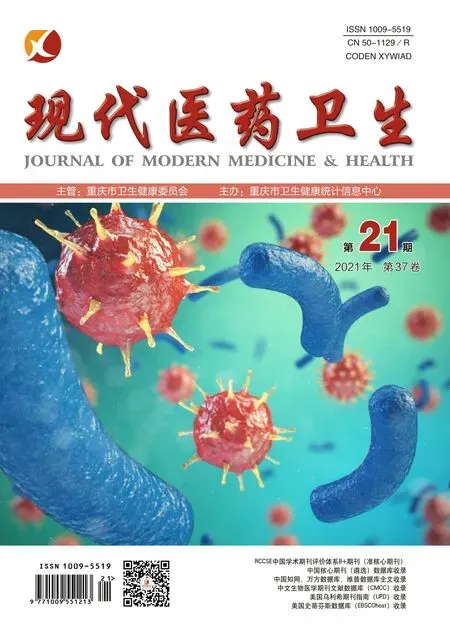湖南省郴州市1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家庭聚集性疫情流行病學調查*
劉 勛,朱韓武,劉 衛,鄭 文,譚 徽
(郴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湖南 郴州 423000)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負擔,當前國內仍有因境外輸入導致的多點散發或局部聚集性疫情,有必要及時總結防控經驗,以便科學、精準地應對新發疫情[1-2]。2020年2月9日,郴州市某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接到市某COVID-19定點醫院報告,收治該縣1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且該醫院檢測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核酸呈陽性。定點醫院于2020年2月10、11日分別采集該病例咽拭子送至市CDC檢測,結果均為陰性。2020年2月11日,縣CDC對該疑似病例22例密切接觸親屬咽拭子采樣送檢,發現該病例2例共同居住的親屬咽拭子SARS-CoV-2核酸結果為陽性。市、縣CDC立即聯合縣公安局等部門開展調查處置,及時查明了傳染來源,有效控制了疫情。現將該起疫情的調查處置情況總結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收集2020年2月9-15日湖南郴州市某縣1起COVID-19家庭聚集性疫情中的所有確診病例、密切接觸者及病例的居住環境和家庭情況。
1.2方法
1.2.1調查方式 市、縣CDC根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四版)》[3]的要求,對病例的基本情況、發病診療經過、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測、病例家庭及周邊環境情況、出現癥狀前28 d暴露史和接觸人群進行詳細調查。會同縣公安局、街道社區等部門對病例、接觸人員的活動史、暴露史進行調查、梳理和比對。
1.2.2確診標準 病例確診:按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4],疑似病例中咽拭子SARS-CoV-2核酸檢測結果陽性者為確診病例。臨床診斷分型:臨床癥狀輕微,影像學未見肺炎表現者為輕型COVID-19病例;具有發熱、呼吸道等癥狀,影像學可見肺炎表現者為普通型COVID-19病例[4]。
1.2.3核酸檢測 根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實驗室檢測技術指南(第四版)》[3]的要求,對呼吸道標本采用實時定量熒光逆轉錄聚合酶鏈反應(RT-PCR)檢測SARS-CoV-2核酸的2個靶標(ORF1ab和N),試劑盒購于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號:2020003)。
1.2.4聚集性疫情判定 14 d內在小范圍(如1個家庭、1個工地、1個單位等)發現2例及以上的確診病例或無癥狀感染者,且存在因密切接觸導致人際傳播的可能性,或因共同暴露而感染的可能性[3]。
2 結 果
2.1病例基本情況 本起疫情共發現3例確診病例,病例A為指示病例,2月5日出現發熱(38 ℃)、乏力,遂到縣人民醫院就診,檢查未發現明顯異常,按普通感冒處理。2月7日再次出現發熱,2月8日前往市某COVID-19定點醫院就診,入院后胸部計算機斷層掃描(CT)顯示雙肺邊緣呈磨玻璃樣病變進展,醫院對其進行4次咽拭子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2月14日第5次深痰液核酸檢測SARS-CoV-2為陽性后于當日確診。2月11日縣CDC對A的密切接觸者篩查時,發現與其共同生活居住的家庭成員病例B、C咽拭子核酸檢測陽性,2人發病時因癥狀較輕均未就診。3例確診病例臨床診療信息見表1。

表1 郴州市某縣COVID-19聚集性疫情病例臨床診療信息表
2.2流行病學調查
2.2.1病例暴露史調查 病例A在廣東省某市從事美容工作,2020年1月1日從廣東回到郴州某縣,發病前一直在縣城及周邊活動。病例B長期在郴州某縣居住生活,發病前近半年未離開縣城。通過縣公安局、街道社區等部門對該縣所有確診病例的活動史進行梳理和比對,從監控視頻中發現2020年1月23日B與該縣另一家庭的確診病例L同時段出現在S市場買菜,進一步調查和比對2人在S市場的行走路線,發現B在市場自產自銷區與L有近距離接觸,且均未戴口罩。經B和L在市某定點醫院隔離病區當面辨認,2人互不認識但表示曾見過面,提示2人有過接觸。病例C在廣東某市汽車部件公司工作,2020年1月12日從廣東回到郴州某縣家中,期間在縣城家中較少外出。
2.2.2病例居住環境及家庭情況 病例A同丈夫(E)、兒子(F)、婆婆(B)、弟弟(C)共同居住在某小區4室1廳的套房,該居室為樓梯房,層高為3米;小區周邊無農貿市場,環境尚可。一家5人居家期間每天共同就餐至少1次,在家均未戴口罩;房間窗戶常處于關閉,室內通風不良。E和F均無呼吸道癥狀,近期未到過重點疫區,也未接觸過來自疫區的發熱或有呼吸道癥狀的患者,2人經咽拭子核酸檢測SARS-CoV-2結果均為陰性。
2.2.3病例接觸人群調查 對病例A、B、C接觸的35人進行調查走訪,除B接觸的L為該縣COVID-19確診病例外,其他34人均無呼吸道癥狀,也無重點疫區旅居史和重點疫區人員接觸史,34人咽拭子核酸檢測SARS-CoV-2結果均為陰性。
2.2.4病例傳播鏈分析 2020年1月23日病例B接觸確診病例L時,L已出現發熱、干咳等癥狀,正處于COVID-19排毒時期。病例B無其他COVID-19暴露史,且在接觸L后8 d出現癥狀,與COVID-19發病潛伏期相符[4]。A和C無其他COVID-19流行病學史,與B共同居住生活期間因密切接觸感染SARS-CoV-2可能性大。綜上推斷,本起疫情的傳播鏈為L將病毒傳播給B,B又傳播給A和C。
2.3疫情處置 疫情發生后,縣政府立即組織衛生健康、公安、社區等相關部門聯合開展傳染源的調查、部署社區防控,并對確診病例居住地、暴露場所及其周邊環境進行消毒。2020年2月14日該縣對所有小區實施封閉式管理,居民憑“出入證”限制出入,嚴格落實佩戴口罩防護措施。2020年2月15日采集病例小區周邊居民咽拭子標本161份,檢測SARS-CoV-2結果均為陰性,未發現社區傳播的證據。截至2020年3月14日,經過2個最長潛伏期,該縣未發現新發病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3 討 論
COVID-19聚集性疫情是各地疫情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北京、上海及江蘇等地區的聚集性疫情涉及病例數占全部確診病例的50%~80%[5]。數據顯示,聚集性疫情83%發生在家庭聚集,而聚集性疫情的家庭續發率達49.56%,高于其他聚集性疫情的續發率(35.00%)[6],提示防止家庭聚集性疫情的發生是控制疫情蔓延和流行的關鍵。本起疫情中的傳染源病例L與病例B近距離接觸而感染,病例B將病毒帶入家中,致使病例A和C感染。分析其原因為,COVID-19的主要傳播途徑是經呼吸道飛沫和密切接觸傳播,家庭內如有攜帶病毒的病例,家庭成員間因共同居住生活而密切接觸,交叉傳播概率大大提高,極易引發家庭聚集性疫情的發生。由此可見,疑似傳染病患者早期居家隔離可能導致家庭聚集性疫情的風險,新發不明原因傳染病時建議盡量以集中隔離代替居家隔離,以防可疑病原被帶入家庭,進而避免家庭聚集性疫情發生和傳播。
本起疫情病例無明確的COVID-19流行病學史,該市首次通過現場流行病學調查結合公安部門的監控系統和手機軌跡,對病例的活動史進行對比分析,發現了病例L將病毒傳播給病例B的證據,排除了該家庭病例從其他途徑感染的可能,及時查明了疫情的感染來源。提示應積極采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提高傳染病流行病學和溯源調查能力,并以此契機促進流行病學學科智能化、信息化發展。疫情發生后,在縣政府主導下的采取多部門聯防聯控措施,如全縣小區封閉式管理、限制出入和人員流動及嚴格佩戴口罩,對病例所在社區進行拉網式排查,使得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未發現社區的廣泛傳播。因此,建議政府主導制定傳染病聯防聯控長效制度,成立社區防控部門,引導全社會參與,以實現全覆蓋精準防控。
需要注意的是,COVID-19具有傳染源隱蔽、傳染性強等特點[7],病例A就診時臨床高度懷疑為COVID-19患者,胸部CT顯示雙肺邊緣呈磨玻璃樣病變進展,但前4次咽拭子核酸檢測陰性,經第5次深痰液核酸檢測才顯示結果為陽性。李泉等[8]認為,肺泡灌洗液中最易檢出病毒核酸,其次是深咳痰,再是鼻咽部、口咽部。對初步咽拭子核酸檢測陰性而臨床又高度懷疑為COVID-19的病例,應采集檢出率更高的標本進一步檢測診斷。此外,病毒核酸檢測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還存在假陰性結果的可能[9],發病早期需結合胸部CT的輔助診斷,避免發生漏診及誤診[10]。本起聚集性疫情中,縣CDC在病例A未確診時仍對其密切接觸人員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和核酸檢測,本起疫情才得以較早被發現和處置,提示排查密切接觸者工作不僅是發現病例的有效手段,更是發現傳染源的有效途徑,對早期發現感染病例具有重要意義[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