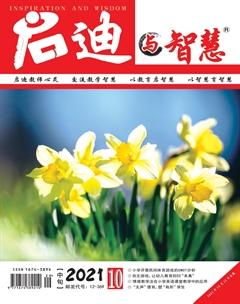我們還能從《論語》中收獲什么?
郭尚蕾
“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是宋朝宰相趙普說過的話。
之前總以為《論語》中的觀點看法很多都已陳舊,對現今的我們貌似沒有多大的用處,可當我重新拿起它、走近它時,才發覺那歷經了2000多年的智慧,至今還在熠熠生輝。
《學而》篇第一章中的第一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句話我們都很熟悉,因為七年級時我們學過一篇課文《<論語>十二章》。很多時候,我們對于自己熟悉的東西,不會去深思、去一探究竟,只是覺得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學習了之后要時常去復習、使用,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每個人都會覺得這是《論語》里最普通的一句話了。孔子在這里說了“習”又說了“說”,為什么呢?那“習”在這里又有什么寓意呢?我們都知道,古人學習的是“五經六藝”,“五經”是古人的知識,“六藝”是古人的技能,他們的學習內容本身就很廣泛,知識與技能相結合,所以“習”在這里更多偏向實踐的意思,“時習”就是選取合適的時間去實踐、去刻意練習,這樣才算“時習之”。
我們很多人在學習的時候,其實更多的是一種不悅的狀態,所以孔子才會說“亦”這個字,“不亦”的意思是“不也……嗎?”言外之意就是很多人還是覺得學習不是一件“悅”的事。孔子所說的悅接近一種狀態叫作“心流”。“心流”就是當你全身心地投入某件事時,達到了忘我的程度,并由此獲得內心的秩序與安寧,有一種極大的滿足感會悄悄地潛入你的心,使你快樂,使你幸福。這種感覺帶給你的不僅僅只有幸福,還會讓你有更高的成就感,讓你對生活有掌控感,讓你知行合一等。所以孔子在這里的意思是當你全神貫注地去做某件事時,就會獲得幸福。朱熹曾說過:“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當老師之前,我對于學過的知識遺忘得非常快,那是因為沒有地方去實踐,在經過了時間的歷練之后,我的感覺發生了變化,一些內容、一些方法使用過后便刻在了腦海中,這是因為這些東西是我真正實踐了的。如果能深刻理解孔子的這句話,我們就會更加明確教與學的關系,更加偏向于讓學生自己去體驗、去探索了,而新時代的教育正在逐步回歸教育的本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習之樂,在于練習、在于實踐,在于面對困難、解決困難中獲得的心靈體驗。
著名的“新教育實驗”發起人朱永新教授的新作《未來學校》,提出了對未來教育的思考和設想。教育該遵循什么樣的規律,孔子其實早就告訴我們了。孔子為師時,只要你拿著十條干肉來,無論你是什么身份,貴族也可,貧民也可,盜賊也無不可。只要你有愿意學習的心,你便可做孔夫子的學生。當時本是貴族才有資格接受教育的,孔子卻做到了有教無類,不分階級,無論年齡。
孔子曾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到學生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時候就不去開導他,不到學生想說卻說不出來的時候就不去啟發他。教育,不是將所有知識全塞給學生,而是要循循善誘、因時而動,就是我們常說的因材施教。
孔子很會觀察學生,有時候同樣的問題,不同的學生詢問,會給予不同的回答。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子路和冉有都問了同樣的問題,聽到一件合乎意義的事就應當付諸實施嗎?孔子對子路說,父親和兄長還活著,怎么可以不去請教他們就去做呢?對冉有又說道,聽到之后就應該立刻去做。因為冉有做事經常畏縮不前,就應鼓勵他積極行動,而子路性格魯莽,所以就要讓他三思而行。
因材施教,貌似簡單,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班主任深有此感。要了解一個孩子是非常不易的,他的成長環境、性格特征、家庭狀況等都要去綜合考慮。大班額之下想要深入了解每一個學生,更是難之又難。在課堂中,我們面對著坐在同一個教室中的孩子,雖是同齡,但每個人的接受能力、興趣目標都大不相同,我們所傳授的內容他們又能接受多少呢?
其實對于一個教室里的學生,我們大多時候只能滿足三分之一的人的需求,其他三分之一會覺得這些內容他們很容易就能掌握,他們還需要更深層次的內容,而另外三分之一可能會覺得內容晦澀難懂,超乎了他們接受范疇。人人都不一樣,我們卻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從夸美紐斯提出了班級授課制這個概念后,我們一直在沿用這種教學方式。
工業革命開始至今200多年了,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只有教育還在遵循之前的模式,這是不協調的,孩子不是機器,這種工業時代統一而為之的方法本身就是有待改進的。
《未來學校》這本書中提到了一個概念,叫“學習中心”。未來的教育會在學習中心進行,學習中心擁有更多優質課程,能利用人工智能讓學習變得更符合每個人的需求。這本書為我們刻畫了一幅未來教育的藍圖,在這個藍圖中,我們的教育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從時間、空間這兩個維度打破了學校的概念,每個人的學習方式更自由、更全面,人也會變得更幸福。這幅藍圖如何才能變為現實呢?這還是一條漫漫長路,需要我們每個人的努力。
讓我們這些教育人攜起手來,共繪美好教育未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