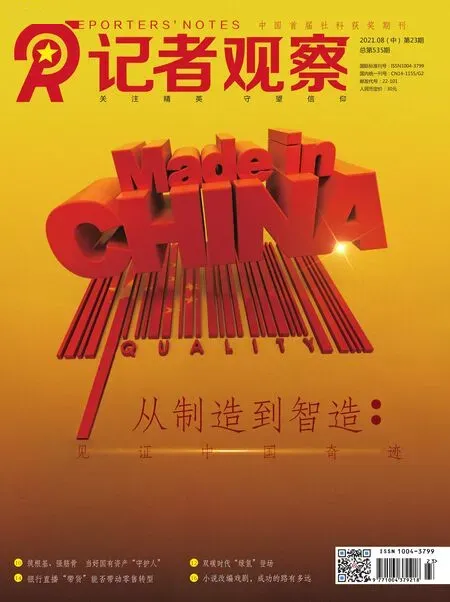“記憶之場”概念對電影再現歷史的思考
——以貴陽三線工廠及其社群文化為例
文 宋青和
本文首先將要闡明的是法國史學巨擘皮埃爾·諾拉所提出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學概念——“記憶之場”。其次,本文將貴陽三線工廠及其社群文化作為研究論述的具體對象,結合貴陽三線建設的歷史背景及特點,討論“記憶之場”概念如何能夠為那些以呈現三線記憶為目標的電影創作帶來新的思路。本文以期通過對再現三線記憶的研究,增加民族、地區對其歷史的認同感與歸屬感,為貴陽三線歷史及其同類型歷史文化遺產的電影創作提供新的解決方案。
“記憶之場”是由法國歷史學家、法蘭西學院院士皮埃爾·諾拉在1984到1992年間所提出的一個歷史與記憶的概念。借由此概念,皮埃爾·諾拉推動了一項龐大的歷史學研究:通過研究承載記憶的場所,探尋殘存的集體記憶,從而尋得國家、民族、群體的認同感與歸屬感。“記憶之場”概念及其研究一經問世,不僅在全世界的歷史學界引起了廣泛反響,并且在文化藝術領域,尤其對再現歷史電影類型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我們應該厘清“記憶之場”概念的含義,并且闡述為何這個概念對電影再現歷史具有啟發性和原創性的意義。
“記憶之場”
“場”,其有地點、場所及現場等意。應當注意的是,如同中文里場地或氣場兩個詞中場字的不同含義,在此,場字既可以指有形的空間地點,也可以指無形的情境。而“記憶之場”指的是那些承載了某個集體歷史記憶的事物,借由這些事物,我們可以探尋該集體的語言文化、生活方式、工藝實踐及情感表達。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可以傳達歷史記憶事物既可以是具體和有形的,例如歷史的親歷者、博物館、檔案館或紀念碑;也可以是無形的,例如節日、方言或傳統。就本文所論述的對象舉例而言,貴陽某座三線工廠的場址、流水線、職工宿舍可以作為有形的喚起三線歷史記憶的事物。同樣,某位三線職工、廠話(三線社群所形成的特殊方言)或者是“三線精神”,也可以作為無形的“記憶之場”。正如皮埃爾·諾拉寫道:從最物質、最具體的物體,再到最抽象的智力構建都能夠成為‘記憶之場’。
“記憶之場”概念的原創性,不僅僅在于其關注了考古學所不曾研究的集體記憶,并且在于讓我們可以從有形和無形、具象和抽象等截然不同的角度去呈現歷史記憶,這無疑極大地拓寬了我們恢復三線記憶的能力。
在皮埃爾·諾拉早年的著述中,我們不僅發現了其思想的連續性,而且也洞見了我們想要恢復三線記憶的原因及重要意義。早在1978年,皮埃爾·諾拉在百科全書《新歷史》中對“集體記憶”這一詞條的撰寫中就指出,“歷史是在集體記憶的壓力下寫成的,它通過賦予一段未被經歷的過去以價值,從而對曾經的逝去和未來的焦慮進行補償。”在此,結合我們的論述對象,我們對諾拉的這句論述可以理解為:對三線記憶的追溯是三線建設的見證者與傳承人所自覺要求的歷史書寫,通過賦予這段后人沒有經歷過的事件以價值,從而消除我們對這段記憶缺失而引發的焦慮,從而尋得國家、民族、地區、群體間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有形的歷史記憶
“記憶之場”的概念自問世后,不僅給予了許多以再現歷史為目標的電影創作以新的思路,而且也影響著我們面對歷史的態度,因為拍攝電影的方式同樣也構成了電影的意義。面對一個時間上延續了三個國家五年計劃;地理上,涵蓋了全國二十多個省、市一百多個陸續遷入貴州的企業。我們是應該用虛構、戲說的方式再現這段歷史,還是應該用鏡頭在現實中去發現、紀念歷史?這應該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問題。
然而,我們應該通過怎樣的“記憶之場”去呈現貴陽三線的歷史?在眾多的“記憶之場”里,對于諾拉而言,能呈現歷史記憶的,“首先是歷史殘存的痕跡,因為在殘存的痕跡之中蘊含著紀念意識”。諾拉所說的殘存的痕跡,對于貴陽三線歷史而言,可以是那些破損的廠房和流水線,也可以是如貴陽新添光學儀器廠中那些不再生產甚至無法識別功能的光學儀器,或是從上海遷入貴陽的三線人攜帶的具有上海風格的生活用品。總之,殘存的痕跡具有這樣的特點,它們是具體有形的事物,其次,它們都有著不完整、不經改造的特點。此外,這些痕跡之所以能夠喚起歷史記憶,不僅僅是因為它們是歷史的產物,而且其中蘊含著觀者自發紀念那段歷史的意識。因為,在日新月異的城市化建設中,像是三線建設這樣的歷史留存,自然地攜帶著那個時代謎樣的魅力,用諾拉的話說就是,盡管曾經三線歷史遺忘了這些痕跡,但這些痕跡卻召喚著那段歷史。

無形的歷史記憶
從三線遺址中重獲三線建設的記憶固然是一個有效的方式,但是面對那些遭到嚴重損壞、重新改造,甚至已然消失的遺跡遺址,又如何用視聽的方式對其進行 重現呢?而且這樣的情況對于貴陽的三線工廠及社群文化而言不在少數,比如被改造為藝術與餐飲園區的貴陽晶體管廠,被改造成城市生活空間的貴陽軸承廠等。
當歷史的記憶沒有任何具體之物可以依存時,因此我們應該將鏡頭轉向那些無形的“記憶之場”。如段娟在其論文《近20年來三線建設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述評》中,總結了兩個十年中三線問題的主要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決策的評價、影響效應、三線企業的調整改造、與西部大開發的關系、人物、三線精。其中,以三線人物與三線精神為主體的調查研究就屬于典型的對無形的“記憶之場”的探尋。這就是為什么在近年來的研究中加入了社會生活、微觀個案研究、口述歷史等,基于某個人而對三線建設展開研究角度和方法。同樣,如果用電影對三線歷史的經歷者進行采訪的話,對于諾拉而言,所呈現的人物和話語不僅是三線歷史的告知者與代言人,而且人物就是三線建設的“記憶之場”,換句話說,三線人物就是他們所講述歷史本身。
此外,有必要加以說明的是對于人物采訪的問題設計,不僅僅可以圍繞三線建設的宏觀層面展開,也可以對微觀細節層面進行發掘。首先,這符合電影敘事的特點,電影是細節的藝術,是一連串具體、典型的事件組成的故事。例如,在對貴州新添光學儀器廠的上海援黔員工的采訪里,其中有一段采訪者用獨特的廠話詳細講述了她因為上海與貴陽氣候、飲食、等不同所導致的疾病。根據諾拉的觀點,作為“記憶之場”的歷史人物的敘述與家譜的作用不同,家譜的有用性在于表明家庭的歷史譜系。而作為記憶之場的人物卻是集體的歷史,通過三線人物對于生活工作細節的描述,我們不僅可以生動地感受到那段歷史與群體,并且可以由此了解到三線工廠及其社群的具體面貌。
皮埃爾·諾拉在八十年代推動的關于“記憶之場”的研究,為歷史學以及其他的人文科學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這樣的影響同樣也深深地改變了再現歷史類電影的創作。“記憶之場”理論的原創性在于對歷史的物質和非物質痕跡進行整體性的思考。借由對“記憶之場”的探尋,我們不僅擴大了呈現歷史的能力,而且還可以喚起國家、民族、群體間的歸屬感與認同感。“記憶之場”的概念以及重要性雖然在歐美國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與認知,但是對于中國的學界而言仍然缺乏對該概念的充分認識。尤其是該概念中對于還原歷史的非物質視角,能夠廣泛地啟發對于再現中國歷史的影像創作。本文淺述了該理論的含義,并以貴陽三線工廠及其社群文化為例,論證了該理論對呈現三線歷史記憶的有用性,“記憶之場”理論從非物質的研究角度解決相關問題,并且能夠起到讓國家、民族、地區對這段歷史產生歸屬感與認同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