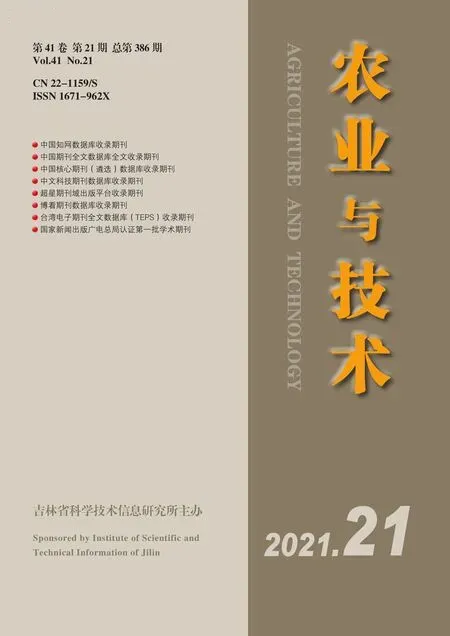鄉村振興背景下我國農業生產效率分析
張笑 朱薇姍
(河北經貿大學,河北 石家莊 050061)
民以食為天,各國學者十分重視對農業生產效率的研究。路國勝等[1]通過采用DEA模型,比較各地區的效率差異,研究其空間演化規律。但由于農業生產效率受外界因素的影響,因此需要準確反映農業生產效率,保證數據真實可靠。萬永坤等[2]采用結合DEA-Malmquist指數的方法,對甘肅省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深度分析。還有部分學者既沒有采用截面數據,也沒有使用連續的面板數據,而是抽取個別年份進行分析,如王蕾等[3]選擇了2009年、2013年、2016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分析農業生產效率方面的時空差異。
本文通過建立三階段DEA模型,消除外部環境和偶發因素對效率產生的影響,真實反映出我國在農業生產方面的效率,為中國農業未來的生產與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1 研究方法與數據說明
1.1 三階段DEA模型
三階段DEA模型是在原DEA模型的基礎上,剔除了外界環境和隨機噪聲對效率評價產生的影響,采用三階段DEA模型可以對投入產出指標進行調整,利用調整后的變量得到更真實的效率。主要包括以下3個階段。
1.1.1 第1階段
運用傳統DEA模型對原始數據進行處理,分析最初的效率。選擇對應基礎投入導向下規模可變的BCC模型,用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的乘積計算出技術效率。
1.1.2 第2階段
利用隨機前沿分析(SFA)將第1階段松弛變量分解為包含外界環境影響、管理無效率和隨機誤差等3個因素影響在內的函數。借鑒Jondrow等提出的JLMS技術[4],以處于隨機前沿的DMU(Decision Making Unit)的第1階段指標的投入為參考,對其它DMU進行調整,保證DMU都在相同的外界環境中。即可從隨機前沿分析中剔除環境因素影響和隨機項,即每一個決策單元都有一樣的初始條件,增加數據準確性。
1.1.3 第3階段
對調整后的數據進行DEA效率分析。運用第2階段調整后的投入變量和初始的產出數據再次采用第1階段的模型對各DMU的效率進行測算,從而計算出不包含外界的環境影響與隨機因素的影響在內的較為準確的農業生產效率。
1.2 變量選取
根據已有研究的描述與選取原則相結合,選用指標見表1。

表1 指標選取
2 結果與分析
2.1 第1階段DEA分析
將我國2019年農業生產的原始數據通過DEAP 2.1軟件進行處理,從而可以對我國農業生產效率水平和規模狀態進行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無視外部環境變量和偶發因素,2019年我國綜合技術效率的平均值為0.691,純技術效率全國總體平均值為0.763,31個省市總體農業生產的規模效率平均值為0.903。北京、浙江、福建、山東、海南、貴州、青海等7個省市3項效率值都為1,處于技術效率的前沿。除此之外,有5個省市純技術效率值都為1,但其它2項效率值有一定的進步空間,分別為天津、上海、廣東、四川、西藏。其它省市的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
由于第1階段DEA分析結果中包含外部環境的影響和偶然因素的干擾,因此無法反映我國不同省市的農業生產的實際效率水平,需要進一步調整和計算,去除外界環境與偶然因素對效率的影響。
2.2 第2階段SFA回歸結果
通過Frontier 4.1軟件進行隨機前沿分析(SFA),需要準確了解生產效率被環境變量干擾的程度,才能剔除環境變量與隨機因素的影響,因此將4個環境變量用作解釋變量,把第一步獲得的DMU元素的輸入松弛變量用作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大部分統計數據在1%的檢驗水平下是顯著的,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并且表明外界環境變化影響農業生產。
2.2.1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在5個投入松弛變量中,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和有效灌溉面積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化肥施用折純量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由以上結果可知,當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時,除化肥施用折純量以外的投入會增加,會產生農業生產效率降低等不利于農業發展的影響,反映出目前中國農業高投資低回報模式。
2.2.2 農林水預算支出
該變量增加對投入的松弛變量的相關系數均為正,但只有在化肥施用折純量通過了5%顯著性檢驗。這一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農林水支出結構的不合理,資金管理效率低下等現象。
2.2.3 農作物受災面積
農作物受災面積對5種投入松弛變量的相關系數均為正,且均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表明自然災害將產生使農作物產量降低,投入要素的資源浪費等一系列高投入低回報的負面影響,符合理論預期。
2.2.4 第二三產業總產值
這一變量對5個投入松弛變量的相關系數均為負值,且除農林牧漁業從業人數外均通過顯著水平為0.01的顯著性檢驗,這體現了第二三產業對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產生了正向效果,該變量是有利因素,能減少投入要素的浪費,與第二三產業能帶動第一產業發展的設想相符。
由于各環境變量對我國各省市的農業生產效率影響顯著,且不同省市之間的政府政策、農業受重視程度、受自然災害的影響程度等環境因素不同,從而表現出不同的農業生產效率。因此,需要調整原始生產要素投入變量,使所有地區均剔除外在因素影響,反映出真實的農業生產效率水平。
2.3 第3階段DEA實證結果
將第2階段SFA模型的各要素投入量與原始產出進行調整后,再次代入BBC模型中進行測算,得到相對真實的效率值。調整投入后,2019年我國各省市的農業生產綜合技術效率平均值上升為0.719,純技術效率均值上升為0.921,規模效率均值下降為0.781。各省市農業規模狀態也由規模報酬遞減為主調整為以規模報酬遞增為主。由以上論述可知,我國各省市區平均農業生產效率水平還有進一步上升的空間。
將第3階段的結果與第1階段相結合進行分析可知,北京、福建、山東、貴州的技術效率仍處于全國前沿,表明這4個省市是否考慮外部環境與隨機因素農業生產效率都比較好;第3階段中廣東、云南、四川3個省提升至農業生產效率的前沿面,表明這3個省份在處于同一外部環境條件下的農業生產是十分高效的;而浙江、海南、青海由于規模效率的減少退出技術效率前沿,說明第1階段的高效率沒有真實反映實際的技術管理水平。
以效率值0.9為分界點,根據純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的大小對我國各省市區農業生產效率進行劃分,可分為以下4種類型:“雙高型”地區,即農業生產規模相對合理,技術管理水平較高,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均在0.9以上的省市;“高低型”地區,特別是西藏和青海,其規模效率不及0.3,提高農業效率的方向是提高可擴展性、擴大農業生產和形成中央資源中心;“低高型”地區,這些省份有足夠的農業生產規模,在今后的發展中應改進技術管理;“雙低型”地區,此類省份的農業生產規模需要調整,同時在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提高技術效率。根據以上論述,將我國各省市區農業生產效率劃分,如表2所示。

表2 2019年我國31省市區農業生產效率類型劃分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本文運用三階段DEA模型,采取2019年我國農業生產的數據,對我國農業生產效率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通過第2階段回歸分析,發現外部環境和隨機因素顯著影響著農業生產效率。
第2階段調整前后,各省市農業生產效率產生了明顯的變化,農業生產綜合技術效率平均值由0.691上升為0.719,純技術效率均值由0.763上升為0.921,規模效率均值由0.903下降為0.781。此現象進一步說明外部環境與隨機因素對農業生產效率存在著顯著影響。
根據純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的大小對我國各省市區農業生產效率進行劃分,可分為“雙高型”地區、“高低型”地區、“低高型”地區及“雙低型”地區。從而可以根據各省市區所處類型,采取相應措施以提高我國農業生產效率。
3.2 建議
根據上述結論,不難發現外部環境與隨機因素對農業生產效率存在顯著影響,但隨機因素不可避免,所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方法就是對環境因素加以控制,因此提出以下建議。
不斷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強農業機械化,同時需要農民對經營模式進行學習與提升,以增加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且需要加大農民的投資知識,對收入進行合理分配,減少投入資源的浪費,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改善農業援助支出組合,盡量減少農村公共利益系統效率損失,同時改善農村地區公共產品的外部供求條件,通過農業援助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農業發展十分依賴于自然條件,因此對自然災害進行防治,將其扼殺在萌芽狀態迫在眉睫。因此,需提高農民防災意識,大力修建田間排水溝,改善土壤結構,預防自然災害的發生。
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合理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對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有著不可否認的影響。通過第二產業與第一產業結合,將農業生產的原料進行加工,促進雙方發展。
由于我國各省市的農業生產效率特征并不一致,各地區應結合當地農業的不足之處,因地制宜進行變革,而不是盲目地按照特定模式來發展農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