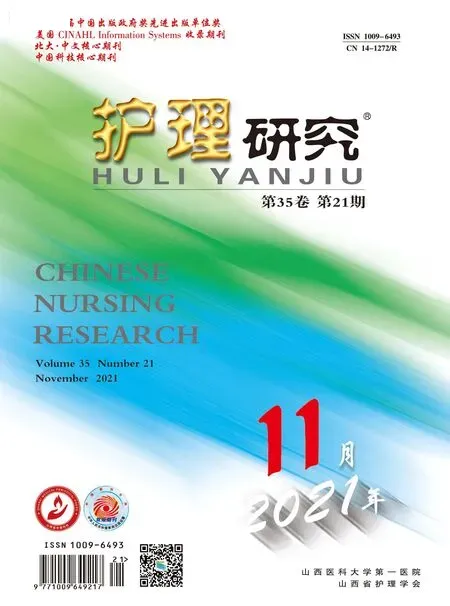外固定感染風險預測模型預測能力的前瞻性研究
余文娟,楊靜華,劉樹霞,郭凡依,彭小偉,陳雅琴,翟惠敏,馬 玥*
1.南方醫科大學,廣東 510440;2.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
外固定是利用外固定架對骨折端和(或)關節進行固定,防止繼續損傷或者是骨折端移位的一種有效方法,目前已在創傷骨科中得到廣泛應用。不管哪種支架,其螺釘都會穿過皮膚、軟組織,導致骨與外界之間形成通道,為細菌侵入、發生針道感染提供機會。針道感染癥狀有疼痛、發炎或滲液等[1],其發病率為3%~80%[2]。如果能夠在病人術后早期預測其發生感染的風險,就能及時采取護理措施預防感染的發生,達到良好的康復效果。基于以上因素,依據前期初步建立的外固定感染護理風險因素預測模型,本研究前瞻性驗證該模型的預測能力并矯正模型,為篩選術后外固定感染的高危病人提供參考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根據樣本量計算方法,本研究共有21個變量,根據統計學多變量分析的要求樣本量應為105~210例[3]。采用便利抽樣法,納入2019年6月—12月廣州市某三級甲等醫院行骨外固定手術的300例病人設為建模組。納入標準:符合自愿加入原則;采用外固定架搬運的病人;意識清醒。每月進行電話隨訪并追蹤半年,將完成半年隨訪的病人設為驗證組。
1.2 方法
1.2.1 感染程度判斷標準 本研究由1名副主任醫師與1名主管護師采用Sims等[4]的針道感染嚴重程度分級方法判定,將感染分為6級:1級為針道口皮膚微紅,少量滲出;2級為針道口皮膚發紅,滲血滲液,疼痛,針道口周圍軟組織敏感;3級為在1級和2級癥狀的基礎上,口服抗生素無效;4級為嚴重軟組織感染涉及多個針道,有時伴針孔松動;5級為X線顯示可見死骨;6級為慢性骨髓炎。其中1~3級為輕度感染,4~6級為重度感染。
1.2.2 驗證模型 前期經過Logistics回歸,為方便護理工作中使用,將判斷工具賦值簡化見表1[4]。風險預測模型的驗證可以采用外部驗證,通過研究來自同一家醫院不同時間(時間驗證)或來自不同醫院(空間驗證)的病人來評估模型的外推性[5],本研究收集了來自同一家醫院不同時期的病人資料來進行外部驗證。

表1 外固定感染風險因素評分標準
1.2.3 風險預測模型的評價依據 驗證模型的預測效能通常包括模型的一致性和區分度兩個方面。一致性通過H osmer-L emeshow(H-L)χ2檢 驗和O/E(observed outcome/expected outcome)來評價,比較實際患病率和模型預測患病率的一致程度。若Hosmer-Lemeshowχ2檢驗結果P>0.05,表示模型具有滿意的一致性,P<0.05則提示模型一致性較差。O/E值接近1提示模型具有滿意的一致性,O/E>1代表模型低估了感染的發生率,O/E<1代表模型高估了感染的發生率。區分度通常用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AUC)評價,評估模型準確判斷感染發生的能力,AUC<0.7說明模型區分能力較差,>0.7說明模型區分能力較好。最后采用約登指數尋找模型的最佳臨界點,其最大值對應的風險概率值為最佳臨界點。
1.2.4 質量控制 為了保證資料收集的質量,收集資料階段嚴格按照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篩選病人。本研究在實施調查的過程中遵循保密、不傷害原則。
1.2.5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采用SPSS 20.0統計分析軟件,服從正態分布的定量資料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不符合的采用秩和檢驗,定性資料采用χ2檢驗。以單因素分析結果中P<0.1的變量為自變量,進入Logistic回歸分析,分析采用前進(LR)法,進入和排除標準分別為0.10和0.05。最后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OC)對模型的一致性和區分度進行檢驗,找到模型的最佳臨界點。
2 結果
2.1 建模組和驗證組基線資料比較 隨訪過程中,出現疑似感染情況的病人通過復診確定感染情況,最后1例納入病人追蹤至2020年5月底,共追蹤到病人106例。建模組和驗證組在年齡、身高、體重、性別等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僅在是否臥床方面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881,P=0.049),說明建模組和驗證組組間具有較好的同質性,可以利用驗證組資料對模型進行驗證。見表2。

表2 建模組和驗證組一般資料比較
2.2 驗證組追蹤半年感染發生情況 驗證組共106例,實際發生感染35例,感染發生率為33.0%。感染具體情況見表3。

表3 驗證組外固定感染情況(n=106)
2.3 驗證組感染發生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顯示,外固定術后發生針道感染的危險因素為是否臥床、長期服用藥物、基礎疾病、術后白蛋白、美國麻醉協會(ASA)分級3級以及使用抗生素情況等。見表4。

表4 驗證組病人感染的單因素分析 單位:例(%)

(續表)
2.4 驗證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將以上單因素分析中P<0.1的變量,包括是否臥床、長期服用藥物、基礎疾病、術后白蛋白、是否使用抗生素、ASA評分6個因素納入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有2個因素進入了回歸方程,包括合并基礎疾病和是否使用抗生素。見表5。

表5 驗證組病人感染發生的多因素分析
2.5 外固定護理風險因素預測模型的一致性和區分度 追蹤2019年6月—12月的入選病人,發現模型的陽性預測值為64.3%,陰性預測值為78.2%,準確性為74.5%(見表6)。模型預測的感染發生率為26.4%,驗證組實際的感染發生率為33.0%,O/E=1.25;Hosmer-Lemeshow檢驗χ2值為2.519,P=0.340,說明模型的一致性較好。分別應用模型組和驗證組外固定病人資料繪制ROC曲線,模型組AUC為0.808[95%CI(0.753,0.862)],驗 證 組AUC為0.704[95%CI(0.598,0.810)],當截斷值為0.373時,約登指數最大值為0.287(見表7),將驗證組人群的風險概率值以0.373為界,≥0.373判斷為感染,<0.373判斷為未感染。

表6 外固定感染護理風險因素模型預測感染情況與實際發生情況 單位:例

表7 外固定護理風險因素預測模型不同截斷值評價效果
2.6 模型預測分級情況 根據外固定感染風險因素的評分標準和風險分級,對驗證組病人進行風險預測分級。將預測分級與有無感染進行統計檢驗,結果見表8。從低風險組到較高風險組,模型預測的風險越高,感染發生率越高。

表8 驗證組預測風險分級與感染情況
3 討論
3.1 外固定感染護理風險因素預測模型的驗證 研究結果顯示,建模組預測感染發生率為26.4%(28/106),驗證組實際感染發生率為33.0%,O/E=1.25,Hosmer-Lemeshow檢驗P=0.340,提示該模型對外固定術后感染預測的一致性較好。建模組的AUC為0.808,驗證組的AUC為0.704,提示模型對外固定術后感染預測能力的區分度較好。當截斷值為0.373時,約登指數最大,為0.287,將驗證組人群的風險概率以0.373為界,≥0.373判斷為感染,<0.373判斷為未感染。風險預測分級中,根據驗證組結果,建議合并高風險組和較高風險組,合并后風險組的感染率為62.5%(15/24)。即當病人預測風險≥5分時,發生感染的風險高。劉夢元等[6]對肝移植術后多重耐藥菌感染風險預測模型的驗證結果顯示,模型的AUC為0.750[95%CI(0.651,0.862)],得分≥6分即可判斷為高風險,與本研究驗證結果相似。
3.2 納入風險預測模型的因素分析
3.2.1 基礎疾病、消毒溶液的使用 病人合并基礎疾病是外固定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本研究基礎疾病包括糖尿病、肺炎、心臟疾病,發現合并基礎疾病者發生感染的風險高。糖尿病病人術后傷口難以愈合,血糖濃度高利于細菌生長,這增加了感染的風險[7]。Kazmers等[8]的研究發現,合并慢性支氣管肺炎會增加外固定病人的感染風險。秦翠玲等[9]對骨折病人術后醫院感染的相關因素分析也發現,合并基礎疾病的病人術后感染風險高,與本研究結果一致。另外有研究顯示,病人本身已有骨髓炎,在應用外固定進行治療時,也容易發生針道感染[10-11]。針對這類病人,應加強局部換藥,將莫匹羅星膏涂于針孔周圍,每天2次,必要時給予頭孢呋辛鈉靜脈輸注,以有效控制感染[12]。
前期建模組研究還發現,使用碘伏消毒傷口對比聯合使用碘伏、氯己定和銀爾爽,可以降低感染的發生率,這與馮麗麗等[13-14]的研究結果一致。但是碘伏使用時間過長會導致局部皮膚色素沉著,且碘伏對金屬支架有腐蝕性[15]。而銀爾爽活性銀離子抗菌液是近幾年的研究熱點[16],其氧化性極高,對革蘭陰性菌、陽性菌和真菌都有效,從而極大地提高了抗菌效果[17],且銀離子抗菌液價格便宜,將抗菌液噴在針道表面,每天2次,以抑制細菌的生長。后期研究可收集使用銀爾爽進行消毒的病例來驗證其控制感染的效果。
3.2.2 營養和免疫相關因素 血清清蛋白是預測術后并發癥發生的可靠指標。傳統觀點認為清蛋白是人體營養狀況的一個指標。創傷后,炎癥介質會通過影響肝臟蛋白質的合成而致血清清蛋白水平下降[18]。研究表明,術后早期清蛋白下降對預測結腸癌切除術后手術部位感染發生有重要價值[19],也有研究發現術后早期清蛋白降低14%是術后感染并發癥發生的重要影響因素[20]。這與前期建模組的研究結果一致。建議根據病人術后清蛋白的情況,給予營養支持,以預防感染的發生。
前期建模組的研究還顯示,術中出血>200 mL,術后血紅蛋白<120 g/L也會導致術后發生針道感染的風險增加。術中大量失血后,機體有效血供減少,包括免疫球蛋白在內的大量體液蛋白丟失,導致機體免疫力下降,增加了細菌感染的幾率。類似研究也發現,術后失血量≥200 mL是感染發生的獨立風險因素,且隨著出血量的增加,感染率逐漸上升[21-22]。因此,對于術中出血量大的病人,應該采取措施恢復病人的血容量,例如采用益氣補血法可以改善骨折術后病人的貧血狀態[23]。此外,大量出血后機體血紅蛋白下降,血液攜氧能力下降,短時間內無法彌補,病人會感覺頭暈、乏力,免疫力下降,增加了針道感染的幾率。
3.3 未納入風險預測模型的因素分析
3.3.1 臥床與抗生素使用 王濤等[21,24]的研究發現,臥床>7 d會導致感染率增加,且隨著臥床時間增加,感染率上升。但驗證組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臥床不是導致術后發生感染的危險因素,前期建模組研究構建的模型也并未納入這個因素。一方面是因為部分研究對象為骨折術后病人發生醫院感染的危險因素、老年髖部骨折圍術期發生感染的相關性危險因素,都不是針對外固定針道感染的研究;另一方面現在大部分醫院推行快速康復,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術后48 h內康復醫師會協助指導病人開始康復訓練,以傷肢肌肉的等長收縮為主,同時可進行按摩、熱敷及紅外線燈物理治療,以減少疼痛以及軟組織紅腫,這些措施可以有效預防臥床病人術后感染的發生[12,25]。綜上所述,在本次建模中,并未將臥床因素納入外固定風險預防模型。
盡管驗證組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使用1種、2種抗生素發生感染的幾率高于不使用抗生素者,部分病人培養出多重耐藥菌鮑曼不動桿菌。但是前期建模組研究并未納入這個因素,主要源于使用外固定的病人存在實際情況的差異:一方面,若病人因骨髓炎需要進行外固定,而骨髓炎需要使用大量抗生素進行治療[26],容易發生針道感染;另一方面,行外固定支架拆除術的病人,手術創傷性小,大部分沒有切口,所以,不需要使用抗生素,發生感染的幾率也很小。綜上所述,外固定術后病人應根據感染指標和藥物敏感試驗等合理使用抗生素[27]。并可結合其他材料,如抗生素骨水泥[28],針對性地對感染加以控制。
3.3.2 手術部位針道感染多發生于活動較大的部位 主要原因為固定針與骨體結合不緊密產生移動[29]。模型中未納入外固定針部位,本研究結果也顯示手術部位不是外固定感染的獨立風險因素。醫院護理人員或病人術后每天都會檢查外固定支架的螺絲是否松動,固定鋼釘是否有彎曲滑動,如果發生松動,立即與主管醫生溝通采取措施,且護士進行護理時動作輕柔,避免人為原因造成針道松動。有研究也采用這種護理方法,結果25例病人中只有3例發生了輕微的針道感染[30],可見每天監測外固定針是否松動是控制感染的有效措施。
4 小結
驗證組前瞻性追蹤了來自廣州市某三級甲等醫院外固定病人的臨床資料,先利用模型對驗證組進行預測,與實際情況做對比,然后進行單因素分析、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探討模型納入因素與未納入因素,最后繪制ROC曲線圖對模型的預測效能進行評價。結果顯示,模型的區分度和一致性較好,說明模型整體預測性能較好。綜合各項研究結果來看,基礎疾病、清蛋白、術中出血量、血紅蛋白和消毒溶液應該納入模型,但是未發現臥床、抗生素和外固定針部位是外固定術后感染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驗證組通過外部驗證來評估模型的外推性,比內部驗證更具有說服力,提高了構建外固定感染護理風險因素預測模型的科學性。后續研究可應用外固定感染護理風險因素預測模型對病人進行判斷,做出綜合性、針對性強的預防外固定感染的護理計劃,并根據風險水平制定護理方案,形成評估-識別-應對的連續性風險管理方法,使模型在臨床運用中更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