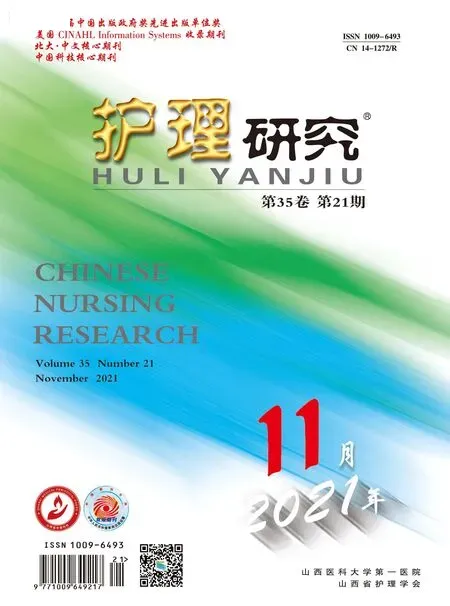智能篩查系統與NRS?2002對頭頸部腫瘤住院病人營養風險篩查效果比較
馬建紅,吳瑞臻,葉正強,曹 峻,石 勤,王豪冬
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上海 200031
因頭頸部腫瘤解剖位置特殊,與病人消化系統密切相關,腫瘤本身的因素及治療急慢性不良反應均使病人易發生營養風險[1]。研究發現,營養風險可降低病人對治療的耐受性和敏感性、延長住院時間、增加術后并發癥風險,影響治療效果[2-5]。營養風險篩查簡表2002(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2002,NRS-2002)是經過驗證的篩查工具,被廣泛推薦為病人入院后的標準程序[6-9]。但因專業人員匱乏、醫護精力不夠等原因,營養風險篩查在大多數醫院都是結合“腫瘤營養示范病房”創建或依托于某個項目在逐步推進,難以在現有的就醫環境中全面實施。已有文獻報道,營養風險篩查在腫瘤病人中的應用現狀不理想[10]。基于醫院信息系統(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實驗室信息系統(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LIS)等進行智能化營養篩查設計,輔助醫護人員進行快速篩查是亟須解決的問題。王艷莉等[11]開發了一個針對住院腫瘤病人的營養篩查系統,提取了體質指數(BMI)、體重下降、進食減少、膳食醫囑、白蛋白等指標,發現與NRS-2002相比,智能篩查系統靈敏度為83.0%,特異性為80.1%。該研究中頭頸部腫瘤病人比例不高,占23.4%。Jabbott等[12]針對門診腫瘤病人基于BMI和體重變化建立了一個自動營養篩查系統,發現與整體營養狀況主觀評估(PG-SGA)相比未達到預期的靈敏度和特異度。也有學者探索了計算機自動篩查評分預測營養不良相關并發癥[13]。本研究以NRS-2002為參考,探討自制智能營養篩查系統在頭頸部腫瘤住院病人中的適用性,從而促進營養篩查在醫院的落實。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以NRS-2002篩查結果為金標準,采用PASS 15軟件估算樣本含量。通過預實驗,預計智能篩查系統靈敏度為75%,特異度為70%,靈敏度和特異度的容許誤差均為10%。選取置信度1-α=0.95,通過軟件運行取最大樣本量為81例,再加10%失訪,共需篩查結果為陽性病人89例。預實驗營養風險篩查檢出率為24%,故需連續納入371例病人,可滿足本研究要求。采用連續抽樣的方法納入2018年11月—2020年6月在中國上海某三級甲等專科醫院接受手術治療或放化療的住院腫瘤病人439例。納入標準:年齡18~90歲;病理學診斷為喉癌或鼻咽癌;無交流障礙,知情同意參加營養風險篩查。排除標準:有胸腹水或水腫;裝有心臟起搏器;住院時間不足24 h;臨時出院病人。該研究符合赫爾辛基宣言要求,并得到了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批準號:NO.2018024)。
1.2 研究方法
1.2.1 營養風險篩查 ①NRS-2002:在病人入院后24 h內使用NRS-2002對病人進行營養風險篩查,包括營養狀況受損(BMI、體重下降、進食量減少等)、疾病嚴重程度(是否為腫瘤病人、有無糖尿病、慢病急性發作等)、年齡是否≥70歲3部分內容。NRS-2002總分為0~7分,<3分為無營養風險,≥3分為有營養風險[14-15]。②智能篩查系統:病人入院第2天,智能篩查系統從醫療信息系統、實驗室信息系統提取營養相關數據,如身高、體重、體重變化、年齡、膳食醫囑、有無糖尿病史、白蛋白、前白蛋白、診斷信息等對病人進行營養風險識別。
1.2.2 質量控制 問卷調查、營養篩查由經過統一培訓的營養師、護士完成。身高、體重測量時要求病人排尿、穿病號衣、脫鞋,使用已校正的身高體重計(Seca,中國)測量,身高精確到0.01 m,體重精確到0.1 kg,計算BMI。實驗室指標包括白蛋白(ALB)、前白蛋白(PA)。體成分使用便攜式人體分析儀(Biospace Inbody S10,韓國)測定,分析指標包括身體細胞量(BCM)、去脂指數(FFMI)、骨骼肌指數(SMI)、上臂圍(AC)、上臂肌圍(AMC)。
1.2.3 統計分析 采用EpiData 3.1數據庫專人雙錄入并核查錄入數據準確性。采用SPSS 19.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以NRS-2002為參照,計算智能篩查系統的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準確度、Kappa系數等。相關分析采用Person相關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研究期間共篩查了439例病人,其中男386例(87.9%),女53例(12.1%);年 齡20~84(60.63±10.12)歲;喉癌378例,鼻咽癌61例。病人基本特征見表1。入院時NRS-2002和智能系統篩查營養風險檢出率分別為22.8%(100/439)、34.3%(151/439),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按照腫瘤TNM分期,兩種篩查方法均發現喉癌病人Ⅲ期、Ⅳ期營養風險檢出率高于Ⅰ期、Ⅱ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鼻咽癌病人中Ⅲ期、Ⅳ期營養風險檢出率差異無統計 學 意 義(P>0.05)。有12.8%(56/439)體 重 不 足(BMI<18.5 kg/m2)的 病 人。有7例 超 重(BMI為24.0~27.9 kg/m2)病人被NRS-2002判定為有營養風險,有21例超重肥胖(BMI≥24.0 kg/m2)病人被智能篩查系統判定為有營養風險。

表1 不同營養風險病人基本特征分析

(續表)
2.2 靈敏度、特異度 以NRS-2002為參考,智能篩查系統有較高的靈敏度(84.0%)、特異度(80.2%)和準確度(81.1%);有16例(16.0%)NRS-2002判定為有風險的病人未被智能系統識別。NRS-2002與智能篩查系統篩查結果一致性中等(Kappa=0.544,P<0.001)。見表2。

表2 智能篩查系統的靈敏度及特異度
2.3 不同營養風險病人的血液學及體成分指標比較 NRS-2002和智能篩查系統兩種結果均顯示有營養風險組的血液學指標(包括ALB、PA)及體成分指標(包括BMI、BCM、FFMI、SMI、AC、AMC)較無營養風險組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3。
表3 不同營養風險病人的血液學及體成分指標比較(±s)

表3 不同營養風險病人的血液學及體成分指標比較(±s)
項目NRS-2002例數339 100智能篩查系統288 151項目NRS-2002智能篩查系統分類無營養風險有營養風險t值P無營養風險有營養風險t值P分類無營養風險有營養風險t值P無營養風險有營養風險t值P BMI(kg/m2)23.53±2.55 19.33±2.72 14.260<0.001 23.66±2.59 20.21±3.03 10.870<0.001 FFMI(kg/m2)18.11±1.69 16.19±1.48 9.556<0.001 18.12±1.69 16.81±1.76 7.032<0.001 ALB(g/L)44.16±5.44 40.77±8.16 3.554 0.001 44.96±4.95 40.45±7.37 6.400<0.001 SMI(kg/m2)7.51±0.79 6.64±0.78 8.829<0.001 7.51±0.80 6.93±0.86 6.528<0.001 PA(mg/L)256.78±67.62 207.29±44.63 6.817<0.001 273.75±54.73 190.66±51.05 15.581<0.001 AC(cm)30.00±2.51 26.10±2.49 13.244<0.001 30.06±2.53 27.29±2.96 9.445<0.001 BCM(kg)33.55±4.47 29.29±4.46 7.781<0.001 33.64±4.52 30.59±4.72 6.166<0.001 AMC(cm)26.96±2.05 24.12±1.98 11.390<0.001 26.99±2.02 25.04±2.41 7.909<0.001
2.4 相關性分析 NRS-2002與智能篩查系統的篩查結果有中等程度相關性(r=0.567,P<0.001)。NRS-2002、智能篩查系統兩種工具篩查結果與年齡、3個月體重下降百分比相關性無統計學意義,與血液學指標(包括ALB、PA)及體成分指標(包括BMI、BCM、FFMI、SMI、AC、AMC)相關性有統計學意義(P<0.05)。NRS-2002與體成分指標(包括BMI、BCM、FFMI、SMI、AC、AMC等)、2個月體重下降百分比、1個月體重下降百分比等參數的相關性優于智能篩查系統;智能篩查系統與血液學指標(包括ALB、PA)的相關性優于NRS-2002。見表4。

表4 不同篩查工具篩查結果與測量指標的相關性
3 討論
NRS-2002在我國住院病人中的適用性已有報道[16]。本課題組的前期研究也顯示,NRS-2002適用于頭頸部腫瘤病人營養風險篩查[17]。以NRS-2002為參考,基于醫院HIS、LIS系統探索實現智能篩查,對該工作在醫院的全面落實、及時發現有營養風險的病人具有積極的意義。
本研究將智能篩查系統與NRS-2002進行比較顯示,兩者營養風險篩查結果較為一致,但智能篩查系統營養風險檢出率(34.4%)高于NRS-2002(22.8%)。智能系統較NRS-2002增加了白蛋白、前白蛋白指標,可能是營養風險檢出率高的主要原因。在2019年發布的營養不良診斷和分級新標準中,除C-反應蛋白外,ALB、PA作為支持性炎癥替代反應的生物標記物被納入病因學標準[18]。由于我院C-反應蛋白未列入入院病人檢驗常規,故智能系統提取字段只列入ALB、PA兩個實驗室指標。本研究發現,在NRS-2002和智能篩查系統兩種方法中,有營養風險組ALB、PA水平均低于無營養風險組。
以NRS-2002為參考,智能系統有較高的靈敏度(84.0%)、特異度(80.2%)和準確度(81.1%)。但研究樣本中,有16例NRS-2002判定為有營養風險病人未被智能系統所識別。進一步分析發現,醫生寫病史時習慣性填“體重無變化”或“體重無明顯下降”,從而導致智能系統“體重變化”獲取的數據比人工NRS-2002篩查少。除加強對醫生病歷規范書寫的培訓外,還需要尋找并在智能系統中添加與體重下降強相關的營養指標,以進一步提高智能篩查系統的敏感性。
同時,從數據中發現,使用BMI確定營養不良風險有一定的局限性。BMI<18.5 kg/m2的比例為12.8%(56/439)。另外,有7例超重病人被NRS-2002判定為有營養風險,有21例超重肥胖病人被智能篩查系統判定為有營養風險。有研究報道,體重極度下降(消瘦)與極度增加(肥胖)都是醫療費用增加的相關危險因素[19]。
本研究還發現,NRS-2002與體成分指標(包括BCM、FFMI、SMI、AC、AMC等)的相關性優于智能篩查系統;智能篩查系統與血液學指標(包括ALB、PA)的相關性優于NRS-2002。近年來,體成分測定被越來越多地應用于臨床營養評估,與BMI相比,體成分測定可更準確地評估肌肉營養狀況[20]。有研究表明,BCM、FFMI、SMI與營養狀況和結局密切相關[21]。在2019年發布的營養不良診斷和分級新標準中,低BMI、體重減輕、肌肉減少被納入表型標準[18]。黎娜等[22]報道,鼻咽癌病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營養不良,營養篩查評估評分聯合白蛋白、淋巴細胞計數等血液學指標以及體格測量指標能更全面評價病人的營養狀況。本研究中NRS-2002與體成分指標(包括BCM、FFMI、SMI、AC、AMC等)的相關性為中等,提示體成分測定不僅僅是營養評估指標,在營養風險篩查中也具有重要意義。智能篩查系統將ALB、PA列入提取項納入評分可能是其與血液學指標相關性優于NRS-2002的原因。
4 小結
智能篩查系統適用于頭頸部腫瘤住院病人營養風險篩查,與NRS-2002同樣有效,但其在其他病種中的適用性需要在更多病種的病人中進一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