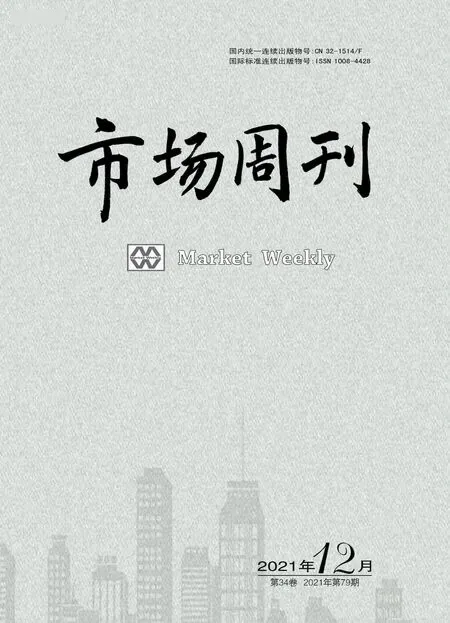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與研學旅行開發互動機理研究
楊 洋
(湖北大學知行學院,湖北 武漢 430011)
一、問題的提出
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是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族地區文化之根,是高品質的文化旅游資源。相較于物質類遺產,非遺傳承發展具有動態性、流變性、對環境和時空的非孤立性的特點[1],這決定了非遺生態性保護傳承更加注重良性發展,致力于活化利用和代際傳承。2021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正式頒布的第十年,如何實現非遺在當代社會的保護傳承發展再次成為關注焦點和研究熱點。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賦予非遺生存空間和傳承的動力。活態傳承是由傳承人、文化空間和文化傳續時間三者相互關聯、相互推進的一種狀態,最注重“傳承隊伍”和“生存環境”兩個核心內容[2]。而研學旅行正好具備這一功能。研學旅行因其“文化性、在場性”的特點,可以促進建立代際傳承鏈條、促進文化時間延續、生態式擴大文化存留空間。
正是基于這樣的前提和基礎,形成了非遺活態傳承與研學旅行開發的互動關系。因此找到兩者二維互動空間的有效聯結點和互動契合點,借助研學旅行對“非遺”進行保護性開發利用,有利于實現非遺資源由靜態的、封存式、數量型保護向動態的、開放式、質量型活態傳承轉變。
二、文獻綜述
“活態傳承”是非遺保護概念的外延詞匯,是區別于“基因封存”的一種活態保護方式。非遺活態傳承研究最早出現在人類學研究中,提倡“將人與遺產聯系起來”,并強調通過政府和公眾來識別、保護和傳播非遺[3]。趙越基于活態傳承的核心是人這一特性,將活態傳承分為縱向歷時性活態(以口傳心授方式,世世代代相傳而保留下來)和共時性活態(社會傳承或者群體傳承進行非遺傳播)[4]。因此活態傳承強調傳承過程是傳承者與接受傳承對象共同參與互動的活動過程。知網數據顯示國內外研究學者對于文化遺產活態研究已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從研究內容來看,相較于物質實體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化研究更加豐富,研究視角也更加多維。
以“活態傳承”并含“旅游開發”為主題,進行知網期刊高級檢索(2007~2021年數據),共有19篇相關論文。張婷婷認為旅游作為民俗文化傳承的一種特殊載體,其活態傳承是民俗文化傳承人、民俗文化的可持續性和民俗文化的生存環境三者緊密互動的過程[5]。齊超認為研學旅行與非遺活態傳承存在三大共性,從研學旅游視角,為福州油紙傘技藝活態化傳承提出了對策與建議[6]。洪琦提出發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游功能,建設基于非遺的主題旅游項目是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的有效途徑[7]。總體來看,非遺活態傳承與旅游開發關系的相關研究有一定的基礎,但將活態傳承和研學旅行放在同一框架中進行的研究不多。研究歷史時間也不長,研究基礎較為薄弱,關于二者互動關系的探究更是比較缺乏。鑒于此,本文將非遺活態傳承與研學旅行有機結合起來,對兩者的互動發展動因與機理開展系統研究,以期為實現非遺活態傳承的可持續性提供新思路。
三、非遺活態傳承與研學旅行開發互動動因分析
互動是社會學的概念,是指相關的事物總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非遺是依托“人”存在的活態遺產,其特點是活態流變,在某一文化空間內不斷傳承變遷。因此非遺活態傳承內涵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注重非遺原真性,即非遺生態式的有效傳承,著眼于非遺就地保護;二是強調非遺環境性,即非遺整合式地創意轉化,實現非遺回歸生活的目的。從概念內涵、價值理念等因素出發,兩者二維互動契合點主要體現在主體共存、理念契合、價值共創、需求互補和空間對接五個方面。
(一)主體共存
從非遺活態傳承的內涵中可以看出,非遺保護核心問題就是保持非遺的生存與傳承能力。非遺傳承途徑主要包括群體傳承、家族傳承、社會傳承三個層面,歸根結底離不開社會的廣泛參與和技藝的代際傳承。目前學術界關于研學旅行的概念沒有統一界定。廣義的研學旅行者可以是任何出于求知、研修(學習)目的的旅游者,即所有社會公眾。而狹義的研學旅行則具有很強的指向性,即有特定的參與者(學生群體)、有特定的組織者(教育部門或學校)、特定的參與方式(集體旅行、集體食宿)、明確的活動范圍(校外)[8]。但不管是從廣義還是狹義出發,研學旅行的主體都是“人”。二者在主體媒介上存在共同性,即“人”作為社會公眾,不僅是研學旅行體驗者、參與者,還是非遺文化的感知者、傳播者、傳承者。
(二)理念契合
非遺保護與旅游開發的關系一直是非遺旅游研究的熱點,不同的學者保持不同的觀點。在旅游開發過程中能否保持非遺的原真性?其實,無論對于旅游客體——非遺資源的活態傳承,還是對于旅游主體——游客的體驗,原真性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非遺是“活”的文化,活態傳承是在保持原真性的基礎上,實現非遺動態的、質量型活化利用。而研學旅行是典型的在地性旅游形式,相較于其他類型的旅游,更注重對特定文化場景的感知對話、互動體驗。其發展理念是研究性學習和旅行體驗的有機融合,其本質功能是實踐育人[9]。因此研學旅行主體與非遺吸引物、非遺傳承人之間的互動,既可以保持非遺生態式的有效傳承,也可以實現非遺整合式的創意轉化,還能達到實踐教學目的。
(三)價值共創
Prahalad和Ramaswamy基于“消費者體驗邏輯”視角,提出了價值共創的四個基本要素,即對話(dialogue)、獲取(access)、風險收益(risk-benefit)和透明性(transparency),也稱作價值共創的DART模型[10]。非遺與研學旅行的互動過程中,社會公眾通過與非遺文化之間的對話,感知其所蘊含的歷史傳承價值、文化資本價值、藝術審美價值、科學認知價值、經濟價值等,從而獲取復合體驗價值,這為研學旅行提供了充足的發展動力。而且研學旅行的“在場性”決定了兩者之間的產品互動和人際互動更具有真實性和透明性。研學旅行在了解傳統文化、擴大知識寬度、增強文化自覺等方面的價值,可以使其成為非遺價值彰顯的平臺。因此兩者的價值共創體現在文化資源和價值彰顯上[11]。
(四)需求互補
非遺核心內涵是“非物質”,是無法用語言或者其他符號表達出來的內蘊,其傳承和保護需要有形載體來實現。研學旅行需要擺脫“只游不學”的刻板印象,需要增強產品文化內涵和深化文化體驗。因此非遺傳承需求與研學旅行文化需求形成良好的互補關系。研學旅行可以激發非遺的多維價值,以產業化、市場化的方式對非遺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使非遺回歸社會,融入現代生活,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實現其在當代語境下以多樣化的具態產品活性生存和傳承。非遺活態傳承是對風俗習慣、傳統技藝、生活形態等傳統歷史文化的尊重和保護,而這些“活”的記憶文化正是研學旅行產品開發最好的基底要素。研學旅行從保存下來的非遺資源中汲取養分,來提高其產品的深度和廣度,實現科學育人的目的。二者在需求上實現“輸血”與“造血”的雙向互動。
(五)空間對接
為達到學習知識、了解社會、培養人格的目的,研學旅行需要真實的沉浸式場景體驗空間。非遺的產生、發展、傳承也需要存在一定的環境地域空間,而且活態傳承講究“在場空間”。二者空間對接主要體現在研學旅行所需的場景文化空間正是非遺文化展示和活性利用的傳播空間。研學旅行活動的開展有利于實現非遺傳承人與潛在被傳承人在場空間交融。在蘊含非遺文化場景空間內,兩個群體會進行主動或者被動的交互對話。主動參與非遺體驗活動,刺激社會公眾獲得真實的旅游體驗的同時,也能加深其對非遺的認知,使其在生活中自覺地傳承;而且同一空間內群體之間的氛圍渲染和人際傳播,也有助于擴大非遺傳承群體[6]。
四、非遺活態傳承與研學旅行開發互動機理
對互動動因的分析,驗證了二者之間具有良性的互動媒介和互動通道。約翰遜提出了“文化環”理論,他認為文化首先在文化領域被“編碼”,在旅游領域被“譯碼”。David Herbert對“文化環”模型進行修正,提出文化旅游建構和消費需要經過三個層次:閱讀—影響—建構[12]。因此本文以“文化環”模型為出發點,依據文化旅游消費三個層次和旅游開發生命周期,提出非遺與研學旅行開發的三個互動階段,即導入期(旅游注入——非遺靜態保護);發展期(旅游影響——非遺價值釋放);成熟期(旅游反哺——非遺動態傳承)。這種互動關系是一個循序漸進、不斷循環的過程,兩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從而使非遺活態傳承與研學旅行開發處于一個平衡、良好狀態。
(一)導入期
非遺文化作為旅游吸引物,剛剛注入研學旅行市場時,作為一類高品質、稀缺性、獨特的文化資源,被引入研學旅行產品開發的價值鏈中。此時二者的互動作用并不是特別明顯,但研學旅行開發使得非遺文化形式得到了一定的表現,旅游者的非遺文化閱讀停留在“文化表層屬性”。非遺研學旅行產品開發大多是靜態工藝欣賞、民族歌舞演藝展示。相較于其他產品類型,研學旅行因為非遺文化的介入,會呈現文化差異。這也成為研學旅行發展的最大動力,使兩者之間互動進入下一階段。
(二)發展期
研學旅行介入程度加大,非遺文化逐漸由初期的“靜態”展覽向“動態”演示、現場演繹轉變,非遺原真性、獨特性、地方性的價值開始釋放彰顯,非遺文化價值開始轉變為資本價值。兩者的互動作用進入“文化價值屬性”,游客通過旅游項目體驗、旅游商品消費等方式對非遺文化進行“解碼—譯碼”,感知在地文化差異,影響旅游者消費意向,研學旅行展現特色品牌效應。
(三)成熟期
這一階段研學旅行開發進入平穩期,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遺文化有了地方標志性的產品屬性,旅游者通過自己真實的旅游體驗對目的地形象進行建構,行為越來越理性。兩者的互動進入“文化行為屬性”。非遺有形載體呈現了特色展示與商品展銷、主體展示與群眾互動、傳統手工與現代元素結合等多種形式。地方利益相關者文化自覺意識增強,旅游經濟價值反哺非遺保護,逐步向動態傳承轉變。
五、結語
非遺保護與傳承是一項長期而且艱巨的工作,學術界關于旅游開發與非遺保護的關系爭論不已。本文試圖將研學旅行與非遺活態傳承放在同一框架中進行研究,分析兩者互動的動因和機理,希望可以促進研學旅行原真性與“非遺”活態傳承的共同發展。目前以研學旅行為切入點實施“非遺”資源活化利用和傳承保護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定量研究不多,因此本文為進行深層次探討提供了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