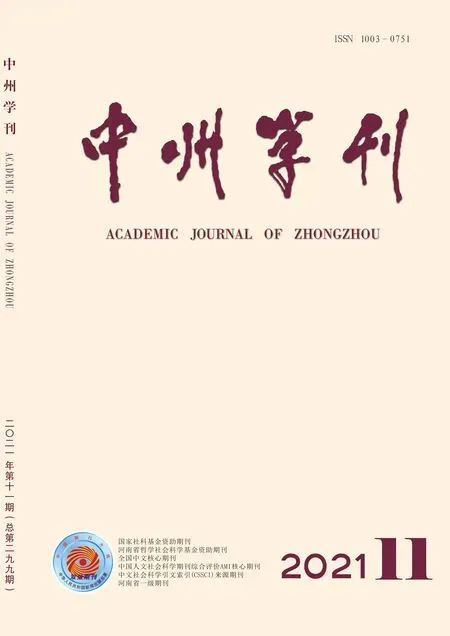葉燮“陳熟生新”思想的現代闡釋*
楊 暉 羅 興 萍
葉燮是一位具有歷史感與現實感的詩論家,他堅持以“變”為核心的文學批評觀,體現了文學史家的眼光與方法。就“陳熟”與“生新”問題,他以歷時性的視角,從“相續相禪”與“踵事增華”兩個層面,分別闡釋了“前”與“后”、“舊”與“新”之間的流變與關系,成為傳統詩學中對這一問題思考最全面的詩論家之一。對葉燮“成熟生新”思想進行現代闡釋,對于我們認識傳統詩學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連續性與非連續性
要處理好“陳熟”與“生新”之間的關系,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問題無法回避。連續性是指新與舊之間的相關性,側重連續,關注它們的共同性。非連續性是指新與舊之間的異質性,側重斷裂,關注它們的差異性。連續性與非連續性何者為先,猶如雞與蛋何者為先一樣難以回答。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思考世界來源時,似乎傾向于連續性;但在面對現實世界時,又多主張“兩一”,即對待合一,似乎先有“兩”后有“一”,傾向非連續性。事物的演變在于對立雙方的不斷交替,就歷時性角度看,非連續性在先,如果沒有這種非連續性的差別,即沒有所謂的“新”與“舊”的相異,便無更替可言。所以,就“陳熟”與“生新”而言,要先肯定其“不同”。
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非連續性本身又包含著連續性的一面。非連續性的雙方有差別,但又有相通性,否則就無法成為對立的雙方。如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在回答物質與意識誰是第一性的問題時顯出差別,但它們都是在回答關于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問題,體現出相通性來。同理,“陳熟”與“生新”雖然各執一偏,但它們都在回答如何面對“舊”與“新”的關系。詩的演變不是簡單的復制,它總是在新的環境下以某種不同的方式出現,猶如父母的生命基因傳承到子女身上并得到延續一樣。歷史上的“陳熟”雖已過去,成為歷史的記憶,但其生命基因可以通過“生新”得以延續。所以,“新”與“舊”的交替,同時又是“新”對“舊”的突破,這種非連續性同時又顯示出連續性來。
我們既要看到“對待”這一前提,一”的結果。“生新”中必有“陳熟”的因素,因為只有這種相通,才可能超越“陳熟”,跨越古今。可見,只有“舊”與“新”的隔閡,才有“古”與“今”之別;只有“舊”與“新”的相通,才可能有“舊”與“新”的合一。理解“陳熟”是為了認識“生新”,通過對“舊”的超越,實現“陳熟”與“生新”的統一,即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
有學者認為,葉燮的“陳熟生新”“其實就是文學創作中繼承與革新的關系問題”①,或者說“陳熟與生新問題的實質是詩歌的繼承與發展問題”②。雖然這些論述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陳熟”與“生新”的共時性視角,但就歷時性角度看,的確道出了問題之根本。葉燮的“陳熟生新”是關于文學演變的問題,與其“因”與“創”、“沿”與“革”的問題相類似。如果將“陳熟”與“生新”置于詩歌延綿不斷的演變長河當中來看,似乎既沒有靜止的“陳熟”,也沒有靜止的“生新”,所謂的“陳熟”或“生新”都是相對的。這就要求我們既要在非連續性中看到連續性,也要在連續性中看到非連續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葉燮那里,與“陳熟”“生新”相類似的概念還有很多。如王運熙等指出的,“源、流、正、變是指詩歌的歷史發展,而沿、革、因、創是指詩歌發展中的繼承和創造的關系”③。蔣寅指出,“這里的沿、因即繼承、沿襲,革、創即變化、創新,是文學史觀念中兩個最基本的概念”④。可見,在源與流、本與末、沿與革、因與創等過程中,每一次衰落都孕育著新生,每一次新生總會衰落,正是在這種“陳熟”與“生新”的交替中構成了詩歌的演變軌跡。“陳熟生新”是葉燮關于詩歌演變的宏觀表達,它包含“相續相禪”與“踵事增華”兩個層面。那么,“陳熟”與“生新”在其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這是我們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
二、“相續相禪”中的“陳熟”
葉燮重視天地古今之變化,《原詩》開篇云:“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詩之為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⑤正因為如此,朱東潤說:“橫山之論,重在流變。”⑥張少康也說:“葉燮《原詩》的中心是闡述詩歌的源流發展和演變狀況。”⑦綜觀《原詩》及其諸多詩序可以發現,在他的“相續相禪”中,延續者是“陳熟”,禪讓者也是“陳熟”,表現了對“陳熟”的高度重視。
1.“相續相禪”的重心在“陳熟”
如何理解“相續相禪”呢?就“續”的字義,《說文解字》有:“續者,聯也。”《爾雅》有:“續者,繼也。”就“禪”者,此處多為“禪讓”之意。那么,“相續相禪”就是后者對前者的相續,前者對后者的禪讓。因為有了“陳熟”,才有“相續”的對象;也因為有了“陳熟”,才有“禪讓”的主體。可見,“相續相禪”的重心在“陳熟”。
葉燮是一位主變論者,他雖然強調“生新”,但不忽視“陳熟”。他在《原詩·內篇下》中用了五個“不讀……不知……”顯示對前者的重視:
不讀《明》《良》擊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不讀三百篇,不知漢魏詩之工也;不讀漢魏詩,不知六朝詩之工也;不讀六朝詩,不知唐詩之工也;不讀唐詩,不知宋與元詩之工也。夫惟前者啟之,而后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創之,而后者因之而廣大之。⑧
因先有“不讀”的對象,方有“不知”的后果,其結論是唯有“前者啟之”,方有“后者承之”;唯有前者“創之”,方有后者“因”之而“廣大”之。沒有“前者”,就無“后者”,即無“陳熟”就無“生新”。他還特別用“夫惟”兩字來強調對“陳熟”的重視。他在《原詩·內篇下》中所說的“后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后人,何以竟其引伸”⑨,表達了“前人”與“后人”的辯證關系。正如朱東潤所說,“此言謂不學古人,乃正所以深學古人,其意在此”⑩。
葉燮在《原詩·內篇下》中又以“地之生木”為喻,闡釋了“陳熟”的重要性。他將詩之演變的順序以“根”“蘗”“拱把”“枝葉”“垂蔭”“開花”為喻,呈現了蘇李詩、建安詩、六朝詩、唐詩、宋詩的變化邏輯,再次肯定這層層累進的過程是“從根柢而生”,于是有了“無根,則由蘗何由生?無由蘗,則拱把何由長?不由拱把,則何自而有枝葉垂蔭、而花開花謝乎”的一連串反問。
值得注意的是,葉燮曾提到過“陳言”,這是借韓愈“惟陳言之務去”之說,批評時人因無“去陳言”的本事而缺乏創新。葉燮的學生沈德潛對此理解更為清晰,他在《說詩晬語》(卷下)第三十六條中說:“蓋詩當求新于理,不當求新于徑。譬之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未嘗有兩日月。”這是借唐人李德裕《論文章》中的“璧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的說法,提出“理”要新,而不當求新于徑。用葉燮的“陳熟生新”來解釋,就是日月“光景常新”,但本質未變,故能“生”中見“熟”,今對日月,雖有異樣,然似曾相識。一生盡對日月,但無生厭之感,乃因語境不同,心情不同,雖有新元素參與,但仍是以前的日月。
徐中玉先生曾在《論陳言》一文中對韓愈“陳言之務去中”作解釋時論及葉燮。他說:“在文學語言的創造上,在消極方面要除去‘陳俗’,在積極方面就要追求‘清新’……完全的成熟固不足取,完全的生新一樣也無作用,必要從成熟中說話出來的生新才是真正的清新。所以葉燮《原詩》卷三中說:‘陳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濟,于陳中見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在徐先生看來,“清新”不能離開“成熟”而“故趨新奇”,“完全的成熟固不足取,完全的生新一樣也無作用”,“清新”來源于“成熟”。徐先生又從接受者的角度,分析了“清新”之所以被稱贊,在于“用人人用慣看慣的一套材料,去安排編制出嶄新的東西來”。這里肯定了“成熟”的作用。這些論斷對于我們理解葉燮“陳熟”與“生新”的關系具有啟發意義。
葉燮對明代復古主義只得“陳言”而不得“古人之興會神理”的創作的批評,與韓愈《答劉正夫書》中“師其意,不師其辭”的說法相通。可見,葉燮提出的“于陳中見新,生中見熟”的思想,正是對“惟陳言之務去”的進一步闡釋。
葉燮提出“察其源流,識其升降”,同樣顯出了“陳熟”的價值。他說:
吾愿學詩者,必從先型以察其源流,識其升降。讀三百篇而知其盡美矣,盡善矣,然非今之人所能為;……繼之而讀漢魏之詩,美矣、善矣,今之人庶能為之,而無不可為之;……又繼之而讀六朝之詩,亦可謂美矣,亦可謂善矣,我可以擇而間為之,亦可以恝而置之。又繼之而讀唐人之詩,盡美盡善矣,……又繼之而讀宋之詩、元之詩,美之變而仍美,善之變而仍善矣;吾縱其所如,而無不可為之,可以進退出入而為之。此古今之詩相承之極致,而學詩者循序反復之極致也。
葉燮提出古今之詩時變而有詩變,但其間必有“相承”的延續。雖然不必如《三百篇》,漢魏之詩、六朝之詩、唐人之詩、宋之詩、元之詩,但其間的“善”與“美”則是相承的。他批評公安派、竟陵派不能“入人之深”,正在于他們“抹倒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說,獨辟蹊徑,而栩栩然自是也。……入于瑣層、滑稽、隱怪、荊棘之境,以矜其新異,其過殆又甚焉”。他批評“近代詩家”“一切屏棄而不為,務趨于奧僻,以險怪相尚;目為生新,自負得宋人之髓”,乃是“新而近于俚,生而入于澀,真足大敗人意”。歸根結底,都是因為沒有處理好“陳熟”與“生新”的關系,無視“陳熟”。
2.漂浮中的“陳熟”
葉燮堅持以文學史家的眼光與方法看待詩學問題,因此他對“陳熟”的認識不是獨立的、靜止的,而是整體的、流動的,是將其還原到歷史的原初狀態,不僅看到局部的變化,更能從整體上認識演變的過程。葉燮認為,詩歌的發展呈現出復雜的流變過程,“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復盛”。詩歌的延續性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短時段中“盛與衰”的轉化,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衰而復盛;二是長時段中盛衰交替,很難說清何者為盛,何者為衰。詩歌的演變正是短時段的局部運動和長時段的整體運動的統一,“是一個局部運動和整體運動交互作用的歷時性過程”。
“陳熟”與“生新”的關系與葉燮所講的“盛”與“衰”的關系一樣,就一時而論,有“生新”與“陳熟”之別,但就千古而論,“生新”必來自“陳熟”,又必自“陳熟”而復“生新”。當然,前一“生新”已不等同于后一生新,前一“陳熟”也不同于后一陳熟。正如王運熙先生所言,“在源流滾滾的詩歌發展長河中,從一個階段來說,有正有變,由盛而漸衰,而總的趨勢則表現為每一次衰落孕育的興盛”。
葉燮所謂的“陳熟”與“生新”的相互轉化也如“盛”與“衰”的轉換一樣,從短時段看,或由“陳熟”轉“生新”,或由“生新”轉向“陳熟”;但從長時段看,并沒有固定的“陳熟”與“生新”。詩歌演變是“啟”與“承”的統一,“承”離不開“啟”,詩歌傳統需要不斷地創新賦予生命力;“啟”離不開“承”,詩歌發展離不開對詩歌傳統的繼承。但“承”與“啟”的屬性不是一成不變的。
詩歌的演變總是“舊”與“新”的沖突與轉化,或“舊”融入“新”,或“新”取代“舊”,是關系、比例和價值的“調整”,是“新”與“舊”的“適應”,其“舊”是調整中的“舊”,“新”是“調整”中的“新”,它們通過不斷的“適應”在各種條件作用下走向自己的反面。無論是“承”與“啟”,還是“盛”與“衰”,都離不開“對待”這一關系。葉燮不僅看到對待的對立統一,而且能把握住對立雙方運動的特征,即對待雙方屬性在正負兩極間滑動著,消解了恒定,體現出不確定性來。
其實,詩歌演變中的長時段是短時段的累進,任何短時段都無法擺脫長時段而獨立存在。每個時期的文學作品“都處在‘相續相禪’、有‘沿’有‘革’的詩歌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不能把它們看作是孤立的,彼此、前后毫無關涉的存在”。長時段中的短時段才真實,才有意義。短時段只是理論分析的需要,讓詩變“突然”停下來,靜止不動,這是一種理論的假設,而真實的情況是每一短時段都處于長時段的過程當中——這才是詩變的原始面貌。
葉燮論詩總是在長時段中認識對象,重視其“節節相生”“息息不停”,將短時段還原于長時段的真實面貌當中,消解了理論上的假設,在“節節相生”中去認識每“一節”,在四時之序中去認識每“一季”。因為,每一節,或每一季中的“生新”必將淪為“陳熟”,而“陳熟”又會孕育著“生新”種子,詩歌在“陳熟→生新→陳熟→生新”的不斷交替中演變,呈現了對立雙方交替的詩史演進模式。所以,就有了“歷考漢魏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為源而長盛,變為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這一觀點性的表述。
建安風骨慷慨悲涼,反映民生疾苦,抒發建功立業的豪情,是繼“漢樂府”的“生新”之作,開一代詩風,但它又不可能長盛不衰,終將因時代變化,以及詩體自律之需求而流于“陳熟”。詩至六朝,“卑靡浮艷之習”沿襲至唐初,詩壇萎靡不振。唐之開元、天寶又達到鼎盛,有王維、孟浩然的山水田園詩與高適、岑參的邊塞詩,相得益彰,沿著“盛→衰→盛→衰”的模式交替。在這延綿不斷的流變當中,建安詩、六朝詩、初唐詩、開寶詩等,誰是“陳熟”,誰是“生新”呢?顯然,它們既是“陳熟”也是“生新”,這將隨著參照物的變化而變化。它們既是下一段的陳熟,又是上一段的生新。雖然葉燮是一位詩之主變者,但他以宏觀的視野,在“舊”與“新”的關系中不忽略“舊”的重要性,即不忽略“陳熟”的重要性。
三、“踵事增華”中的“生新”
時代在變化,詩體也在變化。葉燮論詩主張“生”“新”“深”,雖然他在“相續相禪”中側重“陳熟”,看到“陳熟”的功績,但他詩學思想的主體精神則是在“踵事增華”中的“生新”。
1.“踵事增華”辨析
在講到創作起因時,葉燮提出“先有所觸以興起其意,而后措諸辭、屬為句、敷之而成章”,即有現實感觸,方能作詩。他說:“忘其為熟,轉益見新,無適而不可也。若五內空如,毫無寄托,以剿襲浮辭為熟,搜尋險怪為生,均為風雅所擯。”這里的“熟”與“新”就涉及“陳熟生新”問題。“剿襲浮辭”與“搜尋險怪”都被“風雅所擯”,他列舉了上古的飲食器具、音樂變化、古者穴居等,提出“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于極”,從宏觀上描述了詩演變中“踵事增華”的特征。
“踵事增華”是兩組動賓結構“踵事”與“增華”的并列。踵,作名詞時表示足跟,《釋名》有“踵:足后曰跟,又謂之踵”;作動詞時表示步行、繼步之義。“踵事”即繼步前事,其目的在于“增華”。“華”即繁華,越來越茂盛。“踵事增華”字面的基本內涵是繼承前事而越來越繁華。
在詩學上,“踵事增華”大約首見于南朝梁蕭統《文選序》。他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增加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冰塊增大乃因積水而至,積水越多,冰塊越大,“踵事增華”就是“變其本而加厲”。這里的“厲”為形容詞,表示“越來越……”的意思,并無貶義,是對以往的超越。
“踵事增華”的這種意思還被其他多處地方運用。如宋人王黼在《宣和博古圖》一書中談論“敦”的演變過程后說:“因時而制,踵事增華,變本加厲”,提出這種制器“與時為損益”,“時異則跡異”,認為“若乃敦者,以制作求之,則制作不同:上古則用瓦,中古則用金,或以玉飾,或以木為;以形器求之,則形器不同:設蓋者以為會,無耳足者以為廢,或與珠盤類,或與簠簋同”。總之,器物隨時代演變而越來越精致完美,時代變了,就不能“求合于古人”。“踵事增華”是一種進化論思想的典型表述,重點在“生新”。
“相續相禪”的重心在“陳熟”,“踵事增華”的核心卻在“生新”。明人謝榛在《四溟詩話》卷四曾鼓勵詩人要有創新的勇氣,他說:“人不敢道,我則道之;人不肯為,我則為之。厲鬼不能奪其正,利劍不能折其剛。古人制作,各有奇處,觀者當甄別。”葉燮則以“古云天道十年而一變”的立場,執著地追求“踵事增華”中的“生新”。
葉燮認為“踵事增華”的動力,一在于乾坤不息,二在于人之智慧心思之無盡。詩的演變亦然,“虞廷《喜》《起》之歌,詩之土簋擊壤、穴居儷皮耳。一增華于三百篇,再增華于漢,又增華于魏”。他將詩的演變比喻為人的行路:唐虞(堯舜)詩如第一步,三代(夏商周)詩如第二步,漢魏以后詩如第三步、第四步。在葉燮看來,踵事增華是萬物演變的模式,前人“始用”,后人所以能“漸出”“精求之”“益用”。這也如他所說的,自《詩經》以來,“其間節節相生,如環之不斷;如四時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停,無可或間也”。這是他主張“生新”的理論表述。
葉燮在《原詩》中還連續用了太虛、工拙、造屋三個形象的比喻,來進一步表述其“增華”的思想。他以“太虛”之喻講詩的演變,認為漢魏詩初見形象,其外在格式初步成形,但遠近濃淡俱未分明;六朝漢魏詩雖已烘染設色,初有濃淡之分,但遠近層次無顯明分野;唐詩諸多手法分明,能事都已具備;宋詩則更加精益求精,各種手法“無所不極”。葉燮以繪畫技巧為喻,講述詩之手法精益求精的過程:漢魏天然,六朝略備,唐詩大備,宋詩精致。他又以“工拙”為喻來講詩歌的藝術追求,認為漢魏詩工中見拙,拙中見工;六朝詩工者為多,拙者為少,能從工中見出長處,拙中見出短處;而唐詩可以工言之;宋詩則有意求工求拙,但反對以此作為論詩之優劣。詩之優劣,從藝術追求上講,漸漸走向精致化之路。他以“造屋”來比喻詩歌結構的發展,列漢魏、六朝、唐詩、宋詩為節點,結合前兩個比喻中由不分而至分明、由拙而工,認為詩之演變如造屋之過程,由宏大而至精細,這是“運會世變使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天也”。太虛、工拙、造屋三個比喻表現了葉燮對詩之演變的基本看法,即他所說的“變本加厲”,“以漸而進,以至于極”的“踵事增華”模式。正如蔣寅所言,葉燮所說的“踵事增華”是文變的合目的性,這為進化論文學發展觀提供了一個矢量。
葉燮認為“生新”是詩歌演變的必然。他說:“原夫作詩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觸以興起其意,而后措諸辭、屬為句、敷之而成章。當其有所觸而興起也,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于心。出而為情、為景、為事,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使即此意、此辭、此句雖有小異,再見焉,諷詠者已不擊節;數見,則益不鮮;陳陳踵見,齒牙余唾,有掩鼻而過耳。”他從創作因觸而發和欣賞之接受過程兩個方面分析了“生新”的合法性。就創作而言,詩變系乎時事,觸的情、景、事不同,創作也不同;就欣賞而言,“初見”尚好,“再見”不擊節,“數見”不鮮,“陳陳踵見”則遭人“齒牙余唾,有掩鼻而過”,從接受方面提出“生新”的必然性。
他進而以日常生活的實例論述詩變的思想:
譬之上古之世,飯土簋,啜土铏,當飲食未具時,進以一臠,必為驚喜;逮后世臛臇炰魚膾之法興,羅珍搜錯,無所不至,而猶以土簋土铏之庖進,可乎?上古之音樂,擊土鼓而歌康衢,其后乃有絲、竹、匏、革之制,流至于今,極于九宮南譜。聲律之妙,日異月新,若必返古而聽擊壤之歌,斯為樂乎?古者穴居而巢處,乃制為宮室,不過衛風雨耳,后世遂有璇題瑤室,土文鏽而木綈錦;古者儷皮為禮,后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純百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禮以儷皮,孰不嗤之者乎?
這里從古之飲食器具、音樂、穴居等三個方面,再次論證了詩變的合理性,自然得出“生新”的合理性,與劉勰《文心雕龍·通變》中詩體、語體和風格方面的演變軌跡“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新”相通。
總而言之,葉燮并不忽略“陳熟”。但相比而言,他更重視“生新”。這種重視是貫穿他整個詩學思想之始終。
2.重視“生新”的詩歌批評
葉燮重視“生新”,不僅有較強的理論表達,而且將其作為詩歌批評標準。縱觀他的批評活動,大凡有“生新”者都給予肯定,這形成其詩評的特色。他這樣描述詩歌的發展演變:
漢蘇李始創為五言……,建安、黃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后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為創。此變之始也。三百篇一變而為蘇李,再變而為建安、黃初。……一變而為晉,如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其間屢變而為鮑照之逸俊、謝靈運之警秀、陶潛之澹遠……。歷梁、陳、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習而益甚,勢不能不變。小變于沈、宋、云、龍之間,而大變于開元、天寶。高、岑、王、孟、李,此數人者,雖各有所因,而實一一能為創。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一一皆特立興起。……宋初,詩襲唐人之舊……蘇舜卿、梅堯臣出,始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自后諸大家迭興,所造各有至極。……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為最,各能自見其才。有明之初,高啟為冠,兼唐、宋、元人之長,初不于唐、宋、元人之詩有所為軒輊也。
葉燮以“變”為核心來描述歷代詩歌創作的軌跡,將“生新”元素多者,視為“大變”,少者視為“小變”。其中所列的代表人物,都是有所創新的,鮮明地體現出他詩歌批評的標準。這是他詩學觀念中最有價值的地方。
在中國詩歌史上,葉燮最推崇杜甫、韓愈、蘇軾三人,正是因為他們詩歌創作中的“生新”。他認為“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是因“惟神,乃能變化”,也就是能“生新”。葉燮對杜甫評價最高,說杜詩“包源流,綜正變”,不僅具備漢魏之渾樸古雅,六朝之藻麗秾纖、澹遠韶秀等“陳熟”的基因,而且“無一字句為前人之詩也”,更有“生新”元素,是“陳熟”與“生新”的統一,其影響之大“無一不為之開先”。葉燮認為杜甫之所以能別開生面,是因為他有“胸襟”。因其“胸襟”而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以出,隨遇發生,隨生即盛”,所以題材上能“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吊古人、懷遠道,凡歡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因其所遇而得題材,因其題材而抒發其情感,因情感而形成詩句,獨開生面,“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茍,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憤陶情”。葉燮對杜甫推崇之至,有“可慕可樂而可敬”的贊揚。
葉燮認為韓愈詩為唐詩一大變,“用舊事而間以己意易以新字者”,“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直接影響到宋代的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蘇軾、王安石、黃庭堅等,形成“無處不可見其骨相棱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獨善于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的生面目。雖然在當時韓愈還沒有得到足夠的認同,但“二百余年后,歐陽修方大表章之,天下遂翕然宗韓愈之文,以至于今不衰”,開啟了“思雄”的生面目,連俗儒都能看到“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
葉燮也非常推崇蘇軾,因蘇詩為“韓愈后之一大變”。他認為蘇詩“包羅萬象,鄙諺小說,無不可用”,“常一句中用兩事三事者,非騁博也,力大故無所不舉”,“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后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形成其“無處不可見其凌空如天馬,游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罵,四時之氣皆備”的生面目。
葉燮之所以贊揚這三家詩,正是因為他們都開生面,有“生新”的創舉。如蔣寅所說:“葉燮更具體地闡述了三家‘大變’和詩史背景,變革方式以及歷史意義,顯出獨到的批評眼光。杜甫承先啟后,不僅集前代之大成,更開啟后世無數法門;韓愈懲于大歷以來的成熟,一變以生新奇奡,遂發宋詩之端;蘇東坡則盡破前人藩籬,開辟古今未有的境界,而天地萬物之理事情從此發揮無余。”
葉燮用“河流之喻”來論說詩之演變。他說:“從其源而論,如百川之發源,各異其所出,雖萬泒而皆朝宗于海,無弗同也。從其流而論,如河流之經行天下,而忽播為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于海,則亦無弗同也。”他認為,詩之演變,就其源頭而論,不同的是源,相同的是“皆朝宗于海”;就流而言,不同的是“經行天下”“忽播為九河”,相同的是“俱朝宗于海”,都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從“陳熟”與“生新”的角度看,河流是由無數的波浪聚成的,后浪推前浪,也如“陳熟”和“生新”是互為前提、相互生成的。詩之變如一波水浪,詩的演變歷史由很多這樣的水浪組成,當一個水浪走向衰亡時,它便會被另一個水浪所替代。詩演變的轉折點既是“陳熟”的結束,也是“生新”的開始。它不是新的替代舊的,而是“新”的包含了“舊”的,是“舊”與“新”的統一。
葉燮詩論中的詩歌發展進程具有歷史延續性。他在探究詩歌的源流、本末、沿革、因創、正變過程中,將孤立的二元相互鏈接,融入整個詩歌的歷史進程。他認為前者“禪讓”并“相續”于后者,后者承接前者,踵事增華,形成正負二元交替的詩史演進模式,詩的演變就呈現出一個動態的、渾然的、互動的整體。
楊鴻烈在談到中國詩的演進時,對持進化論觀點的葉燮評價頗高:
詩的退化說——中國是崇古思想最發達的國家,這種說法在詩里自然很多,但這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要推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著者從詩的本質,和心理學方面觀察都是部分的承認,但章先生要用人力來復古便是發可笑之論——并且從歷史進化的眼光不能不承認詩是進步的。詩的進步說——這說在中國最是鳳毛麟角——著者所引的只有元稹、都穆、方苞、吳雷發、袁枚、葉燮六人,葉燮的說法最詳切明盡——葉燮正確的歷史觀念在中國思想史上應該占有極重要的位置。
楊鴻烈肯定葉燮在《原詩》中表達的“增華”思想,并給予大量的引用,說“這樣正確的歷史觀念不只有中國詩學思想發達史上提上一筆,就是在文化思或思想史上都應該大書特書呢”,表達了對葉燮的推崇。
中國傳統詩學提出“陳熟生新”問題的時間雖然較遲,但它卻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在詩學誕生之初,人們似乎都在試圖回答這一問題。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發現,葉燮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比前人更廣闊、更深入,豐富了傳統詩學的內涵。他一方面以歷時性的角度,從“相續相禪”與“踵事增華”兩個維度詳盡地分析了“相續相禪”側重“陳熟”,“踵事增華”中側重“生新”的意義,肯定了只有在“陳熟”與“生新”的“相濟”中才能賦予詩歌創作以生命和意義;另一方面他還以共時性的角度,從“對待”之不確定入手,消解以往“陳”與“生”、“熟”與“新”的優劣之爭,將其還原到詩歌真實的、現實的創作演變鏈條中,肯定“陳”“生”“熟”“新”的歷史合理性,以及它們之間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相濟”狀態。
總之,葉燮的“陳熟生新”思想已超出了簡單的進化論或退化論的層面,突破了狹窄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呈現出完整的、延綿不斷的生命體的成長過程。他對詩歌創作演變過程的描述和對其演變邏輯的探索,使詩歌藝術在時間軸上得到敞開,為后人闡釋“陳熟生新”思想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注釋
①黃保真、成復旺:《中國文學理論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81頁。②葉燮、沈德潛:《原詩·說詩晬語》,孫之梅、周芳批注,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43頁。③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60、261頁。④蔣寅:《原詩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78頁。⑤⑧⑨葉燮、薛雪、沈德潛:《原詩 一瓢詩話 說詩晬語》,霍松林等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3—4、33—34、34、34、243、35、44、44、3、8、5、45、6、6、33、5、5—6、4—5、19、8、17、17、17、50、8、50、28、8、51、9、50、6—7頁。⑥⑩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276頁。⑦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51頁。徐中玉:《論陳言》,《國文月刊》第7冊,1948年。蔣寅:《清代文學論稿》,鳳凰出版社,2009年,第259頁。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126頁。沈德潛《葉先生傳》有“先生論詩,一曰生,一曰新,一曰深,凡一切庸熟陳舊浮淺語須掃而空之。”沈德潛:《清詩別裁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85頁。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29頁。王黼:《宣和博古圖》,諸莉君校,上海書店,2017年,第296—297頁。謝榛:《四溟詩話》,宛平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第107頁。劉勰:《文心雕龍》,范文瀾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第520頁。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211、218—2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