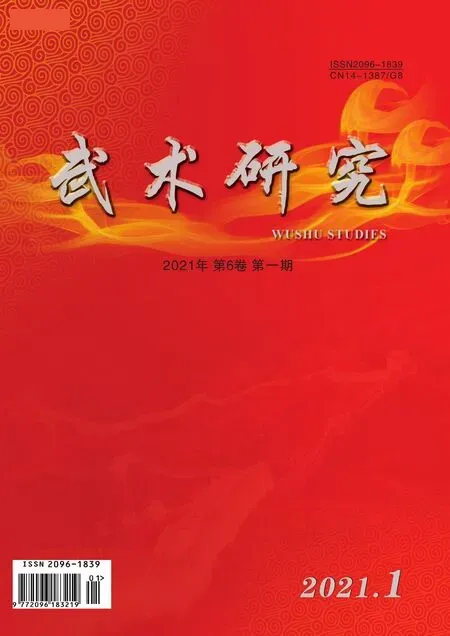研究武術與文化之關系的兩種范式
喬鳳杰
清華大學,北京 100084
截至目前,我和我的團隊所做的最主要研究工作,是武術文化哲學,是在哲學層面研究武術與文化的關系,而我們在哲學層面對武術與文化之關系的研究,大致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武術視角詮釋文化,看看文化對武術已經或者能夠提供什么樣的指導與幫助;二是從文化視角詮釋武術,看看武術能夠為文化的傳承與傳播做些什么樣的貢獻。從武術視角詮釋文化和從文化視角詮釋武術,是關系密切但卻又是性質不同的兩種研究。在這篇文章我要分享給大家的,正是我們進行這兩種研究時的基本范式——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和從文化視角對武術的實然考察。
1 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
1.1 此范式的含義
三重詮釋,即“實然考察”“應然推測”“可然聯想”。實然,即實際如此;應然,即應該如此;可然,即可以如此。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是要通過“實際如此的考察”“應該如此的推測”“可以如此的聯想”,來分析被詮釋文化中有哪些東西對武術是有意義的,讓被詮釋文化成為武術的營養,擴充或者改良武術的文化。
“實然考察”,是對有材料記錄的文化對武術之影響的考察,是要通過材料分析來考察文化對武術已經產生的影響;“應然推測”,是對沒有材料記錄但在邏輯上應該會有的文化對武術之影響的推測,是要通過邏輯分析來推測文化應該對武術產生的影響;“可然聯想”,是對既沒有材料記錄也沒有邏輯上的應該但卻可以讓文化對武術產生影響的聯想,是要通過意義分析來聯想文化對武術可以產生的影響。自然,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需要兼顧這三點。比如,當你從武術視角對儒家思想進行三重詮釋時,不但要基于文字材料來考察儒家思想對武術的可確定的影響,而且要基于兩者的思想理念、行為方式等來推測儒家思想對武術應該產生的影響,還要單純從武術發展的視角來聯想儒家思想對武術可以具有的影響。
有人把所有的詮釋方法歸納為三類,即以作品為中心的詮釋、以作者為中心的詮釋、以讀者為中心的詮釋。如果以此為標準來進行定性的話,那么,我們這里所說的三重詮釋,大致上是一種以讀者(也就是詮釋者)為中心的詮釋。自然,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必然是以武術人為中心的詮釋。
1.2 此范式的合理性
此范式的合理性,主要是因為它直接對應著我們研究武術與文化之關系的某一種目的。對此,可以分解為以下三點:
(1)我們研究武術與文化之關系的目的之一,是建設武術的文化,即“讓文化滋養武術、讓武術承載文化”;(2)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既有實然考察,又有應然推測,還有可然聯想,是具有明顯的建設性的,其本質就是要“讓文化滋養武術、讓武術承載文化”(3)正是因此,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本身就是在建設武術的文化,自然也就是研究武術與文化之關系的一種范式。
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這種研究范式,可能會給人們的觀念或者習慣帶來些許的沖擊。這里需要稍加說明的是,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猛一看似乎只是在為文化服務,但其實更主要的還是在為武術服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武術的文化建設。
1.3 此范式的形成過程
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肇始于我的碩士論文《對<老子>思想的武術學剖析》研究(在導師徐儀明教授指導下),自覺于我的博士論文《中華武術與傳統文化》研究(在導師賴永海教授指導下),逐漸成熟于我的后續研究、我對研究生的學術指導、研究生們自己的學術研究。
現在看來,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在我的碩士論文研究中已經開始了。在我當時從武術視角來剖析《老子》思想時,幾乎是帶著“發現新大陸”的興奮勁來進行的,所以我在這篇論文的研究與寫作中,思想是極其開放的,也就糊里糊涂地運用了我今天才意識到的“實然考察”“應然推測”“可然聯想”相結合的三重詮釋范式。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自覺而清晰地完成了“應然推測”與“實然考察”的有機結合。客觀地講,這并不是事先設計的,而是被逼出來的。因為,傳統的純粹的實然考察范式在我當時的研究中無法發揮太大的作用。具體情況是:當時在進行中華武術與傳統文化之關系的研究時,我遇到了一個非常尷尬的狀況——中國哲學、中國文化研究的資料浩如煙海而武術學科中能夠收集到的則是可信度很低、數量還比較少的資料以及一些無法考證的紛紜傳說。面對這樣的狀況,為了完成這個選題的研究任務,我只能在盡可能考察歷史事實的前提下,而更多地進行義理層面的推測。這種研究范式所導致的是,我對中華武術與傳統文化之關系的研究,雖然也有少量的基于資料的歷史考察,即“實然考察”,即“實際如此的考察”,但更主要的則是對中華武術與傳統文化之內在關系的“應然推測”,即“應該如此的推測”,是對中華武術與傳統文化的思想會通。
把“可然聯想”作為一種明確的研究方法,是在我此后的研究特別是指導我自己的研究生進行學術研究時所慢慢確定的。“可然聯想”,是在解讀原本與武術沒有明顯關系的文化時,讓研究者立足于武術的發展需求,以學習的態度、適宜的解讀方式來吸取被研究文化中的營養成份,從而完善與擴充武術的結構與內容。相比“應然推測”,“可然聯想”的創造性要更加明顯一些。因為“應然推測”雖非引經據典、言出有據,但畢竟還是能夠在武術與文化之間找到或顯或隱的聯系的。“可然聯想”,秉持的是一種學習的、拿來主義的、為我所用的思想原則。當我們發現某一種文化特別優秀,但我們并沒有發現這種文化與武術之間有什么聯系,而我們又特別想從這種優秀文化當中學點東西的時候,“可然聯想”就可以發揮作用了。
客觀地說,如果王獻斐的《武術內向訓練與道教內丹修煉》、熊金才的《論少林拳的禪拳合一》主要還是“實然考察”與“應然推測”相結合的話,那么,趙嚴的《修心:從茶道到武道》,則主要是進行“可然聯想”了。此后,王剛的《道德仁藝:武術修煉視角的儒家思想研究》、朱安洲的《武術視角的老莊思想研究》、嚴盼盼的《武術視角的佛教思想研究》、陳勝飆的《武術視角的天人合一思想研究》,則更是越來越多的“可然聯想”了。當然,我的《武術哲學》《文化符號:武術》中涉及武術與文化之關系的研究,也有很多是在“可然聯想”中完成的。
可以想象,在現代學術研究特別是當今中國的武術研究中,人們對“實然考察”一般不會有什么排斥,對“應然推測”或許會有不同的看法,但對“可然聯想”這種研究范式有很大可能就會產生疑慮了。但是在我看來其實是大可不必的,因為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稍稍回顧一下歷史的話,不難發現,這種研究范式其實早已是中國武術人的老套路了,而且正是因為它才使武術有了很多出人意料的創新性發展。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少林寺僧從武術角度對佛教的“可然聯想”,禪拳合一的少林拳怎么可能產生?如果沒有陳王庭對太極理論、道教思想的“可然聯想”的話,以太極為名的太極拳又怎么可能產生?
需要說明的是,此研究范式中的三重詮釋這種方法,并不只是適合于武術與文化的關系研究,而是可以適用于任何視角(如戲曲、書法等視角)對文化的詮釋,是一種以詮釋者為中心的、拿來主義的、為我所用的文化詮釋方式。這種對實際存在、應該存在、可以存在的文化兼顧詮釋的方式,強調的是在發現基礎上的創新,是一種以詮釋者為中心的、更具生命力與現實意義的學術研究范式。
2 從文化視角對武術的實然考察
2.1 此范式的含義
實然考察,就是作為三重詮釋之一的實然考察;從文化視角對武術的實然考察,是要通過“實際如此的考察”,來看看武術對文化有沒有意義、有什么意義、在哪些方面有意義。當我們把實然考察單獨作為一種詮釋方法,并以前面所講“三個中心說”為標準來對其進行定性的時候,那么,我們這里所說的實然考察,大致上就是一種以作品(或許可以有一點點讀者)為中心的詮釋。自然,從文化視角對武術的實然考察,也就是以作品(或許可以有一點點讀者)為中心的詮釋。
2.2 此范式的合理性
此范式的合理性,也主要是因為它直接對應著我們研究武術與文化之關系的某一種目的。對此,可以分解為以下三點:
(1)我們研究武術與文化之關系的目的之一,是彰顯武術的文化,即“表達武術的文化、讓人們更加清晰地了解武術承載的文化”。(2)從文化視角對武術的實然考察,就是要把武術已經承載的文化梳理清楚,讓武術的文化更容易被人們了解與理解,其本質就是要“表達武術的文化、讓人們更加清晰地了解武術承載的文化”。(3)正是因此,從文化視角對武術的實然考察,本身就是在彰顯武術的文化,自然也就是研究武術與文化之關系的一種范式。
2.3 此范式的形成過程
談到這里,必然要說明的一點是,作為兩種范式,從文化視角對武術的實然考察與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并不是對立而常常是互補的。因為,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是在建設武術的文化,從文化視角對武術的實然考察是在彰顯武術的文化,而建設武術的文化與彰顯武術的文化自然不是對立而是可以互補的。當我們明白這一點之后,也就會明白我下面要講的一個重要觀點——我對武術與文化之關系的研究,既是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又是從文化視角對武術的實然考察。
為什么是這樣呢?這是因為,從研究過程來看,無論是《中華武術與傳統文化》,還是《武術哲學》,抑或是《文化符號:武術》,其中所涉及到的武術與文化之關系的知識,基本上是利用或者部分利用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這種研究范式所獲得的,但是,從寫作過程來看,無論是《中華武術與傳統文化》,還是《武術哲學》,抑或是《文化符號:武術》,其中所涉及到的武術與文化之關系的知識,又都是通過從文化視角對武術的實然考察所獲得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后者是對前者的梳理。對我個人來說,這種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在完成《中華武術與傳統文化》《武術哲學》《文化符號:武術》等書稿以及其他文章的過程中形成的。正是因此,作為我個人之代表作的《中華武術與傳統文化》《武術哲學》《文化符號:武術》,既是武術視角的文化哲學,也是文化視角的武術哲學,從而使我的武術哲學與文化哲學融為了一體。
當然,談到這里,必須還要聲明的是,從文化視角對武術的實然考察,并不一定要依附于從武術視角對文化的三重詮釋,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研究范式,在我這里只是一個巧合而已。事實上,更多人的相關研究,只重視文獻,完全靠材料說話,都是從文化視角對武術的實然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