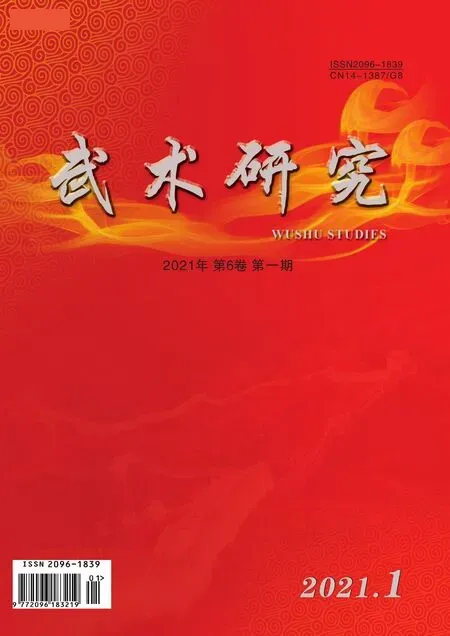形端志正:淺論中華射藝的修身價值
代梧佑 申夢悅
上海體育學院,上海 200438
眾所周知,弓箭的歷史源遠流長,中華射藝文化魅力獨特,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體系。射禮是射藝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周就有大射禮、賓射禮、鄉射禮、燕射禮。至明代,射禮成為“每月朔望的鄉射禮基本制度文化”。[1]射禮的形成與發展,將弓箭從殺戮武器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修身養性的一種途徑。射禮將禮、樂和射結合起來,用禮的典雅端莊規范射的行為,用射的行為來體現禮的精神內涵,超出了原本的弓箭或者單一的禮或者射的范疇。而形端志正無論是對于禮還是對于射而言,既是基本要求又是核心內容。
有詩云:“射貴形端志正,寬襠下氣舒胸。”一個“貴”字不僅體現了射藝形端志正的重要性,而且也點明了射藝修煉的一個重要目的——達到形端志正。形端,即身正體直,四平八穩,不歪不斜;志正,即精神專注,心無邪念、雜念,做到正心誠意。[2]中庸講“中不偏,庸不易”,中正平和正好與行端志正相切合,射藝作為儒家文化的載體之一,傳承千載而不失。
射藝內涵豐富,有君子之射、仁者之射、觀德之射等等。但凡射者無一不是從形端志正開始,可以講“形端志正”初步回答了我們為什么要練習射藝的問題。然而,形端志正并不是射藝的最終價值目標指向,隨著修習的步步深入,它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形端志正”的君子。
1 形端志正——自古已有的射藝之道
“射貴形端志正,寬襠下氣舒胸。五平三靠是其宗,立足千斤之重。開要安詳大雅,放需停頓從容。后拳鳳眼最宜豐,穩滿方能得中。”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
以上摘錄分別出自《鏡花緣:西江月.射箭》和《禮記·射義》。這些經典論述對于射藝有著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可謂字字珠璣,而其主題都是講練習射藝要重視形端志正。本文認為“形端志正”包含兩方面的內容,第一是形端,即外在的身形動作,身端體直;第二是志正,即注意力專注、內心正直、品行端正。
1.1 形端
古圣賢皆愛射,以射為題材的名句經典不勝枚舉。老子將天道比作張弓,孔子提倡君子之爭,孟子提出仁者之。王陽明《觀德亭記》中說“君子之于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后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也。”君子于射,內志正,外體直,方可言中。黃百家在《征南射法》中說到“射雖在手,實本于身。”弓和箭雖然在手中,但“心、身、體既正,則手足相應,引滿時以右眼視左手,無不中矣!”從這些言論中我們不難看出,圣賢們推崇射藝是因為它能夠使人達到“行端志正”的育人效果。
從現代人體解剖學來來看,射箭是依托人體的天然結構特點通過訓練來使人體與射箭這項運動更好的結合。行端是從準備到引弓再到撒放的姿態。準備姿態時講究站姿端正,不偏不斜,頂天立地。引弓時的行端重點在于骨骼支撐,即古人所說的“入彀”,應做到“五平三靠”,即“兩肩兩肘,天庭俱要平正,此之謂五平;翎花靠嘴,弓弦靠身,右耳聽弦,此之謂三靠。”[3]撒放時的行端一方面在于動作的穩固,撒放時前后對稱直線用力,保持動作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則體現為儀態從容。
1.2 志正
志正,從技術層面上講可理解為瞄準。康熙字典中疏曰:“志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所主,欲得中也”。志正,是射箭能否射準的關鍵。志正,從心理方面來講,是決賽競技成敗的關鍵。在《元武門侍射并序》中說道“若天地合道,星辰獻藝,端視和容,內正外直。自近而致遠,耀威而觀德,無不神通,無不極用。”射藝做到胸有成竹、心中有箭、人箭合一,自然能處之泰然,淡定從容。《續修四庫全書射學指南》中也說“容止亦端,乃可引弓,若遽然引弓發失,則力不出、心又亂。諸冰難除矣!”由此可見,良好的心理素質、平和的心態和坦然的射箭觀是志正的綜合體現。志正,從修身觀德方面來講,心志就是我們行為的主導者和內心追求的指引者,射藝在于樹立正確的目標和養成高尚的品德。王陽明“射以觀德”的高度概括和總結,既是對歷代圣賢射藝論述的總結,又是射藝新的發展。射藝是人修煉的手段、方法和過程,觀德則是考核,志正無疑是觀德的核心內容。總之,形端志正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形端是基礎,唯有體直身正才有命中的可能。志正是保障,瞄不準不可能命中,不注意品德修養,談不上修習射藝。形端志正才是完整的射藝修行。
2 射藝的個人追求與社會需要
2.1 射藝對學習者心態和行為的影響
射藝能夠正心正己、修身修德,達到正習性、修德行的目的。這里所說的習性可以理解為習慣與心性,習慣乃是在習射過程中以射藝而正己、端正行為。而心性則是在習射過程中鍛煉射者的態度、性格和觀念。在《禮記·射義》中說道“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然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射藝要求要型端志正,必須要有安定平和、得失坦然的心態,然后才可以射箭。在射箭的過程中如若射不中而不能怨恨對手,而要反思自己失誤的地方。《射經》中對射藝的要求為:“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文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射箭要有泰山崩于面前而面不改色和臨崖射箭而心不驚的從容心態,同時也要內外合一,心志和行為相合方能達到射箭的高級水平。這是古人對學習射藝的要求,這也意味著射藝能夠讓習練者達到正心正己,修身修德的目的。
《論語·八佾》中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這是孔子提倡的君子之爭,在射藝的修習中體悟仁者之道,修身克己,提升自我修養。君子并不是與世無爭,而是在爭斗過程中要像射箭一樣,彬彬有禮、尊重對手。
2.2 射藝對滿足培養人思想價值體系的社會需要
“茲土與肅慎鄰,勁弓毒矢,相殺傷以事者,數千有馀載”,如今“一變而雍容辭遜,爭以君子乃如斯。斯豈非我列圣暨朔之化之至歟?”
——《旅庵遺稿》卷四
“聚羽林而論技,陋前代而不屑。習禮儀而盡正,慶復覩于今日。”
——金孝元:《射以觀德賦》
以上兩則引文主要是說弓箭用途的變化,弓箭從戰爭殺伐利器轉變成了用于教化的一種方式。弓箭是國家的武備大綱,春秋時期的庠序之校就有專門的射藝課程,“禮樂射御書數”為主要的教學內容,射藝是古代教育的一門重要課程,其承載的“德”“仁”等內涵成為社會教化的主要方面。[4]
“王氏力斥文武異事,而主張文武合道當在禮樂之事中寓于射,得乎射禮之精藴。”文武合道是射藝的最大特點,通過射藝的習練來提高習練者的身心素質和道德修養。當下,德智體兼修是我國現代社會教育的發展趨勢,弘揚并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成為國家政策,射藝作為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射藝文化對于提升人民群眾的文化素養和思想道德水平有著重要的作用。真正“工于射者”須體悟四道:體雍和之道以存心,則孝悌之行也;體沉毅之道以踐言,則忠信之友也;推反身之道以改過,則好修之士也;推禮儀之教以治民臨民,則遠近悅懷,頑梗歸化矣。孝悌、忠信、修身、禮儀這些正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以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在滿足人民的文化需求的同時,也在構建現代社會主義文化體系。總之,射藝不僅能滿足個人修煉的需要,同時也適應于社會教化。在當下大力弘揚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傳承并弘揚中華射藝文化,意義深遠。
3 形端志正在射藝中的具體體現
3.1 形端志正調身姿
調整身體的姿態、鍛煉身體的協調能力是練習射藝最直接、最明顯的好處。初次接觸射箭的人,會情不自禁的出現偏頭(后仰,前探)、閉眼、聳肩、扭身、前俯、后仰、曲肘等毛病。[5]通過練習能克服這些毛病,前后對比,一目了然。
射藝的基本姿勢以開弓大小有大拉距、中拉距、小拉距之分;雙腳站位有開放式、閉合式、平行式之分;不同朝代的射法技巧也各有所不同;勾弦方法大體有三指勾弦法和拇指勾弦。無論選取哪一種射藝練習方法,行端志正都是核心技術要領。
3.2 心端志正提境界
射藝不是一門簡單身體運動練習,它可以關乎人的整個一生。《射藝中的禪》的作者赫力格爾六年苦修弓道,探尋射藝中的禪理論,弓道不僅在于日常儀節和修習,同樣重在內心的修煉。即心靈的境界決定著人生的境界,在射箭中同樣也影響著能否命中。
運動員有比賽型和訓練型之分,即有些運動員平時訓練成績突出,然而一遇到大賽卻成績平平,相反另有一部分平時表現一般的運動員在參加大賽時往往能超常發揮,取得更好的成績。因為實際上,比賽成績又很大程度上受到運動員心理因素的影響。[6]心境對于射藝格外重要,高水平的運動員在動作技術上相差無幾,決定成績好壞的就是心理水平。射藝訓練有助于提高心理水平,尤其是經歷過射藝比賽后,學員的心理素質明顯增強。而心理素質增強的直接效應就是成績的上升和人變得自信更有活力。[7]這便是“技近乎道矣”。
3.3 行端志正做好人
“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禮記·射義》)。“立德樹人,天下太平”是千百年來統治者不變的追求,而射藝的君子風范有助于推動達到“觀盛德”的目的。射藝教會人怎么做一個有益于社會的人。在射藝的練習過程中,個人的道德品行在修煉射藝的過程中悄無聲息的修煉著。從弦不空放學會愛惜事物,從揖讓而升中學會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從審彀后發中領悟人生的真諦。一切的修行都只為“行”,“行”是做人的方式,是待人處事的具體形態,做到行端志正,縱然不能福澤一方,最差也不會禍害一方。
3.4 “形”“心”“行”“三行”合一修煉君子之風
通過外在的“形”的練習,不斷提高內在“心”得素養,最終體現在“行”上。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這,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其中”。君子是賢德之人,射藝練“形”、煉“心”、練“行”,三者合一則是通往君子之路的必然之路。[8]
總之,當下學習射藝文有詩詞歌賦、文史典籍,去體悟“仁者如射”“射以觀德”的人生哲學,武可日日操習、勤練不輟,自有強身健體、娛樂身心、益壽延年的功效。而這一切奧妙似乎都始于“形端志正”。
4 結語
“形端志正”較好的回答了我們為什么要練習射藝。蘇聯功勛教練C·瓦伊采霍夫斯基曾指出:“今天,身體強壯的運動員可以進入決賽,而獲得金牌的卻是精神上的強者。”射藝不僅能練就強健的體魄,更能提升個人修養,“志正”即為精神上的強者。
射作為“三十六兵器”之首,其殺傷力不容小覷,但千百年來,射藝并沒有因為它的這種特點而禁止,反而在修身養性和禮儀教化領域取得一席之地,這其中“形端志正”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就如同劍一樣,在暴徒中是兇器,在君子手中則是身份的象征,射藝同樣如此。一切在于人,而不在于物,物為人用,人用物顯現個人德行。射藝教人從“形”到“心”再到“行”最終成為有益于社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