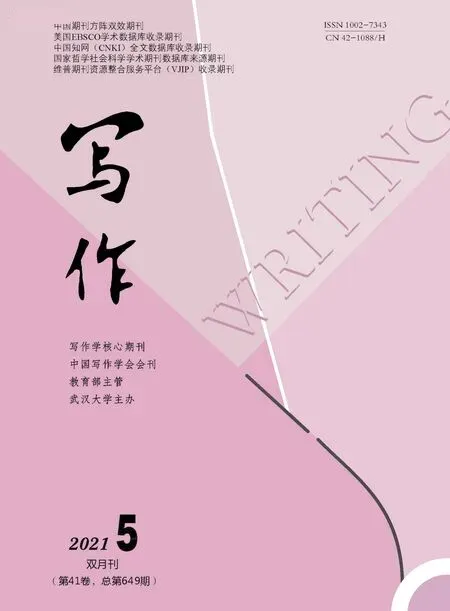在現實與傳奇之間
——趙志明訪談
李 壯 趙志明
為全面展示當下青年寫作力量,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楊慶祥教授策劃主編“新坐標書系”,分卷主編由一批80后、90后青年批評家、學者擔任。叢書第一輯已正式出版。即將出版的《趙志明卷:石中蜈蚣》由筆者擔任分卷主編。為更好地編選該書,筆者與趙志明進行了一次訪談,圍繞個體藝術風格、當下青年作家寫作資源及狀態等主題展開討論。現將對談成文發表,與廣大讀者、寫作者及研究者分享。
李壯:志明兄好!你我之間現在是很熟悉了,周末經常一起踢球,各種文學場合也會頻繁遇見,嘻嘻哈哈地談天說地聊八卦。不過我一直很清楚地記得我們初次見面時的場景。套用一句經典的文學表述,“多年以后,面對訪談提綱,李壯會回憶起在中國人民大學見識趙志明的那個遙遠的下午。”的確是下午,當時我還在北師大讀研究生,去人民大學楊慶祥老師組織的“聯合文學課堂”參加蔣一談老師的研討活動,你也來參加了。那之前已經有朋友跟我推薦過你的小說,說一個叫趙志明的青年作家,小說寫得特別有意思,值得一看。我記在心里,還沒來得及買書,誰知沒幾天就在現實中遇見了本尊。回來后我讀了你的小說集,就是那本《我親愛的精神病患者》,的確是非常喜歡,后來也有推薦給很多人。我記得很清楚,那天下午你坐在窗戶底下的位置,正在我斜對面。陽光從你身后進來,直落在我的眼睛里,因此每當我看過去,都無法看清你的臉,只能分辨出圓滾滾黑乎乎一顆腦袋——從腦袋往上瞧,頭發很短;從腦袋再往下瞧,哈,脖子也不長。然而談起文學來,你的話卻是一點兒都不短。如果把每一句單獨來看,似乎屬于那種短平快的風格,很簡單、很利落;但所有句子結合起來看,延展性又特別強,我相信如果沒有時間限制,你可以用同樣的語速講上一個小時。
這是我對于你的最初印象,看不清五官、看不清表情,但聽得清聲音,聽得出這是一個“講述狂人”。這樣的印象之所以產生,本身帶有很強的隨機性(比如你當時所坐的恰好是窗戶下方的位置)。但我覺得此種印象是非常合適而恰當的。后來讀你的小說,我也常常是著迷于其中那種“講”的氣場。你經常被形容為“說書人”。于我而言,小說里的你就同那個下午的你一樣,會在某個讓觀眾逆光的位置,一拍驚堂木,開始講你的故事。那逆光的所在,也許是在人民大學的會議室,也許是在圓明園的大水法,也許是在人來人往、煙火氣十足、雜糅著街拍攝影師與廣場舞大媽的北京街頭。你讓我們看不清面孔,但我們知道你陶醉其中,甚至忘記了面前有沒有觀眾。
這是一種非常感性、也非常直接的印象。它由一個場景、以及此場景所引發的感受和闡釋構成,類似于古典文學常說的“起興”。我覺得當我們談論文學的話題,倒不妨就從這樣感性的、經驗性的話題引入。在此意義上,我首先想問一下,在你的生命記憶中,有沒有哪個場景、哪種印象,是直接與你的寫作發生過關聯的?比如說,會猛然開啟了你的表達沖動、或讓你感受到了寫作與個體存在的關系?往小里說,這可能關乎你寫作的發生學;往大里說,這或許會涉及你寫作的潛意識。
趙志明:謝謝李壯。你當時撥冗給《我親愛的精神病患者》撰寫的評論,我還時常翻看,特別是你提到“凝視亡魂的深情”,讓我醍醐灌頂。我確乎在小說中多處寫到亡魂,像《我們都是有痔瘡的人》《一家人的晚上》《另一種聲音》等,死去的父親的形象一直徘徊不去,但我此前并沒有很明確地意識到我在“凝視”,且飽含“深情”。可能是因為我父親早歿,這種痛楚或者說是羞愧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難以釋懷。在初中高中甚至大學階段,填寫相關表格中的家庭成員項時,我都會在母親之前寫下父親的名字,還有他如果活著到現在的年齡。很難解釋其中的緣由。因為這種經驗和記憶,當我看到費爾南多·佩索阿寫他父親的詩,因為詩人做了和我類似的事,在其父親去世后多年來一直刻意遮蔽著父親的死亡,制造父親仍然活著的假象,特別有觸動,甚至心悸惶然。我因此正式寫下了我第一首看起來很不像詩歌的詩歌:《一道簡單的算術題》。一個家庭蠶食死亡的方式,是母親和兒子圍繞丈夫(父親)的死亡做算術題。好像始于佩索阿所鼓吹的狂風,在我心田掀起的漣漪,到此詩為止。當然,我不會忘記我和佩索阿做過的相似的夢,努力憶起的煎熬,努力遺忘的痛苦,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說到身邊親人亡故的悲痛往事,我不會忘記兩個朋友和我分享他們的經歷,對于我而言,他們的舉動不僅大方,近乎慈悲。一個比我年長,我視其為兄長,他在某一個晚上說到他的亡母,突然淚涌哽咽的場面,讓我感動,并且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好像多年來我一直恥于啟齒的關于父親的死亡,終于可以向身邊人向所有人向全世界坦承。好像只有到了這般年紀,才可以放肆地大說特說這種糟糕的厄運,才能夠承受并全然不懼死亡帶來的傷害。似乎就等這樣的時刻,禁令完全被解除。一個和我同齡,他有一次說起他外婆家復雜混亂且冰冷的家庭關系,他外婆不易不幸地生活在這種一頭亂麻的關系中,他感到痛心,覺得外婆生不如死。正是說到這里,他才恍然驚覺,原來二十年來死神沒有從他身邊帶走一個親人,他深感遺憾。言外之意,不就是有為他外婆開脫的意味嗎?想來,一個人的成長從來不會缺少死亡的陪伴,除非他用早夭將生命固定住,并以此饋贈給其他活著的人,用他的死亡陪伴其他人的活著。似乎是,我在父親去世的同時(獲得消息時),猛然間成人;又或者是,前面都是假象,我仍然是一個孩童,躲在父親去世的陰影里,直到發現我有勇氣說出父親去世的真相并且不會感到羞愧的時候,我才真正長大。如此一來,造成兩者之間些微差別的時間,該如何審視和考量呢?陷在時間裂痕里的死亡又該如何重新置放呢?這可能是我情不自禁喜歡去琢磨時間和空間的初衷。像《你的木匠活呵天下無雙》,像《石中蜈蚣》,像《I am Z》,都帶有這樣的痕跡。說到這里,不免要提到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我最初是經詩人劉立桿推薦,并從他那里借閱到,因為在我寫了《還錢的故事》后,他當時就說我的小說帶有胡安·魯爾福的風格。當時,我是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堂而皇之地接受了。現在想想,胡安·魯爾福讓一幫死去的人復活,在一個封閉的、籠罩著白霧的山谷里,不知生死地一再演繹著他們的命運無常,這豈是初涉寫作的我所能仰望其項背的。不止有魯爾福,還有帶給我們《莫雷爾的發明》的卡薩雷斯,以及寫出《中國長城建造時》《在流放地》的卡夫卡,現在有“裝置小說”一說,他們的小說整體上確實像裝置一樣,形成閉環,在設定好的軌跡上運行演繹,但又滋生出無窮的可能性,使得閱讀和解讀看起來更像是嘗試一次游戲。我渴望寫出這樣的作品,它若能成功分娩,在拓寬小說的邊界上,建立哪怕只是毫厘寸功,也會讓我引以為傲,快慰平生。
李壯:韓東有兩句詩,“我有過寂寞的鄉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溫柔的部分。”你也有過寂寞的鄉村生活吧?你對于“講”的激情,那種天馬行空、奇思怪談背后的溫柔與深情,是不是都與此有關?如果把你的小說和一些訪談、創作談放到一起來讀,不難發現,你筆下的故事經常會同你的真實經歷有交集。比如《我是怎么來的》,里面寫到主人公的出生與計劃生育政策的關系,我初讀時印象很深,后來發現并不是虛構。包括《小德的假期》,里面極其生動、極其詳細地描寫了小孩子暑假釣團魚的細節,我猜也跟你的真實經歷有關。篇幅所限,這兩篇并沒有收進本書,但我覺得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單獨找來讀一讀。對于童年和故鄉,你曾用“鄉間樸素而光怪陸離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粗獷而又細密的關系”來概括。這樣的童年經歷或者說成長環境,對你的寫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趙志明:在溧陽,有很多神奇之事。我舉幾個例子。在早先,溧陽的行政中心不在溧城鎮,而在舊縣。舊縣,就是很舊的縣,以前的縣,現在淪落為一個村鎮了。舊縣曾經發現大規模墓葬群,據說村戶家家都挖掘到寶物,秘不示人,當作傳家寶傳之后世。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的耳邊就全是盜墓的故事。當時還流傳一個致富口訣,“要想富,去挖墓,一夜一個萬元戶。”對了,在那個年代,萬元戶還是農人祖孫三代都為之奮斗不已的目標,類似于脫貧,奔小康。還有一句,叫“小小的溧陽城,大大的前馬村”,這里面有個來頭。當年陳毅率領新四軍抗擊日本侵略者,在溧陽很多地方都留下事跡。日本軍隊雖然占領了溧陽,但拿轉戰于山山水水的新四軍沒有辦法。有一次在追擊游擊隊時到了前馬村,日本兵竟然被村里巷弄整得頭昏腦漲,才發出這樣絕望的嘆息。前馬村也因此留下美名。別橋是一個年代久遠的古鎮,因為馬姓世家而聲名遠播,其中最有名的是馬一龍,他留下很多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津津樂道,其中一個就是他不希望女兒嫁人,在女兒新婚夜讓女兒吞吃紅雞蛋,而讓女兒窒息而死。促邪,陰缺,這些詞都明確無誤地指向他。后來人又自行腦補,說一個盜墓賊,知道馬一龍女兒殉葬頗豐,夜里去盜墓,移動尸體時,將卡在喉嚨口的雞蛋擠出,馬一龍的女兒因此復活。在我們小學旁邊,有一棵古樹,樹下有青石板墓門,原來被土蓋著,后來水土流失,慢慢顯露。當年曾有幾個人奉村委之命去鋸樹,而離奇生病,說什么的都有,簡直就是《聊齋》的現代版本。樹老心空,年輪出現裂縫,就有蛇鼠鳥雀在其中藏身,陰雨之前悶熱天氣,就會看到丑陋的赤鏈蛇,或者修長的司母蛇從縫隙哧溜出來。那確實是一個古墓,但年代不是很久,墓主生前應該是寄居在清末或者民國,我和幾個小伙伴曾經鉆進去,貓腰走了大概三五米,不知道通向哪里,因為害怕就退出來了,冒險戛然而止。鄉下人家為了漚田,會做草淹塘,將各種雜草、糞便之類堆在里面,任其腐爛,以為肥料,撒在地里,作物會長得很茂盛。鄉村就像一個天然的草淹塘,千年人物萬年怪,都會被她漚成肥料,稱之為“講古今”“講空話”,不就是古今多少事,都成轉頭空嗎?偏偏鄉人生活又浸泡在開門七件事里面,沉溺于親朋來往的“一碗水要端平”之中。我寫小說,若關乎到我熟悉的場景、事件,會忍不住雜糅些個人私料進去,為的是讓敘述生動和有情一點,不然干巴巴的,不要說讀者,我自己都不能卒讀。
李壯:說到一個地方“神奇”,可能多數人會首先想到西部,比如西藏新疆這類土地廣大、人口密度低、又有宗教背景的地區。至于你的家鄉溧陽,地處東南,自古屬于人口較多、生活還算富庶的地帶,想不到也有這么多神奇的故事,也會顯示出如此光怪陸離的一面。對于小說家而言,這樣的話語背景確實可以稱作是“有很多肥料可漚”,這種滋養我想真的是特別珍貴的。
說完生活經歷,再說說寫作經歷吧。你開始小說創作的時間很早,但大量發表和出版作品、為文學界所熟知,基本是近五六年的事情。二者之間,似乎間隔了比較長的一段時間。你自己也在許多文章中提到過,大學畢業后有一段日子,為生計四處奔波,沒有太多進行文學創作的時間。看你發來的創作年表,從2004年到2012年之間,的確存在著一段接近十年的“空白期”。那段時間是如何度過的?對于你的寫作,這段“空白”是不是真的空白?你如今的生活及創作狀態又是怎樣的呢?
趙志明:我表面上是樂觀派,骨子里透著些虛無主義。閱讀和寫作很對我脾性,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盡如人意之事,我也能安之若素。1998年我開始寫小說,在暑假一口氣寫了5篇,投了出去,《另一種聲音》很幸運地在《芙蓉》上發表,我并不知道當時韓東在負責小說欄目,不然會更加喜出望外。但這次發表對我也僅僅是點到為止,并沒有激發我去寫更多小說,爭取更多發表機會。隨后,我認識了楚塵,并經由楚塵認識了韓東、顧前、朱朱、劉立桿、崔曼莉、李檣、朱慶和、外外、趙剛、毛焰、王小山等人,興奮雀躍,溢于言表。相比于寫作,相比于發表,我覺得和他們的交往更有意思。他們都是我的老師,在閱讀上開拓了我的眼界,在寫作上讓我沉潛,因為他們都淵博犀利,不是淺薄之徒可比。我一直很慶幸,我在南京上大學,并且在大學快畢業時認識了這些人。楚塵的書架成了我的私人圖書館,在那里我看到了格里耶、西蒙、卡佛等人,帶來了奇妙無比的閱讀體驗。然后就是像小學生那樣聽他們聊天。確實是小學生,恨不得把舌頭嘴巴都變成耳朵,變成六耳獼猴,因為不敢插嘴,在他們的博學和洞見面前,我噤若寒蟬,這話并不為過。畢業后,我認識了曹寇、彭飛、慢三等人,混跡于他們論壇、西祠胡同,受到激發,開始寫小說,寫詩歌。小說寫完都貼在他們論壇上,然后悄悄看各種留言,我覺得在那里聚集著當時對我來說是最好也最有幫助的評論家。也看其他人的帖子、小說、詩歌,真是目不暇接,真是盛宴和狂歡。于是,我寫了《還錢的故事》。當時《芙蓉》的田愛民也在他們論壇,看到了,幫我發表在《芙蓉》上。從《另一種聲音》到《還錢的故事》,都發在《芙蓉》上,這讓我對《芙蓉》懷有特別的感情。畢業后我在楚塵的公司上班,做圖書編輯,每天看稿子,“年代詩叢”“外國詩歌譯叢”,我簡直如饑似渴,快樂如魚。但南京的這種生活很快落幕了,2004年我收拾行裝,孤身來到北京。但這段經歷太豐富了,值得我花八年、十五年去消化。所以說,從2004年到2012年的這段空白期,我自己反倒沒有意識到。我一直沉浸在南京的余韻中。據說,運動員們會進行一種想象中的模擬訓練。當沒有訓練場地或訓練場地不適合訓練時,就會通過冥想,假想自己在高山滑雪或者擊打一顆不存在的高爾夫球。我覺得打腹稿與此極為相似。一個故事在想象中逐漸成形,通過精雕細琢漸趨完美,然后封存在腦海中;如果不順利,也可能胎死腹中。好幾年時間,我就是這樣玩味小說,至少沒有全然陌生化。這是就我內部環境來說,至于外部環境,在北京遇到的人事和南京大不同,也需要我調整,去適應,以找到俯仰和呼吸的空間。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反哺我的小說。我的朋友都相信我的寫作能力,因為我在生活上如此低能,難以獲得哪怕是任何一種成功,而這種成功他們愿意相信可能是對寫作有害的。換言之,如果在這幾年,我不是那樣潦倒困頓疲于奔命,而是鮮衣怒馬,多金廣廈,那么我很可能漂離寫作,越來越遠,即使還心心念念系于寫作,也回不來了。不寫是一種狀態,寫不來是另一種狀態。我自己,我的很多朋友,都相信我只是不寫,而不是寫不來。不寫而寫,寫而不寫,其間區別,值得深思。有時候,空白可能是留白,我個人覺得留白是中國文化的一種神髓,將棋譜熟諳于心嫻熟調素琴的人,未必能盡得弦外之音。說到我現在的生活和創作狀態,一言以蔽之,就是虛席以待。孔子說四十不惑,我已年過四十,生活也好,寫作也好,早失去年輕時候的心火,但愿能夠從容些、慢一些,不僅心有余,力也要充足。
李壯:不寫是一種狀態,寫不來是另一種狀態。我覺得這話說得特別好。有關于“寫”,你最早的成名平臺是“豆瓣”,你在豆瓣上有一大批忠實的讀者,而且據我所知,豆瓣上很多讀者的專業水準都很高。從“豆瓣”上火起來、隨后在所謂“傳統文學”領域獲得認可的作家,以往還不算太多,近些年已經比較常見了。這樣一種相對特殊的寫作發表平臺,對你的寫作風格包括寫作心態,有沒有潛在的塑造作用?相較于那些通過傳統期刊發表、作協系統推薦方式成名的作家,你會不會覺得自己身上或作品中有哪些比較特殊的氣質,是與所謂“出道方式不同”有關的?
趙志明:發表平臺不一樣,對自己的要求肯定也會不同。豆瓣發表幾乎沒有什么門檻,會讓寫作者有所松懈,而在形成自己風格上則助益頗多。不過,很多小說家在豆瓣發表作品,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把豆瓣當作一個存放文檔的抽屜,他們上豆瓣,更多的是利用豆瓣進行其他方式的閱讀,比如看書、聽音樂、看電影。豆瓣的評分還是有公信力的。擁有豆瓣賬戶的作家,包括很多其他豆瓣用戶,受豆瓣的影響其實很小。拿我舉例子,我是2007年加入豆瓣的,但直到我在豆瓣上傳《還錢的故事》等小說,我的好友一直是三百多,幾乎都是認識的,平時互動也很少。后來寫中國怪談系列,突然漲了很多友鄰,但也幾乎是零交流。若看到有些留言比較有意思,偶爾才會回一下。屬于典型的不活躍用戶。我和很多豆瓣作者還是很不一樣的,他們更年輕,和網絡更親近,同理,我和期刊青睞的很多作家也不太一樣,我重視和別人不一樣的我,所謂“出道方式不同”也在這一范疇。如果試圖挖掘一些比較特殊的氣質,我認為是,首先和他人不一樣,其次,和自己不一樣,求新求變。打一個人用的桌子,和打一張足夠一百人用的桌子,其中的區別遠不如打一張桌子和造一條船。
李壯:問一個很沒有新意、但任何訪談都很難繞開的問題——你的閱讀譜系和影響譜系是怎樣的?對你影響最深的是哪些書?你有哪些最喜愛的作家?
趙志明:在語言上我受詩人影響頗深,在結構上我則努力向小說家學習。結構好比魚的骨架,語言好比魚鱗。我偏愛細密的魚鱗,勝過規則的骨架。閱讀譜系和影響譜系就穿插在那些優秀的詩人和小說家之間,他們的名字若繁星,他們的影子會使文學殿堂的光線變暗。枚舉顯得多此一舉,看山跑死馬,會讓人氣餒灰心。對我影響至深的作者,有但丁、索德格朗、金宇澄、蘇童、韓東、朱文、卡夫卡、馬爾克斯、奈保爾、塞林格、于小韋、小安、顧前、卡瓦菲斯、胡安·魯爾福、麥卡勒斯、圣埃克絮佩里。
李壯:總體來看,你的小說寫作內部會呈現出兩種差別很大的風格。一種很魔幻,腦洞大開、天馬行空、想象力爆表,走的是傳奇故事或生存寓言的路子。還有一種,特別現實主義,很瑣碎,很真實,貼地而行、絲絲入扣。我寫過一篇你的作家論,題目里用到了一個詞叫“上天入地”,就是分別指稱這兩種風格。如果放到文學史脈絡里觀看,前者似乎植根于我國古代筆記小說、志怪故事、“三言二拍”和《聊齋志異》的敘事傳統。而后者,則讓我想起90年代以來韓東、朱文包括更年輕的曹寇等人的寫作。在我看來,兩種風格的區別其實不小,你是如何兼顧這兩種風格的寫作的?在寫作時間上,二者會不會交叉進行?在你心中,是否會存在“誰為主誰為輔”“誰守正誰出奇”的考量?
趙志明:我曾經打過一個比喻,叫寫作的蹺蹺板。寫作像蹺蹺板,只走一端必然會導致那一端下沉,不復彈起。兩端同時加碼,則能保持蹺蹺板的平衡。日本的一些小說家一邊寫自己想寫的作品,一邊寫受市場歡迎的作品,很多作家同時寫作小說和詩歌,一些作家熱衷于冒險。我覺得這不是心有旁騖,而是以寫作滋養寫作,讓寫作在寫作者那里不至于陷入千篇一律循環往復的枯燥中。求變存在變數,更是極大挑戰。但寫作畢竟不是尋常意義上的工作,有時候經驗反而是沼澤,更會讓人裹足不前,甚至有沒頂之災的危險。不管是魔幻的上天入地,還是現實的低到塵埃中,風格迥異,但根源是一樣的,相不相信,訴求也是近似的,不僅自己信,還能讓他者信。煞有介事,還是脫不開事的本質。枝繁葉茂,畢竟離不開根基深穩。
李壯:當初第一次讀到《歌聲》《釣魚》《I am Z》等“名篇”,心中真的是會產生某種近乎震撼的感覺。包括現在回過去再讀,也依然會有這種感受。原因就在于,這些小說雖然在篇幅上都很短小,但它們觸及到了人類生存的許多根本性境遇,觸及到了人之為人諸多終極而又無解的關切。說得通俗一些,即便這些故事在情節和經驗內容層面上跟我沒什么交集(我既沒有臥病在床的父親,也沒有釣魚技能),我依然會覺得這篇小說是與我的生命有關的。在今天的文學寫作圖景之中,這樣的作品并不多見。有趣之處在于,你切入這些大問題的入口,似乎都很小。比如《釣魚》一篇,在我看來寫的就是“孤獨”,但你曾經談到,這篇小說的緣起是你想寫寫“狐臭”。從“狐臭”到“孤獨”,這是一種魔法般(甚至也可以說是“史詩般”)的跨越。你是如何做到的?是有意為之嗎?
趙志明:在我遵囑整理這本書的相關篇目時,我發現你說的這幾篇在體量上非常近似,那就是很短小,每篇幾乎都在5000字左右。我當時就想,如果有20篇這樣的短制,結集成冊,我會很滿意,會聯想到《九故事》《米格爾大街》《小城畸人》,還有埃梅、愛·倫坡、卡夫卡等人。具體到《釣魚》中的“狐臭”和“孤獨”,有個源起。在溧陽話中,狐臭稱為“下風”,因為在下風處聞得尤其明顯。“下風”是一種遺傳病,父親或母親有,孩子基本也會有,早年間,汽車站火車站的廁所里貼的大都是治療狐臭的廣告。我姐夫有個朋友,據說就患有狐臭。我們那還有一個說法,比如夫妻、父子,或者親密的朋友,是聞不到對方的狐臭的,這大概是久居鮑魚之肆、不聞其臭的意思。上大學時,我們一群同學在操場打籃球,有時人不夠,也會和其他人組隊,有時候是附近的中學生。有一次一個中學生就指著我的一個同學說,你是不是有狐臭?問得很突兀。其時我那同學打得興起,赤膊上陣,聞言便嗅聞自己的腋下,很鄙視地跟中學生說,你小孩子不懂,這是荷爾蒙的味道。我們笑倒。雖然一直聽到狐臭,但我并沒有真正聞到過,我想寫一個熱愛釣魚的人和他從不釣魚卻患有狐臭的朋友如何交往,寫釣魚的人和家人,這里面更多的是容忍遷就。然后,寫著寫著大魚就出現了,它好像就潛伏在字詞句子組成的河水中,單等時機出現就上鉤,被人像牽一頭牛一樣慢慢靠近村莊。大魚的出現,我才意識到我想寫的是孤獨,是隱藏在河水深處大魚的孤獨。
李壯:在《石中蜈蚣》《無影人》《你的木匠活呵天下無雙》《侏儒的心》等小說之中,我看到了一種強烈的“戲劇性結構”。一個非常漂亮的創意、或者說一對很鮮明很強烈的沖突關系,在文本中起到了最主要的承重作用。這樣“強戲劇結構”的寫法在今天的文壇并不多見,原因可能是寫作者會在此種寫作中遭遇多方面的難題:例如很多作家缺少想象力、虛構力,例如定力不足的寫作者容易被戲劇性拖著行走以致陷入被動,例如戲劇性結構的誕生對寫作者本身的創造性靈感要求極高、故而此種寫作可持續性相對較差,等等。你是否遭遇過這類難題?又是如何克服的?
趙志明:在大學時,我集中讀過一些戲劇、詩劇,從古希臘的悲喜劇,到莎翁、瓦格納、韋伯,還有拜倫和普希金的詩劇,以及荒誕派戲劇等,甚至構思過一個實驗劇本《手套》,但經驗不足,沒有能夠完成。這種嘗試帶來的好處是,在我構思一個小說,或者對某件事進行復構時,經常會預先描摹出一些矛盾沖突點,類似于一條魚的骨架,然后才是把魚鱗一層層鑲嵌上去。但這種方法并不是總能奏效,像《鄉關何處》這篇小說,結構就沒能立起來,其實是坍塌了的。可能這種結構對偏重想象的小說更加有效,因為想象力能夠做到舉重避輕,遇到障礙,完成輕盈一躍。
李壯:《中國怪談》一書里,幾乎都是志怪故事。有些是你的原創,有些則是從民間故事、歷史傳說甚至古代小說中化用改寫而來。你如何定位這些故事?它們是你敘事才華和講述沖動任性噴薄的景觀性成果(瞬間的),還是意味著你未來寫作的又一種方向(持久的)?
趙志明:寫《中國怪談》,源于一次嘗試。我和小說家孫智正協商,既然豆瓣上發表比較自由,我們何不嘗試寫一些好玩有趣的故事。這和我的興趣不謀而合,本來我就聞怪而喜,可以做到過耳不忘。之后,我們就一人寫了一篇,他寫了《禿尾龍》,我寫了《花瓶女》,沒想到還挺受歡迎,這算是鼓勵我堅持寫系列的一個外部激勵。其實,就算不寫《花瓶女》,沒有豆瓣平臺的支持,我也會進行類似的寫作嘗試。在《中國怪談》里面,故事幾乎都是古代背景,語言也是文白相雜,雖然囿于古代知識和古文能力,行文破綻極多,但我是想利用這種訓練來趨近古代的生活和語言,為我的寫作開拓新的出路。我想寫一些中國古代的小說,效法魯迅、王小波和蘇童,但爭取寫出不一樣來。我知道道阻且長,但我不著急,可以慢慢來,哪怕是60歲,能寫出就不算晚。
李壯:很多讀者都喜歡你小說中的事無巨細、不急不緩、娓娓道來。《還錢的故事》是一種典型,它與鄉間生活有關,這種典型很多。《四件套》也是一種典型,它是都市生活題材,這種典型似乎少一點。事實上,就文化氣質而言,都市文化以及都市生活是快速的、焦灼的、節奏不穩定、呼吸不均勻的。想要在都市經驗的領域內,展開你那種娓娓道來的敘事魔術,難度似乎不小。而與此同時,如何處理和展示都市經驗,又是當下小說寫作者要面臨的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都市經驗和都市有關題材,你有什么想法、感受或者說野心、計劃?你固有的寫作策略寫作風格與都市經驗發生碰撞的時候,迸出過哪些不同以往的火花?
趙志明:有時候聽到關于城市小說和鄉土小說的討論,我會啞然失笑。這里面有一個再明顯不過的悖論,假使一個在城市生活描述城市生活的小說家不能稱為城市作家,那在一個鄉村生活過并把鄉村生活寫進作品的小說家為什么就能言之鑿鑿地被視為鄉土作家?胡安·魯爾福寫的很多小說,都和鄉村、土地、土地上的人有關,我從來不覺得他是鄉土作家。卡夫卡,誰能告訴我,他寫的是城市還是鄉村?因此,我傾向于認為,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是一個場域,類似戲劇舞臺,在上面既可以上演基督山伯爵和王子復仇記,也可以上演白毛女和小二黑結婚。時代偏重哪里側重表現什么人物,就會在典型上體現出來。這是時代的鮮明印記,也是對時代的一種反向迎合。但是,小說家作為自由的崇尚獨特的個體,會謹守自己的寫作準則,對我來說,不會為了寫而寫,不易冒進,也盡量避免用力過猛。我非常喜歡金宇澄的《繁花》,視其為具有代表性的成功的城市小說。因為,至少我反復讀之,沒有在里面發現令人可疑的個人經驗,取而代之的是他人經驗,是時代使然。換言之,假使說現在都市題材的小說乏善可陳,那是源于很多作者急于把自己的個人經驗強行塞進去,以為城市的就是城市的,殊不知這些經驗乏善可陳,來歷不明,而且更加站不住腳。在更年輕的寫作者那里,這些問題可能就會不攻自破,因為他們有了真實的對城市的體驗,并且不會輕易被假象所迷惑,或者對自己的寫作欲望望風披靡。
李壯:在你眼中,小說家最理想的寫作狀態是怎樣的?對于未來的生活和寫作,你有什么樣的規劃?
趙志明:小說家最理想的寫作狀態是不是就是從寫作中脫縛,和寫作達成平等的關系?比如說,恪守工匠式寫作,每天像上班一樣寫作,寫出固定的字數,并且質量上乘,完全匹配自己對寫作的虔誠和野心。但是這需要強大的毅力,而且需要源源不斷的才華提供支持。我不否認通過訓練可以提高寫作的能力,但前提應該是適合寫作,具有起碼的寫作才華。我絕對不相信,一個人從會走路時就開始練習踢足球,到了十幾歲就能具有梅西的水平,或者接近40歲還能像伊布那樣攻城拔寨。如果說,我確實能夠勝任寫作,并值得有所期待,我自然會希望在寫作道路上不斷精進。畢竟,在我身邊這樣的師友比比皆是,像閻連科、韓東、于堅、李宏偉、劉汀、馬拉,他們在寫作上的嚴格、勤奮、多產,每每讓我汗顏。我也希望像他們那樣,和寫作的關系越來越平等,越來越自如。就好像高僧,能夠如常地對頑石講經,也好像武林絕頂高手,摘花飛葉,取勝如探囊取物。我希望能踏上更高一級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