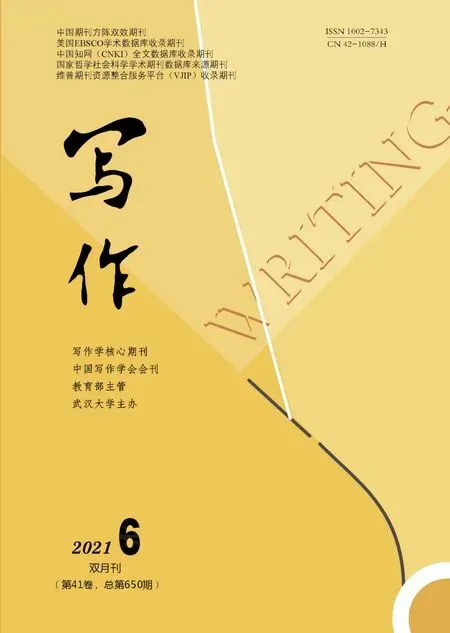中國(guó)現(xiàn)代散文語言的典范:京派散文的語言形象
陳 嘯
在現(xiàn)代漢語界,語言(language)被具體分為“語言”(language,語言系統(tǒng)或代碼)、“言語”(parole,個(gè)人的說話或信息)和“話語”(discourse,單個(gè)說話者的連續(xù)的信息傳遞或具有相當(dāng)完整單位的本文)等。海德格爾說語言是人的存在之域①參見[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shí)間》,陳嘉映、王慶節(jié)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版,第203頁。。而文學(xué)的語言則不僅具有言語或話語組織的本來之意,而且還包括獨(dú)特的文體及各種修辭的手段。“形象”意指藝術(shù)中由符號(hào)表意系統(tǒng)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能顯示事物深層意義之想象的具體可感物。語言形象則是指文學(xué)作品的具體話語組織所呈現(xiàn)出的,富有作者獨(dú)特個(gè)性魅力的語言形態(tài),也即如何再現(xiàn)語言的形象問題。京派散文語言形象作為現(xiàn)代“中國(guó)語言形象”②參見王一川:《中國(guó)形象詩學(xué)》,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在審美表達(dá)中,內(nèi)在且不同程度地再現(xiàn)著中國(guó)現(xiàn)代整體性及中國(guó)現(xiàn)代藝術(shù)性等不同方面,具有著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審美與文化的多重內(nèi)涵。
一、反復(fù)“摶弄”
京派散文的語言給人的整體感,也即第一感覺是“陌生化”。根據(jù)俄國(guó)形式主義理論,“陌生化”就是在描寫一事物時(shí),不用指稱及識(shí)別之方法,而用一種非指稱、非識(shí)別的仿若首次見到這事物而不得不進(jìn)行描寫的方法。京派散文陌生化的語言就如汪曾祺所謂的“揉面”③汪曾祺:《“揉面”——談?wù)Z言》,《花溪》1982年第3期。,將古今中外、方言土語以及不規(guī)范的言語和自造詞放在一起,下筆之前反復(fù)摶弄。化為自己的血肉,鑄成作品的筋骨,以爐錘之功或化腐朽為神奇,或點(diǎn)鐵成金,或匠心獨(dú)具,或秀外慧中……一詞一句,痛癢相關(guān),互相映帶,姿勢(shì)橫生,氣韻生動(dòng),璀璨奪目,妙趣橫生。這就是中國(guó)人常講的“文氣”。要之如下:
(一)古語鑲嵌
京派散文行文,非純粹的現(xiàn)代漢語方式,時(shí)或古今糅合,在保持現(xiàn)代漢語為基本的前提下,常于局部鑲?cè)牍艥h語的詞匯、詞語組合、從句、修辭術(shù)等,巧妙地?fù)慌c糅合,化為自己的血肉,形成古今對(duì)話之新格局,沒有絲毫的生硬拼貼、非驢非馬之感。意義豐富,促人聯(lián)想,言簡(jiǎn)意賅,半文半白,古色古香,明白無誤。如廢名《菱蕩》中的描寫段落:“塔不高,一大楓樹高其上,遠(yuǎn)行人歇腳乘涼于此。于樹下,可觀菱蕩圩。不大,花籃狀,但無花,從底綠起。若蕎麥或油菜花開之時(shí),便盡是花了。稻田,樹林堆成許多球,城里人不能一一說出,村、園,或池塘四周栽了樹,樹比之圩更來得小,走路是在樹林里走了一圈。除陶家村及其對(duì)面一小廟。時(shí)或聽斧斫樹響,但不易見。小廟白墻,深藏到晚半天,此地首先沒有太陽,深。有人認(rèn)為是村廟,因其小,城里人有終其身沒向陶家村人問過此廟者,也沒再見過這么白的墻。”①吳福輝編選:《京派小說選》,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頁。語言干凈,短句居多,時(shí)或以“其”“于”“之”等文言詞匯穿插其間,古雅利落,清爽干脆。
李廣田的《山水》行文基本都是以現(xiàn)代漢語娓娓述說自己如何因讀“先生”之山水的文章而生平原之子的欣羨、寂寞與悲哀,并以一個(gè)平原之子的心情訴說多山之地的缺陷和不足,同時(shí)想起自己故鄉(xiāng),以及平原的子孫對(duì)一洼水一拳石的喜歡和身處平原之地對(duì)遠(yuǎn)方山水的想象,并述說自己的祖先如何來此平原,如何改造平原。最后總結(jié)說,這是一個(gè)大謊,因?yàn)槭且豁摎v史,簡(jiǎn)直是一個(gè)故事。“那里仍是那么坦坦蕩蕩,然而也仍是那么平平無奇,依然是村落,樹木,五谷,菜畦,古道行人,鞍馬馳驅(qū)。”“我在那平原上生長(zhǎng)起來,在那里過了我的幼年時(shí)代,我憑了那一塊石頭和幾處低地,夢(mèng)想著遠(yuǎn)方的高山,長(zhǎng)水,與大海。”②李廣田:《李廣田全集》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223頁。而中段部分寫祖先對(duì)平原的改造即穿插了大段的古語描述,幾近于文言文述說。請(qǐng)看:“以己之力,改造天地,開始一偉大工程,鑿成一道大川流。從此以后,我們祖先才可以垂釣,可以泅泳,可以行木橋,可以駕小舟,可以看河上的煙云。我們的祖先仍是覺得不夠好還要在平地上起一座山岳。用一切可以盛土的東西,運(yùn)村南村北之土于村西,又把那河水引入村南村北的新池,于是一曰南海,一曰北海,山是土的,于是采西山之石,南山之木,進(jìn)而成為:峰巒秀拔,嘉樹成林,年長(zhǎng)日久,山中梁木柴薪,不可勝用,珍禽異獸,亦時(shí)來?xiàng)梗虾1焙#嘧贼~鱉蕃殖,萍藻繁多,夜觀漁舟火,日聽采蓮歌。”③李廣田:《李廣田全集》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223頁。大量的文言字詞與四字句,讀之朗朗上口,古色古香,亦增強(qiáng)了語言的節(jié)奏感。
梁遇春的《春雨》在表述自己喜歡春雨、喜歡春陰以及厭惡晴朗日子的原因時(shí),于基本的現(xiàn)代漢語表述中,也時(shí)或有古漢語表達(dá)方式,或引用,或化用,讀來古雅:“我向來厭惡晴朗的日子,……陰里四布或者急雨滂沱的時(shí)候,就是最沾沾自喜的財(cái)主也會(huì)感到苦悶,因此也略帶了一些人的氣味,……至于懂得人世哀怨的人們,黯淡的日子可說是他們唯一光榮的時(shí)光。穹蒼替他們流淚,烏云替他們皺眉,他們覺到四周都是同情的空氣,……‘最難風(fēng)雨故人來’,……‘風(fēng)雨如晦,雞鳴不已’,人類真是只有從悲哀里滾出來才能得到解脫,……‘山雨欲來風(fēng)滿樓’,這很可以象征我們孑立人間,嘗盡辛酸,遠(yuǎn)望來日大難的氣概,真好像思鄉(xiāng)的客子拍著闌干,看到郭外的牛羊,想起故里的田園,懷念著宿草新墳里當(dāng)年的竹馬之交,淚眼里仿佛模糊辨出龍鐘的老父蹣跚走著,或者只瞧見幾根靠在破壁上的拐杖的影子。……臨風(fēng)的征人,……無論是風(fēng)雨橫來,無論是澄江一練,始終好像惦記著一個(gè)花一般的家鄉(xiāng),那可說就是生平理想的結(jié)晶,蘊(yùn)在心頭的詩情,也就是明哲保身的最后堡壘了;……‘小樓一夜聽風(fēng)雨’,……喜歡冥想春雨,也許因?yàn)槲覍?duì)于自己的愁緒很有顧惜愛撫的意思;我常常把陶詩改過來,向自己說道:‘衣沾不足惜,但愿恨無違’。”①載《新月》1932年11月1日第4卷第5號(hào),署秋心遺稿。
(二)融外化生
京派文人通曉古今,博貫中西,在語言操作中,常常能夠不自覺地移植現(xiàn)代主義甚至后現(xiàn)代主義的外語詞匯、詞語甚至句法,巧妙地為我所用,將文言、現(xiàn)代口語、西化語完美化生。典型的如林徽因《蛛絲和梅花》中:“同蛛絲一樣的細(xì)弱,和不必需,思想開始拋引出去:由過去牽到將來,意識(shí)的,非意識(shí)的,由門框梅花牽出宇宙,浮云滄波蹤跡不定。是人生,藝術(shù),還是哲學(xué),你也無暇計(jì)較,你不能制止你情緒的充溢,思想的馳騁,蛛絲梅花竟然是瞬息可以千里!……就在這里,忽記起梅花。一枝兩枝,老枝細(xì)枝,橫著,虬著,描著影子,噴著細(xì)香;太陽淡淡金色地鋪在地板上;四壁琳瑯,書架上的書和書簽都像在發(fā)出言語;……你斂住氣,簡(jiǎn)直不敢喘息,巔起腳,細(xì)小的身形嵌在書房中間,看殘照當(dāng)窗,花影搖曳,你像失落了什么,有點(diǎn)迷惘。又像‘怪東風(fēng)著意相尋’有點(diǎn)兒沒主意!浪漫,極端的浪漫。‘飛花滿地誰為掃?’你問,情緒風(fēng)似地吹動(dòng),卷過,停留在惜花上面。再加減看看,花依舊嫣然不語。”②林徽因:《蛛絲和梅花》,天津《大公報(bào)·文藝副刊》1936年2月2日第86期。古典秀麗,色彩斑斕,中西合璧,色味俱全,給人一種浪漫而迷麗的感覺。
(三)以俗現(xiàn)美
京派文人多來自鄉(xiāng)間,鄉(xiāng)間日常生活習(xí)用的語言以及內(nèi)在的語言精神,也常常成其為散文語言的妝飾和內(nèi)在的神韻。代表性的如蕭乾,常常在散文中使用一些漢語區(qū)域內(nèi)大致都能懂的北京地方話,即所謂的“藍(lán)青官話”,同時(shí)把北京鄉(xiāng)土文化特有的“雅”幽默情趣浸潤(rùn)其間,使得語言鮮活、風(fēng)趣、精辟、深刻,雅俗共賞。譬如《過路人》(1934年5月)寫自己一次坐船的經(jīng)歷:天剛亮,船進(jìn)港,漸漸,“我”讀到巍峨建筑上的字:洋行,洋行,橫濱的,紐約的,世界各地機(jī)警的商人全鉆到這兒來了。“好一條爬滿了虱子的炕!”③蕭乾:《蕭乾全集》第4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頁。精彩比喻的背后隱藏著幽默。嚴(yán)肅之事以詼諧、滑稽的用語喻之,使人在低迷的微笑中獲得雅化的情緒體驗(yàn)。同一文本中還有:“汽車多啊,多得像家鄉(xiāng)池塘雨后的蜻蜓。費(fèi)了老大氣力提煉成的汽油全在馬路上變成一陣臭煙了。那煙還得通過人們的五臟。”④蕭乾:《蕭乾全集》第4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頁。雍容之事以嘲弄、揶揄的語調(diào)寫,豐富了語言的表現(xiàn)力,讓人產(chǎn)生一種會(huì)心的微笑。林徽因的散文同樣有著北京特有的雅幽默意味。如《窗子以外》中,寫兩個(gè)婦人與伙計(jì)爭(zhēng)秤,“必是非同小可,性命交關(guān)的貨物”“必定感到重大的痛苦”;寫坐車過站的老太太挾著行李,“是在用盡她的全副本領(lǐng)的”;寫她突聞村落之人為明慶王的后人,“這下子文章就長(zhǎng)了”“這樣一來你就有點(diǎn)心跳了”⑤林徽因:《窗子以外》,天津《大公報(bào)·文藝副刊》1934年9月5日第99期。,平常之事以嚴(yán)肅、夸張的口吻寫之,使語言本身蘊(yùn)涵著沖突,逸出了文字本身的語義。“雅”幽默背后深隱的是深刻的文化知識(shí)基礎(chǔ),是無足輕重的東西中深刻的意義和精神的閃光。沈從文的語言整體上皆為湘西水上的言語。此種語言雖來自鄉(xiāng)民,但已“面目全非”,它拋卻了鄉(xiāng)民口語中的那種緣于種種原因及基本精神而與全民族語言結(jié)構(gòu)不相符合的如偶然、臨時(shí)、非鞏固、含糊及發(fā)音不正等的部分。如:“我一個(gè)人坐在灌滿冷氣的小小船艙中”的“灌”字(《箱子巖》)⑥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247頁。,“把鞋脫了還不即睡,便鑲到水手身旁去看牌”的“鑲”字(《鴨窠圍的夜》)⑦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247頁。等,真實(shí)、質(zhì)樸、形象,富有動(dòng)人的生活情趣,以俗現(xiàn)美。沈從文的文學(xué)語言整體上格調(diào)古樸,句式簡(jiǎn)峭、主干凸顯,單純而又厚實(shí),樸訥而傳神,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凸現(xiàn)出鄉(xiāng)村人性特有的風(fēng)韻與神采。
京派散文還常常以詞類的活用等違反常規(guī)之手法使語言產(chǎn)生陌生化的效果,如廢名的《沙灘》中“草更不用說除了踏出來的路只見它在那里綠”①廢名:《廢名散文選》,馮健男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頁。中的“綠”字以及沈從文的《湘行書簡(jiǎn)·過新田灣》中“我好像智慧了許多,溫柔了許多”②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頁。中的“智慧”一詞,即為形容詞活用為動(dòng)詞。
二、譬喻奇警
京派散文有著濃濃的“詩質(zhì)”。其實(shí),京派文人很多就是詩人,而詩人寫作幾乎沒有不用比喻的。這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比喻”成為京派散文的一個(gè)顯著的文體特征。京派散文的比喻精當(dāng)貼切,垂手天成,自然奇警。溫而雅,皎而朗,譬喻引類,幻擬心理,能量無比,著眼環(huán)境,揭示本質(zhì)。
如何其芳的《墓》中:“快下山的夕陽如溫暖的紅色的唇。”夕陽喻示著美好和短暫,紅色的唇代表著溫暖的愛情,把“夕陽”比喻成“溫暖的紅色的唇”,易于產(chǎn)生對(duì)愛的悵惘與失去愛的凄惶、失落、哀悼之情。“他們散步到黃昏的深處,散步夜的陰影里。夜是怎樣一個(gè)荒唐的紫語的夢(mèng)啊。”以“荒唐的紫語的夢(mèng)”比喻“夜”,充分感覺化了,“荒唐”一詞是“我”的感覺,是“我”撫今追昔,痛定思痛,哀惋凄切等情感的外化,以“紫語的夢(mèng)”極言過去美好時(shí)日的蒼涼、幽暗、遙遠(yuǎn)、空幻。“夕陽如一枝殘忍的筆在溪邊描出雪麟的影子,孤獨(dú)的,瘦長(zhǎng)的。”③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4、86頁。把“夕陽”比喻成“殘忍的筆”,情感化,形象化,“夕陽”本身就容易讓人產(chǎn)生一種蒼涼、憂郁、孤獨(dú)、寂寥的感覺,再施之于“殘忍”一詞,更進(jìn)一步突出雪麟的孤獨(dú)與憂郁。《秋海棠》中:“庭院是靜靜的。仿佛聽得見夜是怎樣從有蛛網(wǎng)的檐角滑下,落在花砌間纖長(zhǎng)的飄帶似的蘭葉上,微微的顫悸,如剛棲定的蜻蜓的翅,最后靜止了。夜遂做成了一湖澄凈的柔波,停潴在庭院里,波面浮泛著青色的幽輝。”④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4、86頁。把無可言之靜夜動(dòng)態(tài)化、形象化,先細(xì)致描述“夜”從檐角滑下,落于蘭葉上,這分明是觀察者主體的內(nèi)心感覺,突出了主體的靜、思、寂寥、孤獨(dú),同時(shí)把“夜”又寫活了,可感可觸可觀,這其實(shí)都是主體的思緒在動(dòng)。“夜”如蜻蜓的翅膀、一湖澄凈的柔波,又是極言“夜”的靜謐、美妙,但這一切都是在突出主體的幽孤,對(duì)“夜”的比喻其實(shí)也是對(duì)思婦主體的形容。“夜的顏色,海上的水霧一樣,香爐里氤氳的煙一樣的顏色,似尚未染上她沉思的領(lǐng)域,她仍垂手低頭的,沒有動(dòng)。但,一縷銀的聲音從階角漏出來,尖銳,碎圓,帶著一點(diǎn)陰濕,仿佛從石的小穴里用力的擠出,珍珠似的滾在飽和著水澤的綠苔上,而又露似的消失了。沒有繼續(xù),沒有賡和。孤獨(dú)的早秋的蟋蟀啊。”⑤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4、86頁。這里把蟋蟀的聲音比喻成銀樣的聲音,然后再以“尖銳”“碎圓”等充分物質(zhì)的形容詞述之,以用力的“擠”出,珍珠似的“滾”在飽和著水澤的綠苔上……其實(shí),把蟋蟀聲音的強(qiáng)化、物質(zhì)化,意在突顯思婦主體孤獨(dú)感覺的強(qiáng)化、物質(zhì)化。“這初秋之夜如一襲藕花似的蟬翼一樣的紗衫,飄起淡淡的哀愁。”⑥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4、86頁。把虛空之“夜”比喻成可觸可感的蟬翼樣的紗衫,“夜”成了實(shí)體化、美妙化了的感情載體。“她素白的手撫上了石闌干。一縷寒冷如纖細(xì)的褐色的小蛇從她的指尖直爬入心的深處,徐徐的紆旋的蜷伏成一環(huán),尖瘦的尾如因得到溫暖的休憩所而翹顫。”⑦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4、86頁。把寒冷的感覺比喻成褐色的小蛇,陌生化、物質(zhì)化、恐怖化、形象化,重情感的相似性。“就在這鋪滿了綠苔,不見砌痕的階下,秋海棠茁長(zhǎng)起來了。兩瓣圓圓的鼓著如玫瑰頰間的酒渦,兩瓣長(zhǎng)長(zhǎng)的伸張著如羨慕昆蟲們飛游的翅,葉面是綠色的,葉背是紅的,附生著茸茸的淺毛,朱色莖斜斜的從石闌干的礎(chǔ)下擎出,如同擎出一個(gè)古代的甜美的故事。”⑧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4、86頁。想象化、感覺化、聯(lián)想化、引申化的比喻,拓寬了理解空間,豐滿,圓潤(rùn),溫厚,蘊(yùn)藉。《雨前》中:“一點(diǎn)雨聲的幽涼滴到我憔悴的夢(mèng)。”⑨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4、86頁。自然界的雨聲賦予擬人化、情感化的幽涼,自我的玄想比之為夢(mèng),頗渲染出一種迷離恍惚、凄切、悵惘之感。《遲暮的花》中:“在你的眼睛里我找到了童年的夢(mèng),如在秋天的園子里找到了遲暮的花……”①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121頁。情感的牽連,相似性、相關(guān)性、陌生化的比喻,把對(duì)青春的傷感,對(duì)純潔愛的孤獨(dú)的呼喚,形象昭示。《貨郎》中:“于這些大宅第,他(指貨郎)象一只來點(diǎn)綴荒涼的候鳥,并且一年不止來一次”②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121頁。,此一烘托性的比喻,恰似那“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之功效,更突出和昭示出大宅第的荒涼、古舊、冷清。
汪曾祺《牙疼》:“牙疼若是畫出來,一個(gè)人頭,半邊慘綠,半片熾紅,頭上密布古象牙的細(xì)裂紋,從脖子到太陽穴扭動(dòng)一條斑斕的小蛇,蛇尾開一朵(什么顏色好呢)的大花,牙疼可創(chuàng)為舞,以黑人祭天的音樂伴奏,哀楚欲絕,低抑之中透出狂野無可形容。”③汪曾祺:《牙疼》,《文學(xué)雜志》1947年9月第2卷第4期。比喻感覺化,感覺物質(zhì)化、形象化、幽默化,可觸可感可思可想,且充滿著豐厚的文化想象。師陀《還鄉(xiāng)——掠影記》中寫西方楚先生回鄉(xiāng)尋夢(mèng)卻失落:“西方楚先生感到一點(diǎn)不同,同時(shí)又覺得沒有什么兩樣,也說不出自己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那不是哀傷,不是痛苦,不是失望,也不是細(xì)碎的紛亂,而是咸水魚游到淡水里的極輕微的不適。”④蘆焚:《還鄉(xiāng)——掠影記》,《文叢》1937年第1卷第3期。蘆焚即師陀。把不可言明之情緒以類似的物象喻之,形象明了,含蓄蘊(yùn)藉,耐人回甘。
比喻是語言藝術(shù)中的藝術(shù),具有一種奇特的力量。多彩的比喻,使京派散文詩情蘊(yùn)藉,回味無窮,也成為京派散文文體的一個(gè)顯在標(biāo)識(shí)。
三、行文似繪
京派散文行文似繪,繪畫中的各種技巧及藝術(shù),比如空間藝術(shù),皴染烘托及映照生輝的主次藝術(shù)、白描藝術(shù)、光線藝術(shù)以及色彩的搭配等,很多都被京派文人創(chuàng)造性地移用于散文創(chuàng)作,有著精妙的呈現(xiàn)。以沈從文《桃源與沅州》中對(duì)白燕溪的描寫為例:“沅州上游不遠(yuǎn)有個(gè)白燕溪,小溪谷里生芷草,到如今還隨處可見。這種蘭科植物生根在懸崖罅隙間,或蔓延到松樹枝椏上,長(zhǎng)葉飄拂,花朵下垂成一長(zhǎng)串,風(fēng)致楚楚。花葉形體較建蘭柔和,香味較建蘭淡遠(yuǎn)。游白燕溪的可坐小船去,船上人若伸手可及,多隨意伸手摘花,頃刻就成一束。若崖石過高,還可以用竹篙將花打下,盡它墮入清溪洄流里,再用手去溪里把花撈起。除了蘭芷以外,還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邊崖下繁殖。那種黛色無際的崖石,那種一叢叢幽香眩目的奇葩,那種小小洄漩的溪流,合成一個(gè)不可言說迷人心目的圣境!”⑤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頁。整個(gè)白燕溪在作者筆下就似一幅中國(guó)水墨畫。畫面的中心和顯要位置是芷草,長(zhǎng)葉飄拂,形象楚楚。芷草的周圍則飾以多樣的香草香花,為襯托賓者地位,描寫也較芷草渺茫不清。芷草及各種香花香草的背景則是高的黛色懸崖,下配以清淡的小船及船中人伸手摘花,用竹篙打花,清流里撈花,等等,整幅畫面,有主有次,多少、藏露、濃淡合宜且相生相應(yīng)。
再比如廢名《沙灘》一文中對(duì)史家莊的描寫:“站在史家莊的田坂當(dāng)中望史家莊,史家莊是一個(gè)‘青’莊。三面都是壩,壩腳下竹林這里一簇,那里一簇。樹則沿壩有,屋背后又格外的可以算得是茂林。草更不用說除了踏出來的路只見它在那里綠。站在史家莊的壩上,史家莊,史家莊被水包住了,而這水并不是一樣的寬闊,也并不處處是靠著壩流。每家有一個(gè)后門上壩,在這里河流最深,河與壩間一帶草地,是最好玩的地方,河岸盡是垂柳。迤西,河漸寬,草地連著沙灘,一架木橋,到王家灣,到老兒鋪。”⑥廢名:《廢名散文選》,馮健男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頁。整幅畫面采用的是兩個(gè)觀察點(diǎn)的散點(diǎn)透視,分別從史家莊的田坂當(dāng)中和史家莊的壩上,遠(yuǎn)景掃描,而畫面的中心是史家莊。通過兩個(gè)觀察點(diǎn),由近及遠(yuǎn)依次展開了史家莊周圍的畫面:壩圍以內(nèi),處處竹林、茂樹、青草等等,把史家莊點(diǎn)綴成一個(gè)“青”莊。壩圍以外,河流、垂柳、木橋等等,則把史家莊裝扮成一個(gè)詩意的水的世界。文本除了精心營(yíng)構(gòu)空間藝術(shù)而外,還化用了唐代王維以來中國(guó)繪畫慣用的皴染烘托、映照生輝藝術(shù)。此一藝術(shù)本為畫家用水墨或淡彩在物象的外廓渲染補(bǔ)托,使其藝術(shù)形象鮮明突出的一種藝術(shù)手法。宋代山水畫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一書中說:“山欲高,盡出之則不高;煙霞鎖其腰則高矣。水欲遠(yuǎn),盡出之則不遠(yuǎn),掩映斷其脈則遠(yuǎn)矣。”①郭熙:《林泉高致》,梁燕注譯,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頁。清代畫家笪重光在《畫筌》中說:“山本靜,水流則動(dòng);石本頑,有樹則靈。”②笪重光:《畫筌》,關(guān)和璋譯解、薛永年校訂,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頁。廢名寫史家莊,不重實(shí)寫史家莊內(nèi)部如何如何,而是寫它的外圍之竹之林之草之水之柳之橋等,通過外圍之景,烘托出一個(gè)詩意的史家莊。
“白描”,原是中國(guó)畫技法之一,源于古代的“白畫”,指僅用墨線勾描物象而不著或少著顏色的技法。在古典小說中,“白描”手法也用來指以最簡(jiǎn)練的筆墨不加烘托地描繪形象以達(dá)到傳神的目的。可以說,古代白描語言的基本精神在于以簡(jiǎn)練筆墨或素淡筆墨描摹事物的本相,意于“神似”而非“形似”。“掃去粉黛,輕毫淡墨”,“不施丹青而光彩動(dòng)人”。③朱鑄禹編纂:《唐宋畫家人名辭典·李公麟》,北京:中國(guó)古典藝術(shù)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頁。即魯迅先生所謂的:“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而已。”④魯迅:《作文秘訣》,《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7年版,第474頁。無中生有、虛中見實(shí)、以形寫神、以少總多、氣韻生動(dòng)、客觀真實(shí)、質(zhì)樸傳神等中國(guó)古典文化核心概念是其主要美學(xué)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京派散文語言的“白描”屬于現(xiàn)代性的白描,是在現(xiàn)代白話語言整體中限制性地吸收了白描語言的以形寫神、以少總多及意境等美學(xué)“形式”,揚(yáng)棄了諸如古典宇宙觀和美學(xué)精神及文化意韻等的傳統(tǒng)的“內(nèi)容”。京派散文現(xiàn)代性的白描,典型表現(xiàn)在意境的創(chuàng)造上,它已經(jīng)不似單純的中國(guó)古典文論中由王昌齡的“心中了見”,釋皎然的“但見性情,不睹文字”,以至劉禹錫的“境生于象外”及司空?qǐng)D的“韻外之致”“味外之旨”等的以道、禪之說揭示的“幽渺以為理,想象以為事,惝恍以為情”“得其環(huán)中,超以象外”的“意境”說的美學(xué)本質(zhì),而是帶有了現(xiàn)代理性的思考。如沈從文《湘行書簡(jiǎn)·夜泊鴨窠圍》一文中對(duì)鴨窠圍的描寫,這里吸取了古代白描以少總多、臨境生情的古典神韻,但顯然也趨向于一個(gè)分析的體系,超越完全感性和經(jīng)驗(yàn)的世界,追求一個(gè)體驗(yàn)和恒久的真理世界。沈從文在這里所要表達(dá)的已不僅僅是湘西那種人與自然和諧融合、與“道”合一的高遠(yuǎn)境界,同時(shí)更多帶有了現(xiàn)代的理性思考。沈從文關(guān)注的已不是現(xiàn)象本身的意義,即超越了“天人合一”的物我合一精神境界,開始尋找現(xiàn)象背后的本原和認(rèn)識(shí)論的知識(shí)。
線性與非線性敘述的交融也是京派散文白描手法現(xiàn)代性表現(xiàn)的重要方面。所謂線性敘述,即是指那種由遠(yuǎn)而近、自上而下、從大到小、先物后人的講述方式,是對(duì)古代文學(xué)敘述方式的概括。線性敘述的內(nèi)在根據(jù)是中國(guó)古典宇宙觀:人生存于宇宙整體之中,與之同流依存,卻又能以開放之心靈及流動(dòng)之目光作遠(yuǎn)近、大小、上下、物我間的仰觀俯察,感受其生動(dòng)氣韻,并因此發(fā)現(xiàn)到人本身所存于其中的宇宙的線性特征,以及人與自然的循環(huán)往復(fù)、“氤氳化生”的生動(dòng)畫卷與深長(zhǎng)韻味。其所蘊(yùn)涵的顯然不僅僅是語言的本身,但這種線性敘述卻成為中國(guó)古典詩、詞、小說、繪畫的一個(gè)重要美學(xué)特征,是中國(guó)古典文化傳統(tǒng)的一個(gè)表征。由遠(yuǎn)而近、自上而下、從大到小、自物到人的線性敘述,表現(xiàn)在語言組織上即是白描,以簡(jiǎn)潔素樸傳神為要。京派散文的白描語言突破了線性敘述的單一限制,是線性與非線性敘述的交融,形成古代語言和現(xiàn)代語言的雜語喧嘩格局。
以何其芳的散文《墓》為例。文本的開頭,對(duì)鈴鈴之墓周圍環(huán)境的渲染所遵循的大致是線性敘述:初秋的薄暮,翠巖的橫屏環(huán)擁著草地,高大的柏樹,幽冷的清溪,阡陌高下的田畝,黃金稻穗的波浪,柔和的夕陽,等等,共同組成了一派清幽凄冷的從大而小、從上而下、由遠(yuǎn)而近的環(huán)境。
接著敘述了相較完整的三個(gè)片段:1.鈴鈴十六載寂寞而快樂的成長(zhǎng)過程。2.鈴鈴的期待與希冀及短暫的生命。3.雪麟的“獨(dú)語”。完全是跳躍式的心理寫實(shí),并具體采用了印象式、意識(shí)流、蒙太奇等現(xiàn)代性手法。
片段1:作者一任意識(shí)的流動(dòng),詩意敘述了鈴鈴過去的生命:那“茅檐”“泥蜂做窠的木窗”“羊兒的角尖”濯過其手,回應(yīng)過其寂寞的搗衣聲的池塘是她過去生活的環(huán)境;“她的眼睛、頭發(fā)、油黑色的皮膚,時(shí)或微紅的臉頰、雙手,照過她影子的溪水會(huì)告訴你”①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頁。;她的善良、和氣、謙卑,“親過她足的山草,被她用死了的蜻蜓宴請(qǐng)過的小蟻”等會(huì)告訴你;“她會(huì)天真地對(duì)著一朵剛開的花或照進(jìn)她小窗的星星尋索一個(gè)快樂或悲哀的故事”②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頁。。農(nóng)事忙時(shí),她會(huì)給她的父親送飯到田間;蠶子出卵之際,她會(huì)小心地經(jīng)營(yíng)著蠶事;她會(huì)同母親一起,收割屋后的麻,績(jī)成圈圈的紗;她有一個(gè)祖母?jìng)飨碌男∈旨徿嚒诩拍目鞓防镩L(zhǎng)大。
片段2:她常常以做夢(mèng)似的眼睛迷漠地望著天空或是遼遠(yuǎn)的山外;她有些許的憂愁于眉尖,傷感在心頭;她緊握著卻又放開手嘆一口氣地讓每一個(gè)日子過去,她病了;秋天的豐碩依舊,鈴鈴卻瘦損了。黑暗遮到她眼前,無聲的靈語吩咐她休息。
片段3是對(duì)雪麟的描寫:他有鈴鈴一樣郁郁而迷漠的眼神,他是鈴鈴期待的。雪麟見了鈴鈴的小墓碑,便躑躅在這兒的每一個(gè)黃昏里,猜想著這女郎的身世、性情、喜好。于是一個(gè)黃昏里他遇見了這女郎,他向她訴說著外面的世界及美麗的鄉(xiāng)土;他給她講《小女人魚》的故事,向她訴說著愛的癡迷……
顯然,三個(gè)片段又分別由更小的片段與所要表達(dá)的中心片段串聯(lián)組接,而一個(gè)個(gè)小的片段基本上都是作者內(nèi)心的獨(dú)白、自由聯(lián)想、現(xiàn)實(shí)與虛構(gòu)等心理意識(shí)內(nèi)容,這種心理意識(shí)突破了時(shí)間與空間為序的傳統(tǒng),將過去、現(xiàn)在、未來時(shí)序顛倒和空間相互交錯(cuò)、滲透,重視表現(xiàn)式的主體因素對(duì)客體的滲透,追求心靈的寫實(shí)化。同時(shí),心理意識(shí)的內(nèi)容又多是寫意的、感覺化的、碎片化的、印象式的內(nèi)容。
京派散文很重視語言的色彩,但不完全同于繪畫中對(duì)色彩的運(yùn)用,有著自己獨(dú)特的創(chuàng)造。具體表現(xiàn)為:有時(shí)為了強(qiáng)調(diào)色彩美,往往運(yùn)用各種色彩涂抹周圍一切物象,呈色彩斑斕之韻調(diào)。如何其芳的《墓》(1933年)中對(duì)初秋的薄暮描寫:“翠巖的橫屏環(huán)擁出曠大的草地,有常綠的柏樹作天幕,曲曲的清溪流瀉著幽冷。以外是碎瓷上的圖案似的田畝,阡陌高下的毗著,黃金的稻穗起伏著豐實(shí)的波浪,微風(fēng)傳送出成熟的香味。黃昏和晚汐一樣淹沒了草蟲的鳴聲,野蜂的翅。快下山的夕陽如柔和的目光,如愛撫的手指從平疇伸過來,從樹葉探進(jìn)來,落在溪邊的一個(gè)小墓碑上,摩著那白色的碑石,仿佛讀出上面鐫著的朱字:柳氏小女鈴鈴之墓。”③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頁。作者所見到的一切都賦之于顏色,產(chǎn)生油畫般的效果。
有時(shí)則帶上濃烈個(gè)人的情感色彩,作者對(duì)色彩的選取與調(diào)配有時(shí)甚至有絕對(duì)的支配權(quán),流露出鮮明的主體情感的痕跡。如何其芳《秋海棠》(1934年)中的一段:“景泰藍(lán)的天空給高聳的梧桐勾繪出團(tuán)圓的大葉,新月如一只金色的小舟泊在疏疏的枝椏間。粒粒星,懷疑是白色的小花朵從天使的手指間灑下來,而碎寶石似的凝固的嵌在天空里了。但仍閃跳著,發(fā)射著晶瑩的光,且從冰樣的天空里,它們的清芬無聲的霰雪一樣飄墮。”①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頁。由于作者所要表達(dá)的主觀感情是一種憂郁和傷感,故在色彩的選擇上也是冷色調(diào)為主導(dǎo)。景泰藍(lán)的天空、金色的新月、白色的小花似的粒粒星……都給人一種蒼涼和冰樣的感覺,與主體的情思相映襯。沈從文《鴨窠圍的夜》中:“河面上一片紅光,古怪聲音也就從紅光一面掠水而來。原來日里隱藏在大巖石下的一些小漁船在半夜前早已悄悄地下了欄江網(wǎng),到了半夜,把一個(gè)從船頭伸出水面的鐵兜,盛著熊熊烈火的油柴,一面用木棒槌有節(jié)奏地敲著船舷各處漂去。身在水中見了火光而來與受了柝聲吃驚四竄的魚類,便在這種情形中觸了網(wǎng),成為漁人的俘虜。……這時(shí)節(jié)兩山只剩一抹深黑,賴天空微明為畫出一個(gè)輪廓。但在黃昏里看來如一種奇跡似的,卻是兩岸高處去水已三十丈上下的吊腳樓。這些房子莫不儼然懸掛在半空中,借著黃昏的余光,還可以把這些希奇的樓房形體,看得出個(gè)大略。”②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248頁。這里作者的主觀感情似乎也在影響著色彩的選擇。紅色為主色調(diào),熊熊烈火的油柴把整個(gè)河面照成紅的了,仿佛那古怪聲音、木棒槌有節(jié)奏地敲著船舷的柝聲都變成了充滿色彩美的音樂。這一切是那么的樸素、那么的平常,卻又那么的豐腴靈動(dòng),有著暗示性與音樂性的色彩美。
有時(shí)則不直接用青橙黃綠青藍(lán)紫的顏色本身,而是借助形象化的語言,以深淺濃淡等各種不同的語言色調(diào),摹畫出更加鮮明強(qiáng)烈的色彩,造成極為狀貌傳神的藝術(shù)效果。這種手法常常為了強(qiáng)調(diào)情感的流露。如汪曾祺《花園·茱萸小集二》中所寫的花園,就很少寫顏色本身,而是寫了記憶中菖蒲的味道,及巴根草、臭芝麻、腥味的虎尾草等各種草給“我”的樂趣;玩垂柳上的天牛、捉蟋蟀、捉蟬、捉蜻蜓、捉土蜂等童年的歡樂;故鄉(xiāng)的鳥聲及童年養(yǎng)鳥;自己掐花及花給一家人的幸福等,作者所要表達(dá)的是濃烈的鄉(xiāng)情與逝者已矣的傷感。為了表達(dá)此生命的體驗(yàn),則用了各種濃淡深淺的語言色調(diào)及形象化的描述,極寫童年家中最亮的地方,并強(qiáng)調(diào)說:“我的臉上若有從童年帶來的紅色,它的來源是那座花園。”雖未直接寫顏色,但卻能感覺到色彩的韻調(diào)。林徽因的《窗子以外》由窗子產(chǎn)生聯(lián)想,她從窗外四個(gè)鄉(xiāng)下人的背景談起,浮想聯(lián)翩,想到了平原、山巒、麥?zhǔn)颉⒚姿冢杉依锏墓凸は氲搅死嚨摹①u白菜的、推糞車的、買賣貨物的、追電車的,還談到了坐車過站的老太太等等,對(duì)顏色未著一詞,卻有五彩斑斕之感。
另外,像以形傳神、形神畢肖的中國(guó)畫法在京派散文也有表現(xiàn)。以形寫神,重在一個(gè)“形”字,“形”是重點(diǎn)是基礎(chǔ),無“形”而傳“神”則易空洞無物,但一定要抓住能傳達(dá)人之心靈的那個(gè)獨(dú)特的有意味的“形”,是屬于心靈的“這個(gè)”的“形。傳神寫照的繪畫方法在中國(guó)由來已久,古代藝術(shù)理論史上,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最早提出“以形傳神”。相傳他畫人常數(shù)年不點(diǎn)睛,人問其故,他說:“四體妍媸,本無關(guān)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之中。”③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美學(xué)教研室編:《中國(guó)美學(xué)史資料選編》上冊(c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75頁。其所強(qiáng)調(diào)的即是“眼睛”,是屬于“形”的“這個(gè)”,以之傳神,則神情活現(xiàn),神理如畫,形具而神生,而不必在“四體妍媸”等枝上多費(fèi)筆墨。但寫“形”一定要意在傳神,傳其神,著力于寫其心。如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中對(duì)女人的描寫:“女人臉上呈塊紅色,頭發(fā)披下了一縷,又用手抓上去。”④林徽因:《窗子以外》,天津《大公報(bào)·文藝副刊》1934年9月5日第99期。短短一句話,就把女人那種慵懶、閑散、郁悶的神態(tài)寫活了。
四、“文”“樂”相融
京派散文有著很強(qiáng)的節(jié)奏感,這“節(jié)奏感”原就屬于音樂的,指音樂中交替出現(xiàn)的,有規(guī)律的強(qiáng)弱、長(zhǎng)短的現(xiàn)象,而京派散文的節(jié)奏是引申了的音樂的節(jié)奏。具體表現(xiàn)在聲音的節(jié)奏、句型的節(jié)奏、描寫力度的節(jié)奏等。節(jié)奏藝術(shù)的精心營(yíng)構(gòu),亦讓京派散文充滿了樂感。
(一)聲音的節(jié)奏
“每一件文學(xué)作品首先是一個(gè)聲音的系列,從這個(gè)聲音的系列再生出意義。”①[美]韋勒克、沃倫:《文學(xué)理論》,劉象愚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書店1984年版,第166頁。此話主要是針對(duì)詩歌說的,對(duì)散文也同樣適合。聲音當(dāng)與情緒有關(guān),通常意義上說,散文的情韻節(jié)奏不講究押韻,不講究整齊的句法(當(dāng)然也不排斥整齊的句法)。然而,有時(shí)散文中插入少量有韻的句子,則能使語言在五音錯(cuò)落中呈現(xiàn)重復(fù)與再現(xiàn),讀來鏗鏘、有韻。沈從文、何其芳、汪曾祺等的散文語言都具有著抑揚(yáng)頓挫、音節(jié)變化、語調(diào)流轉(zhuǎn)、優(yōu)美和諧的節(jié)奏藝術(shù)。
比如沈從文《白河流域幾個(gè)碼頭》中,在敘述自己游蹤時(shí)多用的是散句,但敘述之中也間有句式整齊、頗有韻味的四字句:“夾河高山,壁立拔峰,竹木青翠,巖石黛黑。水深而清,魚大如人。”②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353-354頁。鏗鏘有力,且充滿著穩(wěn)定感。這種長(zhǎng)短句式參差有致,整齊和不整齊處的和諧統(tǒng)一,產(chǎn)生了一種錯(cuò)綜的美。《沅陵的人》的中:“山后較遠(yuǎn)處群峰羅列,如屏如障,煙云變幻,顏色積翠堆藍(lán)。早晚相對(duì),令人想象其中必有帝子天神,駕螭乘霓,馳騁其間。繞城長(zhǎng)河,每年三四月春水發(fā)后,洪江油船顏色鮮明,在搖櫓歌呼中,聯(lián)翩下駛。長(zhǎng)方形木筏,數(shù)十精壯漢子,各據(jù)筏上一角,舉橈激水,乘流而下。其中最令人感動(dòng)處,是小船半渡,游目四周,儼然四周是山,山外重山,一切如畫。水深流速,弄船女子,腰腿勁健,膽大心平,危立船頭,視若無事。”③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353-354頁。也是長(zhǎng)短句交錯(cuò),以及大量的四字句式,呈現(xiàn)出整齊與不整齊和諧統(tǒng)一。
聲音的節(jié)奏,使京派散文充滿著音樂性,既有著諸多因排比、對(duì)偶的運(yùn)用而產(chǎn)生的整體美,更有著因句子長(zhǎng)短參差、伸縮有致的參差美。
(二)句型的節(jié)奏
好的散文在句型上也有著一定的節(jié)奏感。通常,動(dòng)作快,節(jié)奏強(qiáng)烈,急促,宜用短句;重說理,重抒情,節(jié)奏舒緩處,則常常用長(zhǎng)句。以汪曾祺《風(fēng)景》系列散文之一的《堂倌》為例,文中說自己對(duì)壇子肉不感興趣的很大原因與那個(gè)堂倌有關(guān),堂倌低眉,對(duì)客人的下作讓人感覺生之悲哀,他很干凈,但絕不是自己對(duì)干凈有興趣。簡(jiǎn)直說,他對(duì)世界一切都不感興趣。這里,作者感情平穩(wěn),以長(zhǎng)句敘述,節(jié)奏比較舒緩。但接下來對(duì)堂倌的具體描述中,則有:“他不抽煙,也不喝酒!他看到別人笑,別人喪氣,他毫無表情。他身子大大的,肩膀闊,可是他透出一種說不出來的疲倦,一種深沉的疲倦。座上客人,花花綠綠,發(fā)亮的,閃光的,醉人的香,刺鼻的味,他都無動(dòng)于衷。他眼睛空漠漠的,不看任何人。他在嘈亂之中來去,他不是走,是移動(dòng)。他對(duì)他的客人,不是恨,也不輕蔑,他討厭。連討厭也沒有了,好像教許多蚊子圍了一夜的人,根本他不大在意了。他讓我想起死!……說什么他都是那么一個(gè)平平的,不高,不低,不粗,不細(xì),不帶感情,不作一點(diǎn)裝飾的‘唔’”,“我們叫了水餃,他也唔,很久不見,其實(shí)沒有,他也不說,問他,只說‘我對(duì)不起你。’說話時(shí)臉上一點(diǎn)不走樣,眼睛里仍是空漠漠的。我充滿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痛苦。”④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7頁。顯然,這里短句居多,節(jié)奏強(qiáng)烈,急促。
(三)描寫力度的節(jié)奏
京派散文的語言節(jié)奏有時(shí)還通過描寫的力度來呈現(xiàn),以使文本力量的發(fā)展方向與變化自然地交織起來,形成鮮明的節(jié)奏。
仍以李廣田的《山水》一文為例。文本的起始,娓娓敘說平原之子因讀山水之文而產(chǎn)生的寂寞、悲哀,以及對(duì)遠(yuǎn)方山水的想象與神往。行文至此,節(jié)奏都比較舒緩。接著述說自己的祖先如何來此平原,如何改造平原。以己之力,改造天地,開始一偉大工程,鑿成一道大川流。從此以后,“我們”祖先才可以垂釣,可以泅泳,可以行木橋,可以駕小舟,可以看河上的煙云。“我們”的祖先仍是覺得不夠好還要在平地上起一座山岳。用一切可以盛土的東西,運(yùn)村南村北之土于村西,又把那河水引入村南村北的新池,于是一曰南海,一曰北海,山是土的,于是采西山之石,南山之木,進(jìn)而成為:峰巒秀拔,嘉樹成林,年長(zhǎng)日久,山中梁木柴薪,不可勝用,珍禽異獸,亦時(shí)來?xiàng)梗虾1焙#嘧贼~鱉蕃殖,萍藻繁多,夜觀漁舟火,日聽采蓮歌。描寫的力度增強(qiáng),節(jié)奏開始加快。接下來在文本末尾卻總結(jié)說:“然而我卻對(duì)你說了一個(gè)大謊,因?yàn)檫@是一頁歷史,簡(jiǎn)直是一個(gè)故事,這故事是永遠(yuǎn)寫在平原之子的記憶里的。……那里仍是那么坦坦蕩蕩,然而也仍是那么平平無奇,依然是村落,樹木,五谷,菜畦,古道行人,鞍馬馳驅(qū)。……我在那平原上生長(zhǎng)起來,在那里過了我的幼年時(shí)代,我憑了那一塊石頭和幾處低地,夢(mèng)想著遠(yuǎn)方的高山,長(zhǎng)水,與大海。”①李廣田:《李廣田全集》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頁。節(jié)奏再度松弛。行文一波三折,以描寫的力度控制行文的節(jié)奏。
結(jié)語
京派散文的語言是一種古今中外狂歡化的語言形態(tài),其“陌生化”的“整體感”,以及奇警的譬喻,似繪的行文,音樂的節(jié)奏等,集中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中國(guó)和西方、審美與文化的多重內(nèi)涵。它以較為純熟的現(xiàn)代漢語句式,融合感性與理性,以精英化獨(dú)白等表現(xiàn)形式,為讀者營(yíng)造了一種感性與思辯、平淡而豐蘊(yùn)、古典而現(xiàn)代的語言盛宴,讓人產(chǎn)生鮮活與無盡的現(xiàn)代性的形象想象。它彌漫著中國(guó)固有的神韻,又氤氳著現(xiàn)代性的美感。在一定的意義上,京派散文的語言標(biāo)識(shí)了京派散文的藝術(shù)高度,是京派散文甚至也是整個(gè)中國(guó)現(xiàn)代散文藝術(shù)的集中體現(xiàn)。或者直接地說,京派散文的語言是中國(guó)現(xiàn)代散文語言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