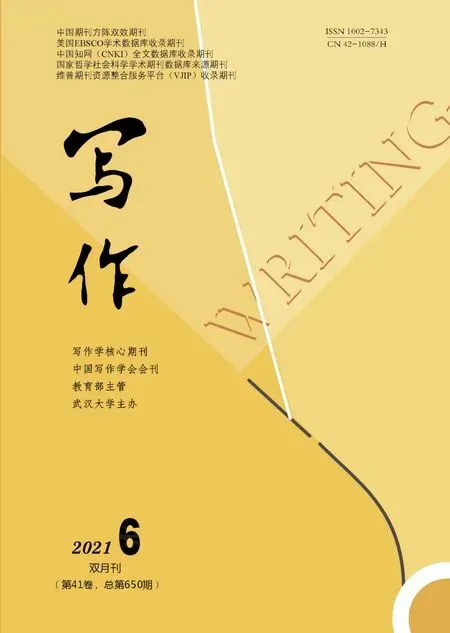自我變化中的恒定堅守
——讀莫言小說集《晚熟的人》
朱 斌
莫言的小說集《晚熟的人》(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是他獲諾貝爾文學獎8年后才姍姍來遲的一部作品集。固然,正如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它體現了作家有意識的自我突破。然而,我覺得,在其自我突破與新變中,有些深層的東西卻被他執著地呵護著、堅守著,那就是其小說的恒定優勢與脈動:一如既往地暴露著人性的扭曲與生命的異化,探尋著人性的美好與生命的健康,還力求揭示人性與生命的復雜多樣;且把人性探究、生命追問與社會歷史反思緊密聯系起來,深入剖析著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時代痼疾及其導致的人性與生命悲劇;但終究又超越了社會歷史與時代現實,有著更加深廣的人性內涵與生命意識;還一如既往地重視故事及其敘述的魅力,堅守著對小說虛構藝術的信仰,有著恒定的敘事姿態。
所以,在為其自我突破的一陣陣歡呼聲中,我甘愿靜下心來,嘗試著,去觸摸其變化中的恒定脈動與優勢堅守。
一、恒定堅守的人性與生命探索
莫言在自我突破中始終堅守的,主要是獨特的生命意識與人性探索。人性尊嚴與生命禮贊,是文學的一永恒母題,它們曾使文學生機勃勃,紅光滿面。然而,在人類的現代化進程中,它們卻遭遇了普遍危機:“一方面,現代人蔑視權威,打破一切偶像后,現代社會并未呈現出‘王道樂土’,相反使人感受到一片憂郁、凄涼的精神荒原。另一方面,新世界的陌生而炫目的光芒又令人迷惘而一時無所適從。”①吳義勤:《文學現場》,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頁。這樣,人性的扭曲、麻木與蛻變,生命的異化、失重與萎縮,就成為現代人真切的生存體驗。因而,許多現代作家無情地暴露著現代社會的人性扭曲與生命異化,并焦灼地尋找著健康的人性與生命。莫言也不例外:他的小說創作,始終執著地暴露現代社會的人性扭曲與生命異化,也執著地探尋人性的健康與生命的美好。生命意識與人性探索,就成為其小說創作一以貫之的追求。
首先,這部小說集一如既往地暴露著人性的扭曲與生命的異化。此前,莫言的諸多小說人物,譬如《檀香刑》中冷血狂妄的劊子手趙甲、《天堂蒜薹之歌》中卑鄙無恥的王書記、《四十一炮》中偏執貪肉的羅小通、《豐乳肥臀》中屈辱墮落的喬其莎和《酒國》中生產“肉孩”的金元寶夫婦等,都可視為丑陋人性與異化生命的典型。這部新小說集里的諸多人物也是如此。《斗士》反復渲染了“斗士”武功的各種“好斗”表現:與黃耗子打架斗氣,把自己珍貴的象牙棋子扔進了河里,還把黃耗子那畝長勢喜人的玉米統統攔腰砍斷;與王魁打架斗狠,逼得王魁最終帶著老婆孩子離開了村子;與村支書方明德斗了一輩子,方明德死了也沒饒過他……這就突出了他那扭曲、偏激而怪誕的人性與生命。一位人性丑陋、生命異化的“睚眥必報的兇殘的弱者”形象,便鮮活地呈現在讀者眼前。這形象是復雜而立體的:既是身份卑微的可憐弱者,又是爭強斗狠的兇殘強人;既是破罐子破摔的自輕自賤者,又是嘴硬氣傲的自尊自大狂。
這種人性的扭曲與生命的異化,在《詩人金希普》中,體現為金希普的沽名釣譽、坑蒙拐騙而毫無愧疚;在《表弟寧賽葉》中,體現為寧賽葉的盲目自信、怨天尤人而毫不自省;而在《紅唇綠嘴》中,則體現為“高參”覃桂英的興風作浪、詭計多端而毫不自知,“不知道自己壞反而認為自己很正確很好”“永遠都在恨別人、罵別人”②莫言:《晚熟的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76、65-66、112頁。。所以,小說反復描寫了這類人物對他人的各種辱罵、欺騙與殘害。仇人方明德死了,武功仍不依不饒罵他“王八蛋”“老混蛋”;與王魁打架時,武功“罵出的詞兒令聽者都感到羞愧”,他還跑到王魁家門口“叫罵不止”,“聲音尖厲,全村的人都能聽到”③莫言:《晚熟的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76、65-66、112頁。。寧賽葉更是罵遍了整個世界:罵“我”是“笨蛋”“騙子”“欺名盜世”,罵文學刊物編輯“有眼無珠”“不識貨”,罵“真實的社會一團漆黑”,罵“虛擬的網絡暗無天日”。“高參”覃桂英當年侮辱打罵李老師逼得她投井自盡,如今則辱罵糾纏鄉長逼迫他主動申請去新疆任職。這諸多辱罵、欺騙與殘害,有效體現了作家批判人性丑陋、暴露生命萎縮的意圖:對他人的辱罵、欺騙與殘害過程,就是人性扭曲和生命異化的過程,它們構成了一個丑陋、卑劣的可怕世界。在此意義上,這些小說就是一篇篇人性異化與生命扭曲的寓言。
其次,這部小說集還一如既往地歌頌著人性的美好,探尋著生命的完善。此前,莫言的諸多小說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譬如《售棉大路》中善良可愛的杜秋妹、《紅高粱》中敢愛敢恨的“我奶奶”戴鳳蓮、《檀香刑》中為愛大膽癡狂的孫媚娘和《豐乳肥臀》中充滿原始母愛的上官魯氏等,都是美好人性與健康生命的化身。這部小說集里的諸多人物身上,也散發出星星點點的美好與可愛,雖然微弱,但如同暗夜里的一盞盞燈火,足以給人希望與溫暖。這主要寄寓在一些女性形象身上,尤其寄寓在她們對愛情、婚姻的信仰與堅守上。在《等待摩西》中,村里最漂亮的姑娘馬秀美,不顧輩分的差異和已有婚約的身份,不顧別人的恥笑與家人的反對,嫁給了自己喜歡的男人柳衛東。為此,她付出了沉重代價:被父母攆出家門,與丈夫搭個棚子過日子,不久就變得“目光悲涼,頭發蓬亂,身上散發著爛菜葉子的氣味”④莫言:《晚熟的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76、65-66、112頁。。后來,她丈夫成了東北鄉首富,據說在外面有了一個家,但她卻并不懷疑丈夫。再后來,她丈夫莫名其妙失蹤了,雖然她曾懷疑“難道就因為我第二胎又生了個女兒,他就撇下我們不管了嗎?”但她依然相信丈夫,苦苦等待著他的歸來。失蹤35年后,丈夫終于回來了,她無怨無悔,依然接納了他,且成了幸福的女人:“身體發福,面色紅潤,新染過的頭發黑得有點妖氣,眼睛里閃爍著的是幸福女人的光芒”①莫言:《晚熟的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32、165頁。。雖然,對馬秀美將其青春、生命與命運寄托在丈夫身上的做法,小說是有所反思與批判的,但她對愛情的信仰與忠誠,對婚姻的堅守與執著,則得到了作者的認同與贊美。這樣,她對丈夫摩西的等待行為,就成為美好人性與健康生命的一種隱喻:超越了愛情與婚姻,暗示了人性與生命中的真善美力量。
這種人性與生命中的美好,在《地主的眼神》中,體現為地主的兒媳婦于紅霞在苦難與不幸中給予“我”的信任、親近與合作互助;在《紅唇綠嘴》中,體現為小學班主任李圣潔老師對學生的坦蕩、真誠與無私關愛;而在《火把與口哨》中,則體現為“我”三嬸顧雙紅對三叔的情投意合、情深意長,對兒女刻骨銘心的母愛,以及她在一連串不幸與打擊中依然體現出來的強悍意志與血性生命。當然,這種真善美力量,在小說集里的一些男性身上,也有所體現。譬如,在《火把與口哨》中,三叔對三嬸的癡情與愛護,對陌生人的由衷同情與幫助,對朋友的坦誠與仗義;在《左鐮》中,田奎對“我”和“二哥”推卸責任造謠中傷的寬宥與原諒,對歡子的接納與不計前嫌;《在天下太平》中被老鱉咬傷的小奧對老鱉的善心與善舉……可見,這部小說集一方面在暴露人性的丑陋與生命的異化,另一方面,它也在探尋人性的美好與生命的健康,渴望建構一種理想的人性與完美的生命。在此意義上,我愿意把“澡堂與紅床”“紅唇綠嘴”等意象,視為人性丑陋、生命扭曲的隱喻,而樂意把“火把與口哨”等意象,視為健康生命與美好人性的象征。
最后,這部小說集還一如既往地揭示了人性與生命的復雜多樣。所以,小說往往避免了善惡截然對立、美丑迥乎分明的簡單傾向,而常常呈現出善惡一體、美丑交融的復雜難解狀態。小說集里的諸多人物,并非純粹的好人或壞人,而往往好中有壞、壞中有好,丑惡里有良善,良善中有邪惡與兇殘。在《地主的眼神》中,地主孫敬賢無疑是丑陋、邪惡的:他虐待欺辱兒媳婦,裝病逃避改造,對村民充滿仇恨,是陰險狡猾的壞蛋。但他也有可取和令人同情的一面:擅長做農活,割麥技術無人可比;深愛著土地,買了三畝賴地被劃為地主,有點冤;被貧協主任任意毆打,在階級斗爭中飽經摧殘。因此,作者對他的態度,并非一味的批判、否定,而是復雜難解的,正如小說敘述者“我”所坦言的:“我承認,我對這個具有超高割麥技藝的老地主沒有絲毫好感,但我對他無端挨打又充滿同情。”②莫言:《晚熟的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32、165頁。這種人性與生命的復雜,也體現在《斗士》中的武功身上:一方面,他家境貧寒,無依無靠,卻從不討好村干部,遭受過冤枉打擊,備受摧殘,是受人迫害的可憐人;另一方面,他又爭強斗狠,睚眥必報,手段陰損,是無人敢惹的惡人。此外,《晚熟的人》中的蔣二和單雄飛,《澡堂與紅床》中的董家晉和石連成,《天下太平》中的村長和警察等,也善惡混雜,正邪難解,也體現了人性與生命的復雜多樣。
其實,關注人性與生命的復雜多樣,是古今中外文學杰作的一個優良傳統。這既在莎士比亞、雨果和福樓拜等筆下有著突出體現,也在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別爾等筆下有著典型反映,還在曹雪芹、魯迅和張愛玲等筆下有著明顯表現。然而,在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中,隨著左翼文學的興起,尤其是發展到后來的“工農兵文學”,人性與生命的復雜,逐漸被一種非此即彼的簡單價值取向戕害了。因此,中國當代作家往往習慣了“革命與反革命”“正義與邪惡”“改革與保守”“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后”等二元對立思維,常習慣性地致力于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的簡單關系設置,而無法洞察人性與生命的復雜存在真相,更無法意識到探究這種復雜存在真相的重要價值。而對此,莫言卻始終保持著自覺警惕,他雖然繼承了左翼小說和“工農兵文學”關注底層民眾的可貴精神,明確宣稱自己是“作為老百姓的寫作”,然而,左翼小說和“工農兵文學”并非他唯一的藝術參照,他還以西方現代文學和傳統民間文學作為參照。對他而言,表現自我豐富復雜的社會感受、人生體驗,呈現民間大眾斑駁復雜的人性存在與生命狀態,才是自己底層書寫的要旨。這樣,人性的復雜多樣,生命的斑斕駁雜,存在的荒誕悖謬,就如鹽溶水般地融入其小說世界,因而有效置換了左翼小說和“工農兵文學”主題蘊含的明晰性、確切性。所以,這部小說既堅守了他一貫的創作立場:探究人性的復雜多樣,關注生命的豐富駁雜,又張揚了左翼文學立足底層大眾的閃亮光澤。
二、恒定堅守的社會歷史反思
這部小說集的人性探究、生命追問,還一如既往地與社會歷史反思緊密聯系起來:主要在深入剖析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時代痼疾及其導致的人性悲劇。此前,莫言的諸多小說,大都涉及了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譬如《檀香刑》涉及義和團運動,《紅高粱家族》涉及抗日戰爭,而《蛙》則涉及當代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因此,總體上,它們折射了中國激蕩起伏的現代化歷史進程,往往具有獨特的社會歷史反思意識:超越主流政治意識形態,主要是立足民間文化精神與民間倫理信仰的社會歷史反思,體現了莫言“作為老百姓的創作”的民間立場。這部小說集也如此:不同于當年諸多先鋒小說脫離具體時代背景對人性與生命的抽象探究,它以直面社會歷史的勇氣,努力挖掘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諸多社會歷史細節,深刻反思其間的社會偏激與時代痼疾,反思當代中國人為此付出的諸多人性與生命代價。
譬如,在《左鐮》中,地主田千畝聽信誣告,殘忍剁掉了兒子田奎的右手;在《斗士》里,方明德借口無產階級專政對村里嘴巴最硬的武功實施誣陷與打擊報復,這使武功心生怨恨跟他斗了一輩子①在此意義上,方明德與武功是兩個互為鏡像的“斗士”:都“生命不息,戰斗不止”。《生死疲勞》中毫不妥協、斗爭不已的洪泰岳也如此。很大程度上,他們的“斗士”精神都是受當時“階級斗爭”哲學熏染而成的。;在《等待摩西》中,柳衛東“大義滅親”與爺爺斷絕關系,且殘酷無情地揪斗爺爺;在《紅唇綠嘴》中,覃桂英、谷文雨兇狠歹毒逼死了李圣潔老師……很明顯,其中的人性丑陋與生命扭曲,都與中國現代化的革命進程密切相關,都屬宏大的社會歷史之罪,不應只歸咎于個體的人性善惡與生命美丑。所以,田千畝對兒子的殘酷,武功對他人的睚眥必報,柳衛東對親人的冷酷無情,覃桂英、谷文雨的自私與奸詐等,都有著社會歷史的必然性。在此意義上,他(她)們其實也是社會歷史變革的受害者。這樣,人性的丑陋與生命的異化,就落實到了具體的社會歷史情境之中:人性的丑惡體現了特定社會歷史的丑惡,生命的病態折射了特定時代現實的病態;對人性的批判暗含了對特定社會歷史的批判,對生命的反思交織著對具體時代現實的反思。因此,小說集里的許多人物,譬如蔣二、武功、摩西、金希普和覃桂英等,都經歷了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起起伏伏的社會歷史變遷:既經歷了20世紀50—70年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現代化變革風云,又經歷了上世紀80—90年代“改革開放”的經濟現代化變革浪潮,還經歷著21世紀以來“深化改革”的全面現代化變革激流。這樣,他(她)們起起伏伏的戲劇化人生歷程,就折射了中國當代農村起起伏伏的時代變遷過程,從而體現了作家深刻的社會歷史反思意識。
為此,莫言致力于社會環境或時代氛圍的營構,完成了對滋生丑陋人性與異化生命的“世道人心”的刻畫。所以,這部小說集對丑陋人性與異化生命的批判,不僅指向每篇作品的主要人物,而且更指向了圍繞在主要人物周圍的蕓蕓眾生——主要人物賴以生存的時代環境與“世道人心”。在《紅唇綠嘴》中,公社書記突發奇想,發起了一場旱田改水田的種植革命,要求學校停課去插秧;覃老九仗著祖宗八輩子的貧農身份,到學校警告老師:欺負貧農兒女就是欺負革命;造反派接管學校,鼓勵學生辱罵批斗老師;后來,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堅決不讓地、富、反、壞、右的后代們讀書……這些,構成了包圍著少年覃桂英的時代氛圍,是中國政治變革時代偏激的“世道人心”,這就為主人公覃桂英的人性扭曲與生命異化奠定了必要的社會現實基礎。而在《晚熟的人》中,“我”的小說《黃玉米》在家鄉拍攝成電視劇后,家鄉政府抓住商機,迅速建成影視基地,且很快把它發展成旅游熱點;游客們喜歡騎“女主角”騎過的毛驢,喜歡坐“女主角”坐過的花轎;村里人沾“我”的光,都發了財;冒牌作家偽造“我”的書法,讓旅游點攤位代賣……這些,則構成了包圍著主人公蔣二的時代環境,是中國經濟變革時代偏激的“世道人心”,這就為主人公蔣二的人性扭曲與生命異化奠定了必要的社會現實基礎。這樣,具體可感的時代環境與“世道人心”,就與主要人物的個性、命運有了真切聯系:既生動揭示了其生存環境的異常,又巧妙暗示了其個性、命運的走向。小說就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主要人物的人性丑陋與生命扭曲,更讓我們看到了整個社會與時代的人性異化與生命萎縮。而且,正因為致力于社會環境與“世道人心”的刻畫,小說集里的人性批判與生命反思才落實到了當代中國社會歷史的具體時空,其批判性與反思性才避免了抽象、空泛,滲透著對社會心理和時代精神的深入挖掘。在此意義上,這小說集的鄉村現實書寫,既迥異于當今主流書寫對鄉村現狀的“主旋律”反映,也迥異于當今消費主義書寫對鄉村現狀的“奇觀化”呈現,還迥異于當年先鋒寫作脫離歷史語境和時代背景對人性狀態的“抽象化”表達,因而是獨具特色的鄉村敘事。
然而,莫言的人性探究、生命追問,終歸又超越了社會歷史與時代現實,立足于更加高遠的人文關懷立場,有著更加深廣的人性內涵與生命意識。所以,無論是“斗士”武功的偏執與睚眥必報,還是“晚熟的人”蔣二的自大與財富欲望,抑或是“高參”覃桂英的興風作浪與胡攪蠻纏,雖都有其歷史根源、時代原因,但更源自人性自身的缺陷與生命本身的劣根性。譬如,“斗士”武功的偏執好斗,雖可歸咎于歷史的錯誤,因為在那偏執于階級斗爭的時代,人人都變得不像人了。但當他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之后,當他有了生活基本保障之后,當他可以保吃、保穿、保住、保醫和保葬之后,當他的仇人們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病的病了之后,他卻一如既往地偏執好斗。這就說明:他的偏執好斗,并不完全是歷史的過錯,而更應歸罪于人性自身的痼疾與生命本身的病態。可見,作家是站在了超越社會歷史與時代現實的人文高度,去觀照他的偏執好斗的。所以,這部小說集超越了一般現實主義的社會批判與歷史反思框架,抵達了人性批判與生命反思高度:挖掘出了社會歷史背后深沉的人性根源與生命痼疾,直面人性的丑陋與生命的殘缺,賦予了小說更加凝重的深廣內涵。其實,莫言前期的成名作,如《透明的紅蘿卜》和《紅高粱家族》等,都超越了社會批判與歷史反思的框架,而抵達了人性批判、生命反思的高度。它們不同于當時盛行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與改革文學等主流作品:只將人性丑惡與生命異化歸罪于客觀的社會政治與時代現實因素。其后來的諸多作品,譬如《蛙》《酒國》《檀香刑》《生死疲勞》等,也如此。
因此,社會歷史意識與人文關懷意識的有機交融,是這部小說集突出的內蘊特征。這樣,粗粗一看,你可以說它旨在現實批判、時代反思。但仔細一看,你會發現:它也旨在歷史批判、傳統反思。而更深入地看,你還可以發現:它更旨在人性批判、生命反思。所以,這部小說集的意蘊層次是多維度的,蘊含深廣,耐人回味。而且,作家暴露人性的缺陷、揭示生命的病態,正是為了認識自身的人性缺陷與生命病態,“以毫不留情的態度向自己問罪”①莫言:《莫言講演新篇》,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64頁。,從而將人們引向人性的美好與生命的完善。換言之,其目的正在于穿透人性的黑暗與生命的荒蕪,而展望理想的人性光芒與完美的生命景觀,實質上通向了人性與生命的救贖之路。所以,其社會歷史反思,有著更縱深的人性反省與更透徹的生命領悟,故賦予了這部小說集更加深廣的內蘊魅力。其實,莫言早就坦陳過自己小說創作社會歷史反思的這種人文追求:“把人作為自己小說描寫的最終極的目的,不是站在這個階級或是那個階級的立場,而是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②莫言:《莫言講演新篇》,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64頁。據此,這部小說集,比當前諸多現實書寫,立意更高遠,意蘊更深廣。
三、恒定堅守的敘事姿態
這部小說集還一如既往地重視故事自身及其敘述的魅力,講述了一個個極富傳奇色彩的精彩故事。所以,故事及其敘述的魅力,充盈于小說的字里行間,不可遏制地徐徐揮發出來。在當今作家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對小說虛構藝術的信仰與自信之際,在當今作家普遍相信現實比小說更精彩因而爭先恐后轉向“非虛構”寫作之時,莫言卻依然堅守著對小說虛構敘事能力的信仰,依然保持著“講故事的人”對故事講述的信心,依然神采飛揚,把一個個故事講得精彩紛呈,引人入勝,這無疑是難能可貴的,而且無疑是他在自我變化中恒定堅守的一種敘事姿態。
這種對故事及其敘述魅力的重視,體現為對小說開篇的重視:諸多小說的開篇,都毫無沉悶乏味的感覺,往往以出人意料的意外性偶遇,形成極富吸引力的戲劇性鉤子,吸引著讀者投身于故事。譬如,《斗士》的開篇,是“我”回鄉看父親時,意外得知方明德去世的消息,且意外遇到方明德的死對頭武功;《詩人金希普》的開端,是“我”參加在京工作的春節老鄉聚會時,意外遇到了“我們”東北鄉的著名詩人金希普;而《澡堂與紅床》的開端,則是“我”去家鄉的大澡堂洗澡時,意外遇到了當年棉花加工廠的廠長和幾位工友……這些,都構成了典型的意外性情境,它們作為小說的開篇,引人注目,是作家巧妙扔出的一個個敘事的鉤子,能牢牢地鉤住讀者的心,將其迅速鉤進小說的敘事之中。
這種對故事及其敘述魅力的重視,也體現為對小說結尾的重視:諸多小說的結尾,往往形成了首尾照應或空白懸念,因而余音繞梁,意味無窮。比如,《晚熟的人》以“我”偶遇暴富的蔣二開篇,以“我”意外接到他哭訴非法用地被查的電話結束;《等待摩西》以摩西改名為柳衛東開篇,以他重新改回摩西結尾;至于《地主的眼神》,則既以孫敬賢的葬禮開篇,又以其葬禮結束……這些,都構成了巧妙的首尾照應,且往往戛然而止,并沒有交代其后的結局,因而耐人回味,啟人深思。在《左廉》的結尾,導致田奎被父親砍掉右手的引發人物歡子,因“是克夫命,沒人敢要她”,但當媒婆問田奎敢不敢要她時,田奎卻毫不遲疑地說:“敢!”小說就此戛然而止。這也留下了諸多懸念與空白:他為什么答應娶當年導致他失去右手的人呢?他為什么對歡子的“克夫命”毫不顧忌呢?后來他真的同歡子結婚了嗎?《賊指花》的結尾,更是留下了一個久久懸而未決的問題:偷了胡東年錢包的人,究竟是誰呢?或許是武英杰,或許是尤金,甚至,或許“就是我”。這些懸念式結尾,并沒有滿足讀者相關的閱讀期待,而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間,因而更令讀者牽腸掛肚,欲罷不能。
這種對故事及其敘述魅力的重視,還體現為對小說情節結構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故事及其敘述的魅力,主要取決于小說結構布局的巧妙與情節進程的搖曳,而人物性格的變化成長則是決定情節結構布局及其發展進程的關鍵因素。這部小說集里的諸多小說,雖靈動跳躍,留下了不少時空的省略、空白,甚至情節懸念,往往缺乏連貫完整的情節進程。但諸多小說都常常遵循人物性格的變化逆轉或人物命運的起伏跌宕,形成了寫意式的情節布局結構,且還特別講究結構上的重復渲染與對比反襯,重視布局上的鋪墊、伏筆與照應,其結構藝術極為出色:常以人物為中心,依從人物的命運沉浮來布局情節結構。其實,這是莫言的明確追求:“我曾經說我是講故事的人,但是講故事不是最終目的,人物高于故事”①莫言:《一切來自土地的都將回歸土地》,《小說選刊》2017年第12期。。這樣,小說總體的結構布局往往圓滿而巧妙,有濃郁的中國古典小說的結構布局色彩:有的具古代志人小說的特色,有的富唐代傳奇小說的風貌,有的則接近傳統筆記小說的特征。
這種對故事及其敘述魅力的重視,還體現為對傳奇色彩的張揚。作者擅長在傳奇氛圍中展開人物命運與情節進程,營構了許多神奇意象與空間環境。譬如,《左鐮》中專門給左撇子用的左鐮、樹林里的墳墓以及墓洞里的大蛇;《賊指花》中的賊指花、松花江上的豪華游船和邊地的黑河旅店;《天下太平》中的臭水灣、咬人的大鱉和長腿的怪魚;《火把與口哨》中的教堂、狼壁畫、蠟燭店與狼窩……這些意象與空間環境,本身就極富神奇色彩、神秘情調,何況,它們又構成了人物的活動空間與故事的展現舞臺,因而奠定了小說的敘事氛圍與基調,有效強化了小說人物及其故事的傳奇性。而其中的人物及其故事,大都屬于典型的“奇人怪事”,也極富傳奇性。正因為有了濃郁的傳奇性做故事及其敘述的底色,莫言才敢不斷改變敘事方向而進行靈動的時空跳躍,去旁逸斜出追憶往事或敘述趣味盎然的細枝末節與次要人事,才敢頻繁中斷故事進程而進行插科打諢式的“元敘述”或“介入評價”。而且,正是“傳奇性”使這部小說集的故事及其敘述變得耐讀、耐咀嚼,成了一篇篇極富魅力的“好看的小說”。在審美的日常生活化浪潮成為審美主流的時代,在“新寫實”重視日常“煩惱人生”與“一地雞毛”的敘事慣性影響下,在依賴社會新聞與通訊報道寫小說已蔚然成風的當今文壇①21世紀以來,中國文壇出現了不少依賴社會新聞與通訊報道改寫的小說。余華的《第七天》是這方面的典型,小說以一位死者的視角,講述了他死后七天的經歷與見聞,串連起了大量社會新聞事件。為此,不少作家甚至還出現了嚴重“撞車”的雷同事故。譬如,2004年劉繼明發表在《山花》第9期上的小說《回家的路究竟有多遠》,2005年李銳發表于《天涯》第2期的小說《扁擔》,還有賈平凹的小說《高興》等,都化用了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千里爬回家》的社會新聞事件。,莫言依然信仰小說固有的虛構魅力,依然堅守小說古老的傳奇品格,且巧妙促成了傳奇性與現實性的有機交融,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無疑,這也是他在自我變化中恒定堅守的一種敘事姿態。
四、結語
如前所說,在這部小說集里,莫言是有所新變與突破的。何況,求新,求變,力求自我超越,原本也是他一以貫之的恒定追求。正如他明確強調的:“我的創作風格肯定還是要變化,不斷地求變”②莫言:《作為老百姓寫作:訪談對話集》,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頁。。但是,其自我突破,是以發揚他長期積淀而成的成功經驗和創作優勢為基礎的。因此,我更愿意強調他在自我變化中的堅守姿態,更樂意欣賞他在自我突破中的穩定步伐。在此意義上,對于莫言在這部小說集里自覺消減了其獨具個性的感覺化敘事,以至淡化了令人著迷的“莫言味”——那種五官開放、五味雜陳的獨特小說味道,那種“調動了自己的全部的感覺,并且發揮了自己的想象力”“具有生命的氣息”③莫言:《莫言講演新篇》,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的獨特小說味道——我是深感遺憾的。盡管如此,我依然有理由相信:莫言會有更成熟的自我突破之作——在自我變化中有著更加成熟的優勢發揮,在自我超越中有著更加流暢貫通的恒定脈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