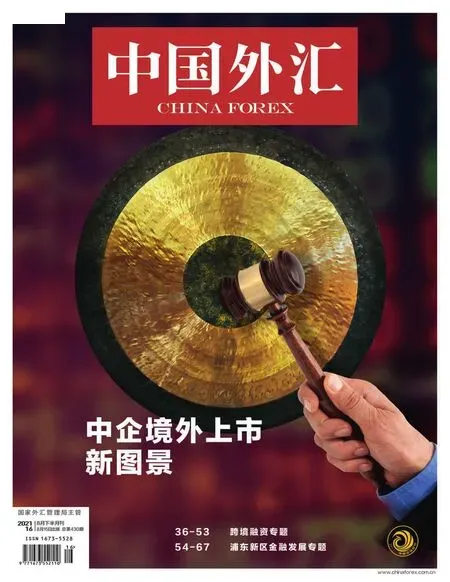美聯儲怎么看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2020年下半年以來,大宗商品價格出現顯著上漲。例如,美國商品調查局(CRB)現貨綜合指數從2020年4月27日低點的347.55上升到2021年7月29日高點的563.78,升幅高達62%。對于大宗商品價格如此快速上升,美聯儲怎么看?怎么辦?這是各界都非常關注的問題。
從歷史經驗看。2001—2008年,大宗商品價格同樣出現了顯著上漲,CRB現貨綜合指數從2001年10月31日低點的205.62上漲到2008年3月3日高點的485.73,7年漲幅達136%。其中,2001年10月至2004年3月,CRB現貨綜合指數從低點的205.62用兩年半的時間上升到高點的310.01,漲幅達50.8%。但在此期間,美聯儲并沒有顯著收緊貨幣政策,除在2003年6月25日宣布降息25個基點外,其他時間均保持了貨幣政策的穩定。美聯儲的首次加息是在2004年6月30日,此后在24個月中通過17次加息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從1%上調至5.25%。此期間CRB現貨綜合指數從低點的291.19上升到高點的337.07,漲幅為15.8%。此后,美聯儲從2007年9月18日開始降息,至2008年年初共降息6次。CRB現貨綜合指數則從2004年6月底的337.07上升到2008年3月的485.73,漲幅達44.1%。這表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決策并不針對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和下降,大宗商品價格的快速上升并不會引發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甚至在商品價格飆升期間還數次通過降息實行寬松貨幣政策。
更進一步看,通過梳理2003—2007年美聯儲的議息會議聲明,可以更好地理解美聯儲在進行貨幣政策決策時如何看待大宗商品價格走勢。
一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決策關注的是核心通脹率和長期通脹預期,而非大宗商品價格。美聯儲之所以在2003年6月25日宣布降息,其重要原因是,盡管彼時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幅度明顯,但美國的核心通脹率卻處于持續下行態勢。從當時的議息會議聲明看,由于彼時美國仍深陷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和美股大跌疊加此后的“9·11”造成的經濟衰退沖擊中,這一階段美聯儲更為擔憂的是“通脹率不受歡迎地大幅下降”。
二是美聯儲在進行貨幣政策決策時會充分考慮失業率等“資源使用率”情況。由于失業率等數據屬于滯后指標,這使得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決策更具有“適應性”而不是“前瞻性”,必然走在曲線之后。
三是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很大程度上還會阻礙美聯儲加息。在2003年至2006年年初的25次議息會議聲明中,美聯儲有15次明確表示,擔憂能源價格等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對美國產生負面的供給沖擊,導致“產出增長放緩,勞動力市場狀況改善步伐放慢”,迫使其在更長時間內盡可能保持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立場。直到2005年9月20日及此后的三次議息會議,美聯儲才在通脹預測中開始強調“更高的能源價格和其他成本上升可能加劇通脹壓力”,而此時美國的通脹已在高位運行。
四是美聯儲并沒有從資產價格和金融周期的角度看待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美聯儲始終認為其不具備超出市場的理性,不能夠早于市場辨識出資產價格泡沫。因而在2003—2007年的歷次議息會議聲明中,其從未提及美國家庭部門宏觀杠桿率的上升、房地產價格的泡沫及其與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及通脹壓力增加之間的關系,忽視金融周期的存在及其對實體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產生的顯著影響。這些寶貴經驗或教訓,成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經濟理論研究和多國貨幣政策實踐的重要思想基礎。
五是美聯儲更不會從全球金融周期的視角看待大宗商品價格上升。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主要關切的是美國的經濟周期,大宗商品價格的漲跌則與全球金融周期關系更為密切,而全球金融周期與美國國內的經濟周期并不一致。2001—2003年,美聯儲基于國內經濟周期的寬松貨幣政策,以及2004—2006年落后于曲線的收縮性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上升。但美聯儲在歷次議息會議聲明中從未提及美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
綜上,從歷史經驗看,盡管2020年4月底以來大宗商品價格的升幅已非常顯著,美聯儲仍然會選擇忽視,強調就業并堅持通脹的臨時性,更為突出大宗商品漲價的負面供給沖擊作用,避免討論資產價格,更不會采取實質性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措施。可以預計,美聯儲不會認真傾聽大宗商品價格上升釋放的預警信號,將再次走在曲線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