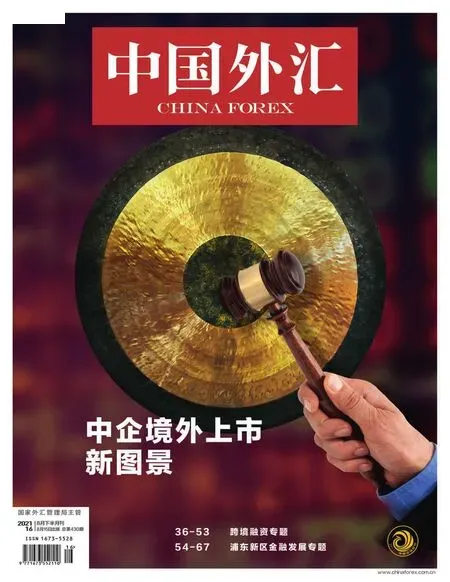中企境外上市:歷程、挑戰與趨勢
文/譚小芬 王煜茜 編輯/王亞亞
以1993年青島啤酒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為始,中企境外上市已近而立之年。近三十年的發展,中企在境外資本市場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群體,業內稱其為中概股,即注冊地在境外、但主要生產經營在境內的企業。來自Wind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7月16日,我國中概股上市企業數量共有1599只,其中,港股中資股1204只,美國285只,新加坡70只,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地也有少量中概股上市。境外上市已成為中資企業重要融資渠道之一,據Wind數據,2020年中資企業在美上市募資120億美元,較2019年的24.5億美元增長了約390%。
不過,自2020年瑞幸咖啡引發中概股新一輪信任危機以來,中概股在美面臨的證券監管環境日趨嚴苛,《外國公司問責法案》的實施進一步加劇了中概股的退市壓力。在此背景下,境內A股與港股市場不斷進行改革,中概股回歸境內資本市場與港股之路也漸趨平坦。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企境外退市的壓力。與此同時,由于境內監管對跨境數據流動、反平臺壟斷等問題的日益重視,中企境外上市也將面臨新的監管機制。從自由生長到規范發展,中企境外上市或將迎來新的時代。
中企境外上市的發展歷程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境內企業上市融資需求增大。但由于A股市場存在上市門檻較高、股票發行審核周期較長、審核過程具有不確定性以及再融資程序復雜等因素,相比之下境外成熟資本市場上市審核制度更為靈活,資本市場結構也更加多元化,一批中資企業,尤其是未盈利的中小科技型企業選擇赴境外上市,我國企業境外上市進程加快。我國企業境外上市發展進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股份制改革促進大型國企境外上市。1993年6月,中國證監會與中國香港證監會簽訂《監管合作備忘錄》,允許內地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在首批試點企業如青島啤酒、上海石化上市成功后,試點范圍逐步擴大,我國制造企業開始了境外上市的進程。在初始階段,主要有直接上市和間接上市兩種方式。青島啤酒、上海石化、華晨汽車等國有企業采取首次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方式,以境內公司的名義向境外證券主管部門申請發行登記注冊并發行股票,在境外直接上市。根據發行市場的不同,這些股票又被稱作H股(Hong Kong,中國香港)、N股(New York,紐約)、S股(Singapore,新加坡)等。部分國有企業為了避免直接上市程序復雜、成本高、時間長的問題,采取了間接上市方式,如中信泰富、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等中資企業,通過收購中國香港中小型上市公司進行改造或通過分拆業務等方式實現境外上市。
第二階段是2000年至2010年,主要是互聯網企業境外上市。早在1995年8月,我國通過了《設立境外中國產業投資基金管理辦法》,允許注冊于境外的基金投資于國內的產業。這一政策為境內企業境外上市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融資渠道。這一時期,正是中國IT行業和互聯網技術處于快速發展的關鍵早期,眾多互聯網企業急速擴張,對于發展資金有著迫切的需求,而美國注冊制度給新興互聯網企業上市帶來便利。這一階段,以新浪、網易和搜狐為代表的中國互聯網企業相繼成功登陸納斯達克,迎來了中國互聯網行業在美資本市場蓬勃發展的十年。這一階段,中概股赴境外上市多采用VIE架構,使以境外基金為代表的外資進入其股權體系,再利用境外分工明確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實現退出。而境外完善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滿足了不同發展階段企業的資金和股權交易需求,同時也保證了退出渠道的多樣性,吸引一批企業選擇境外上市。
第三階段是2010年之后,主要是民營企業境外上市。2005年后,我國相繼推出多項政策,大力促進民營企業在境外上市。金融危機之后,隨著國際資本市場的逐漸好轉,許多國內企業重啟境外上市計劃,致2010年我國境外上市企業數量達到歷史峰值,共計約50家中概股登陸美股市場,迎來了中概股歷史上的上市潮。2012年年底,中國證監會進一步廢除了中國企業境外上市的諸多條件,簡化了審核程序。2013年,中國證監會發布《關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發行股票和上市申報文件及審核程序的監管指引》,取消了財務要求并對流程進行了簡化。在此推動下,加之2012年A股IPO關閘和境外投資者對中國資產的需求,自2013年始,民營企業境外上市數量迎來了持續數年的增長,涉及網游、搜索等一系列泛互聯網企業,教育、連鎖商業等消費型企業和新能源、醫藥醫療、高端制造等一系列新興行業。這些企業將境外中概股的市值規模不斷推向新高。
中企境外上市面臨的現實挑戰
長期以來,中國企業境外上市熱潮不斷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在國內未實行注冊制以前,境外上市的速度和效率更高;二是企業通過境外上市尋找避風港,可規避境內監管機制的約束;三是確有一些企業因自身戰略發展需要,希望借助境外上市來擴大品牌知名度或重構企業治理模式,以促進企業管理層面的良性發展等。在A股市場尚未成熟完善之際,境外發達的金融市場確實為中資企業融資提供了便利。然而,隨著時間變遷,當初選擇境外上市的企業在獲得機遇的同時也面臨水土不服的挑戰。尤其是在美中概股,近兩年更面臨著多重挑戰。
一是中概股面臨更加嚴格的監管和審查環境。當前,隨著中概股公司的治理水平和內控質量不斷提升,美國監管機構對于中概股的監管重點逐漸從2012年以前的“查違規、抓欺詐”轉向審核公司會計處理的公允性、信息與風險披露的完備性等方面。在發生“滴滴事件”和出臺“教培雙減”政策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暫停了中國公司在美國首次公開募股(IPO)和其他股票銷售的注冊。如果未來中美關系繼續惡化,那么美國監管機構對中概股的監管態度將更加政治化、嚴格化,中概股赴美上市的難度會大大增加。因此,未來中概股很可能要面對更加嚴格的監管、審查環境,企業應當有更強的風控意識和更加規范、健全的公司治理理念。
二是做空攻擊成為中概股面臨的重要威脅。相對國內市場做空機制的缺乏,境外市場做空機制則相對豐富得多,其中不乏專業機構的做空套利。2010年以來,中概股先后經歷了多輪做空危機。據統計,2018年以來,美國做空機構接連針對中概股發布做空報告,做空企業超過40家。做空機構主要針對企業的財務問題、公司治理問題、商業模式問題等展開攻擊。雖然部分中概股企業確實存在惡意財務造假、欺騙和侵害投資者利益的行為,中國企業相對境外成熟市場的優秀企業在治理架構和投資者保護方面也確實存在差距,做空機制可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資本市場的配置效率;但做空攻擊行為若不能受到合理約束,也會侵害上市公司和投資者的利益。目前看,空頭機構的惡意攻擊行為,已經使部分優質中概股成為受害者:一方面造成中概股的估值歧視,通過增資擴股進行再融資的成本大幅提升,損害了其在境外市場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則導致中小市值中概股陷入被邊緣化的危險境地。
三是境內監管機構對跨境數據流動、反平臺壟斷等問題日益重視,中企境外上市面臨新的合規風險。2021年7月6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明確了加強中概股監管的政策導向。7月10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在數據處理和國外上市等方面新增了相關規定:如在第六條中規定,掌握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運營者赴國外上市,必須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情況;第十條規定,在網絡安全審查重點評估采購活動、數據處理活動以及國外上市可能帶來的國家安全風險的主要考慮因素中,新增了“核心數據、重要數據或大量個人信息被竊取、泄露、毀損以及非法利用或出境的風險”“國外上市后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核心數據、重要數據或大量個人信息被國外政府影響、控制、惡意利用的風險”。在反壟斷執法方面,近期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對未依法申報的經營者集中案件加大了查處力度,并公布了多起涉嫌協議控制模式的處罰案件。預計,未來國內企業經營和擴張會受到更嚴格的政府監管。隨著國家信息安全重要性的持續提升以及反壟斷執法力度的加大,中資企業境外上市面臨新的更加嚴格的合規要求。
中企境外上市的發展趨勢
一是在國際政治經濟態勢不確定性仍存的背景下,中概股境外上市面臨的監管風險可能增加。從2018年年初開始的中美貿易摩擦,逐漸蔓延到人員交流、科技、金融、地緣政治等領域。當前,對華強硬已成美國兩黨的共識,拜登上臺后中美關系也并未出現明顯的緩和跡象,且已經顯現出在全球性或區域性框架下聯合盟友共同施壓中國的傾向。這可能給境外上市企業增添新的監管風險。不過,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市場開放的大趨勢下,中資企業仍需要美國資本市場的支撐。美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較為完善,規范化程度高,金融市場更為成熟,能夠有效提高上市企業的國際聲譽和全球影響力,因此,中資企業不能完全放棄在美國市場的融資機會。面對日趨嚴格的監管,企業應提升自身治理能力,優化內控水平,防范美國市場惡意做空帶來的股價下跌以及達不到監管要求而導致的強制退市風險。從長遠看,未來中資企業赴美上市會越來越規范化。
二是近年來中國香港及大陸資本市場在制度上進行的一系列變革,增加了市場的包容性,為中概股回歸創造了有利條件和環境。過去大量中資企業之所以沒有在A股上市,主要是由于A股市場實行發行審核制度、不允許同股不同權,同時對企業的財務利潤指標有較高要求等等。從回歸角度看,此前,中概股回歸A股市場往往需要經過完成私有化、拆除VIE構架、清理境外SPV和境內實體股權關系等一系列復雜程序;但近年來,A股市場推出科創板,允許同股不同權及紅籌公司上市,并試驗注冊制發行,不斷降低上市公司門檻,進一步規范企業上市流程。與此同時,中國香港作為連結中國內地與全球金融市場的橋頭堡,具有一國兩制、連貫中西的獨特優勢,在中美關系不確定性增加和境內對網絡信息安全監管趨嚴的背景下,以其上市條件更靈活、資本運作效率更高以及對接國際資本市場更為便利,很可能會較為集中地承接中概股的回歸,港股市場內外樞紐作用也將愈發凸顯。
三是中資企業境外上市依然是我國新興產業對接境外資本市場的主要渠道,也是國有企業拓展(中國香港市場以外的)境外資本市場的重要融資通道,對我國相關產業乃至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斷提升。與此同時,中概股也是國際投資者分享我國經濟成長的重要途徑。對于中資企業而言,一方面不能完全放棄以美國為代表的境外市場,通過完善自身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嚴防財務造假和虛假披露等行為,利用好境外市場,進一步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和國際影響力;另一方面,可以積極擁抱香港和A股市場,在享受政策紅利的同時合理利用資金開展業務。
四是我國監管部門會繼續以中概股回歸為契機,進一步優化金融供給側改革,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建立健全相關的基本制度和法律法規體系,深化雙向開放機制。其一,強化資本市場的法治化建設,推進相關監管體制改革,保護各方參與者的合法權益,增強資本市場整體活力。其二,強化資本市場的市場化建設,包括:完善股票市場注冊制,重視科創板、創業板對主板市場的補充作用;促進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的發展,打破不同市場間的壁壘,建立起企業在不同市場間的轉換通道;完善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實現優勝劣汰。其三,在高質量對外開放的政策基調下,對金融市場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全面松綁;同時進一步縮減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以使部分為引入境外資本和技術、管理經驗的上市公司不必再通過境外上市的方式規避限制。其四,監管態度和制度保持嚴口徑。盡管近期網絡安全審查及反壟斷監管政策收緊或將影響互聯網龍頭企業的估值和發展,但長期看則有利于互聯網產業的規范發展和競爭格局的改善。那些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展開經營的企業,將長期受益。
可以預計,隨著A股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的逐步完善,未來多地上市將會成為中概股全面協同發展的一大趨勢;境內市場也必將秉承更加開放包容的態度,進一步完善中概股相關政策,使中概股回歸之路更加順暢。國內資本市場核心資產池也將因此迎來擴容,行業結構將更趨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