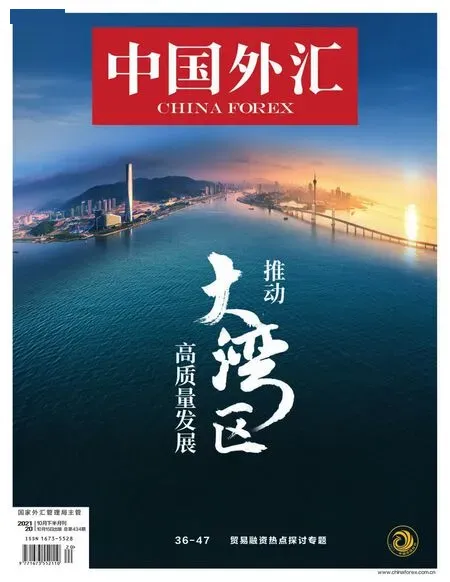慈善信托助推“共同富裕”新時代
文/趙長利 孫新寶 編輯/白琳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做出重大戰略部署:“十四五”時期,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發布。從頂層謀劃到國家戰略落地,我國從全面小康邁向共同富裕的議程和實踐正式展開。慈善信托作為一種將慈善行為和信托制度融合創新的業務模式,可以憑借其獨特的制度優勢,充分發揮其為社會公益事業服務的職能,推動我國共同富裕的進程。
慈善信托在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三次分配是調節收入分配、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徑。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要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提到“三次分配”,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三次分配”最早是由經濟學家厲以寧提出的。1992年,他在《論共同富裕的經濟發展道路》一文中首提“影響收入分配的三種力量”;在其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與市場經濟》一書中又做了進一步闡釋:通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為“第一次分配”;通過政府調節而進行的分配,為“第二次分配”;個人出于自愿,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出去,為“第三次分配”。
由此可見,第三次分配具有天然的“慈善”屬性。推動三次分配發展壯大,關鍵是構建三次分配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慈善信托作為一種將慈善行為和信托制度融合創新的業務模式,可以在三次分配中發揮重要作用。
慈善信托的起源與優勢
信托制度起源于慈善。當今世界各國的信托制度均繼受于英國的信托法或由英國法制演變而來的美國信托法。英美國家的慈善文化最初來自于宗教教義。基督教徒往往留下遺囑,把生前的私有土地死后贈與教會。因為不能對教會征稅,直接影響了封建君主的收益。12世紀,英王亨利三世頒布了限制此類捐贈的《沒收法》,教徒則以各種方式加以規避,其中最為流行的就是USE制度(用益制度),即教徒在生前立下遺囑,把土地贈與第三人所有,并在遺囑中明確土地贈與第三人的目的是保障教會對土地有“用益權”。USE制事實上成為了一種慈善遺贈的手段,這便是公益信托最早的雛形。之后,USE制不僅流行于教徒向教會捐贈土地,農民也利用這個辦法規避封建賦稅,信托制度開始逐步應用于各種私益目的。
我國慈善思想亦古已有之。先秦時期已有萌芽,《禮記·禮運》就為人們描述了一個“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世界。但是,我國的慈善事業一直沒有形成完備的制度體系,直到2016年《慈善法》和2017年《慈善信托管理辦法》相繼頒布,才為慈善信托奠定了基本法律框架,也為我國的慈善事業翻開了新的篇章。
相比直接捐贈、設立慈善基金會等方式,慈善信托具有以下四大優勢:
一是民政部門與銀保監部門雙重監管,合法合規。慈善信托設立前逐筆向銀保監局報備,設立后在當地民政部門備案,受到雙重監管,還需每年定期向民政部門上報慈善信托事務處理情況及財務狀況。
二是進行保值增值投資,實現捐贈資金效益的最大化。慈善信托賬戶內的慈善資金未捐贈時,信托公司可以進行相對安全的投資運作,籌集更多善款。相比于慈善組織,信托公司的投資范圍廣,更具靈活性,且不需要繳納所得稅。
三是信托專戶管理捐贈資金,安全且操作方便。信托公司作為受托人,在商業銀行開設信托專戶,用于保管委托人(捐贈人)交付的慈善資金,確保資金安全,且操作上隨時可以進行慈善捐贈活動。
四是信托合同設計靈活,可更好地實現委托人的意愿。慈善信托合同條款設置靈活,可約定每年捐贈比例,與公募基金相比,不受每年捐贈不低于收入70%的限制。
在促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信托憑借其獨特的制度優勢,可以充分發揮其為社會公益事業服務的職能,提高三次分配效率,推動我國共同富裕的進程。
我國慈善信托發展情況
2016年9月頒布的《慈善法》,推動我國慈善事業進入了全面法治化時代。慈善信托遂迅速成為我國慈善事業進行資產管理的重要方式,并得到快速發展,備案數量和備案規模均呈快速增長。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慈善信托委員會的統計,截至2021年8月31日,我國慈善信托備案單數達633單,備案財產規模為34.87億元。
就慈善信托整體發展情況來看,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一是慈善信托主體日益多元。委托人方面,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名人、普通公眾參與到慈善信托中。受托人方面,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慈善信托委員會的統計,截至2021年8月31日,已有88家機構擔任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其中包括信托公司60家,慈善組織28家。2021年新增受托人有4家信托公司和2家慈善組織,受托人隊伍持續擴大。此外,銀行開始進一步布局慈善信托托管業務。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的《2020年中國慈善信托發展報告》的統計,截至2020年年底,共有31家銀行成為慈善信托的托管人,包含6家大型國有控股商業銀行、9家全國股份制商業銀行、13家城市商業銀行和3家農村商業銀行。
二是慈善信托方式持續創新。在主體上,慈善信托通過與其他慈善組織合作,實現優勢互補。慈善組織在慈善項目運營管理、受益人篩選等方面具有豐富經驗,慈善資源與信托制度有效對接能釋放更大的能量,兩者在合作中探索出了更多的創新合作模式,包括慈善組織擔任項目管理人、委托人,以及以信托公司擔任委托人等。在業務上,慈善信托與其他信托業務相互賦能。比如慈善信托與家族信托有著天然的內在關聯性,二者信托架構均具有事務管理屬性,銜接孵化出的家族慈善信托業務,有助于高凈值客戶實現財富和社會責任精神的雙重傳承。
三是慈善信托目的更加豐富。據中國慈善聯合會慈善信托委員會統計,在已成立的慈善信托中,扶貧濟困、改善民生為目的的慈善信托占據較大比例,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此外,慈善信托還在教育、科技創新、文化保護、社會突發事件等領域體現出精準與專業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由中國信托業協會倡議設立、國通信托作為受托人的“中國信托業抗擊新型肺炎慈善信托”,得到行業的積極響應,共61家信托公司出資委托。此外,多家信托公司還單獨設立了以抗擊新冠肺炎為目的的慈善信托,數量達到92單,財產規模為1.48億元。慈善信托目的已覆蓋社會的方方面面,有望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徑。
慈善信托發展任重道遠
目前慈善信托發展中仍存在一些問題。2016年《慈善法》頒布后,慈善信托曾一度迎來迅猛發展。然而,2019年以來,整體發展勢頭有所放緩。究其原因,除我國慈善信托起步較晚外,還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從信托公司角度看,信托公司雖然在金融領域具有突出的專業優勢,但在慈善領域則專業性不足,缺少專門的人才進行慈善項目的設計和運營,往往要借助外部力量共同開展慈善活動。二是從保障制度看,《慈善法》和《慈善信托管理辦法》均提出了稅收優惠的促進措施,但目前尚無配套的稅收政策出臺,信托公司不具備向捐贈人開具捐贈票據的資格,委托人進行捐贈后無法享受稅收優惠。受制于相關的配套政策不健全,非現金資產的慈善信托也遇到較大障礙,如我國股權慈善信托就受到非貨幣信托財產非交易過戶政策缺失和稅收優惠政策不完善的掣肘。三是從外部環境看,公眾對慈善的認識還不足,仍有人把慈善信托等同于慈善捐贈,認為慈善信托是金融產品、保值增值的工具,這些都是對慈善信托的誤解和偏見。
未來慈善信托將在實踐中逐步完善,積極助推共同富裕。在轉型壓力和市場機遇并存的新時期,我國信托行業正在重新定位自身的目標,以充分發揮自身的制度優勢,抓住轉型中的重大機遇,助力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重點是要充分發揮信托的制度優勢,靈活設計業務模式,與民政部門、慈善組織等充分溝通,在共識的基礎上進行合作;對外則需要通過各種途徑,利用各種平臺積極宣傳慈善信托理念,消除誤解和偏見,增強大眾對慈善信托的認知和理解。在保障制度的完善方面,需要民政部門和銀保監部門相互協調,統一監管口徑。監管部門還需與國家稅務總局協商,落實慈善信托的稅收優惠,推動信托財產登記制度的建立,使不動產、股權等非現金資產也成為信托財產來源,擴大信托財產的接收范圍。相信慈善信托會在實踐中逐步發展壯大,為共同富裕貢獻更多的信托力量。
隨著相關制度的完善,社會公眾對慈善信托的認知越來越清晰,會有越來越多的高凈值人群、企業機構,甚至普通民眾設立慈善信托,體驗慈善價值。作為我國金融業四大支柱之一的信托,也將進一步發揮自身專業優勢,充分利用慈善信托這一金融工具,幫助更多的高凈值客戶搭建專業化慈善公益路徑,滿足客戶的慈善公益需求,努力為共同富裕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