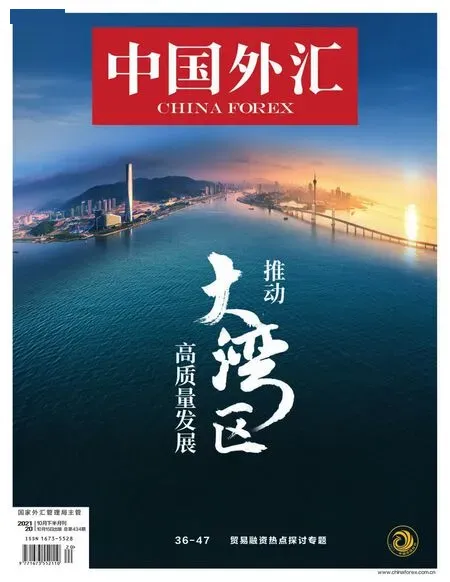從人民幣貨幣基差變動看我國外匯市場開放
文/溫嫻 袁培 林鋒 編輯/張美思
貨幣基差反映兩種貨幣的供需相對力量,常為危機、監管政策等外部因素所左右。貨幣基差提供了一個觀測一國外匯市場開放程度的視角。發達國家貨幣基差整體呈窄幅區間波動特點。近年來,人民幣貨幣基差從寬幅波動且受即期匯率影響明顯,逐漸轉變為波動區間收窄、與即期相關性弱化的特點。這說明我國外匯市場開放程度在不斷提高。
貨幣基差的涵義和特征
根據利率平價原理,遠期匯率可以根據即期匯率、兩種貨幣的利率計算得出。外匯掉期價格等于遠期價格與即期價格的差,反映兩種貨幣的利率差。理論上,如果市場價格偏離利率平價,就會產生套利行為,而套利行為又會驅動市場價格回歸利率平價。外匯掉期價格隱含的利率差與兩種貨幣名義利率差存在的差異,稱為“貨幣基差”。貨幣基差理論上為零,但是實際上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非零偏離是常態。
以三個月歐元基差為例。三個月歐元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Euribor)為-0.58%,三個月美元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Libor)為0.13%,兩者之差為71bps。歐元即期匯率為1.1700,歐元三個月掉期點為28pips,則掉期價格隱含的三個月歐美年化利差為95bps(28÷1.1700÷0.25=95,0.25年是掉期的期限),與實際利差的-24bps的差別就是三個月歐元的基差。這意味著,相對于美元而言,歐元處于“折價”交易狀態,即美元相對歐元更“貴”。
實際上,發達國家外匯市場形成了直接交易貨幣基差的金融產品,稱為交叉貨幣基差互換。交叉貨幣基差互換交換兩種貨幣的“無風險利率”,通常是交換“浮動對浮動”的利率支付。比如上述例子中的三個月美元Libor對三個月Euribor。交叉貨幣基差互換中加在非美貨幣利率上的溢價或折價,就是該貨幣的基差。
貨幣基差反映了兩個貨幣的供需相對力量,會受到市場結構、交易成本、套利限制、資金供求等因素的影響,常為危機、監管政策等外部因素所左右。在2008年金融危機、2020年3月底美元流動性危機等事件中,名義利率市場失效,對美元資金的強烈需求推動大多數貨幣的基差走低。此外,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基差,通常還與其外匯市場開放程度相關。對外開放程度越高,貨幣基差波動的幅度越小,越穩定。
可以說,外匯掉期市場對利率平價關系的背離,產生了非零基差。以美元兌人民幣掉期交易為例,人民幣貨幣基差等于外匯掉期價格隱含的中美利差與中美參考利率差異(名義利差)間的差異。換句話說,基差是名義利差無法解釋掉期價格波動的剩余部分。實踐中,境內美元與人民幣的交叉貨幣互換交易尚不活躍,市場有參考報價,但實際成交寥寥。資訊系統里查到的價格多為參考報價,可參考和使用的價值有限。而外匯掉期交易市場交投非常活躍,其深度和廣度更能滿足基差分析的需要。因此,人民幣對美元基差也有一個近似公式:人民幣對美元基差≈美元人民幣掉期點÷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中美參考利率差。例如,假設人民幣一年期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為3.00%,美元一年期Libor為0.24%,一年期的美元兌人民幣掉期點為1580pips,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為6.4900,則一年期人民幣貨幣基差近似為1580÷6.4900-(3.00%-0.24%)×10000=-33bps。
主要發達國家貨幣的基差研究
2008年金融危機以前,主要發達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基差相對較小。金融危機之后,隨著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厭惡情緒抬升,風險溢價逐漸上升,基差開始長期存在。從G10國家中三個最具代表性的貨幣——歐元、日元和澳元對美元的基差變化情況看(國外交叉貨幣互換市場非常發達,此處的基差數據用的是交叉貨幣互換基差),歐元和日元對美元的基差長期為負,意味著歐元和日元在與美元的互換交易中處于相對“折價”狀態。這種“折價”狀態不僅出現在一年期的互換交易中,其他期限亦是如此。究其原因,美元利率相對于歐元和日元長期具備利差優勢,有源源不斷的歐元和日元資金兌換成美元以追求更高的收益率。同時,歐元和日元對美元的基差走勢存在極高的相似性,這主要由于歐元區和日本央行奉行高度相似的量化寬松政策,流動性泛濫。澳元的情況則較為不同,澳大利亞本土的資本市場容量不足,澳洲企業常年在境外發行美元債券,募集美元資金后再換回澳元進行使用,因此澳元對美元的基差長期為溢價。
發達國家貨幣基差整體呈現出窄幅區間波動的特點。盡管2008年金融危機后,主要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基差長期存在,但整體看,發達國家的貨幣基差波動性較小,波動區間大致在100bps范圍以內。歐元對美元一年期基差波動區間約為[-105, 0],美元對日元一年期基差波動區間約為[-90, -10],澳元對美元一年期基差波動區間約為[-10, 40]。主要原因在于,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相對發達,外匯及衍生產品市場交投活躍,政策管制相對較少,跨市場的無套利機制相對完善,掉期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差異較小,且出現差異的時候調整較快。
人民幣貨幣基差和我國外匯市場開放
回顧近十年人民幣貨幣基差的走勢,其波動區間從寬幅波動走向收窄,且與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的相關性逐漸弱化。這表明,我國外匯市場開放水平在不斷提升。近十年來,人民幣貨幣基差走勢主要分為兩大階段。
第一階段為2015年“8·11”匯改之前。該階段人民幣貨幣基差大起大落,振幅達500—600bps;且受人民幣即期匯率的影響非常明顯,貨幣基差與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價格呈現同向變化。特別是在人民幣升值時,基差明顯擴大。該時期人民幣外匯掉期價格反映的隱含利差與中美名義利差水平相差較大,走勢無明顯的相關性。2009年到2011年4月,人民幣貨幣基差從-50下跌至-600,而同期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從6.82跌至6.3。2011年4月到2012年9月,人民幣貨幣基差上漲,從-600升至-80,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出現大跌勢中難得的回升行情。2012年9月到2014年2月,伴隨著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的下跌,人民幣貨幣基差再次下跌,從-80跌至-500。2014年2月到2015年8月,人民幣貨幣基差漲勢猛烈,從-500到0附近;同期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也迎來大幅上漲。
第二階段為2015年“8·11”匯改至今。這一階段人民幣貨幣基差的波動區間整體收窄,與即期匯率的關系明顯減弱。2015年8月至2017年2月,人民幣貨幣基差從0跌至-200,同期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出現上漲,貨幣基差不再隨即期匯率同向變動。2017年2月到2019年4月,人民幣貨幣基差從-200漲到-13,同期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劇烈波動(其在2017年大幅下跌,2018年上漲,2019年上半年下跌),人民幣貨幣基差與即期匯率之間無明顯的相關性。2019年4月至今,人民幣貨幣基差窄幅區間波動,同期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呈現明顯的雙向波動態勢。
人民幣貨幣基差近十年的走勢變化特點,反映了中國外匯市場開放程度的不斷提升。2015年“8·11”匯改之前,人民幣升值時貨幣基差擴大,反映的是外匯掉期隱含的美元利率水平大幅高于美元名義利率水平。與之相對應的是,外匯市場供求力量尚不夠多元,缺乏多樣化的參與者和交易需求,外匯市場的深度和廣度有待進一步拓展;同時與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等聯動性也較弱,跨境資本流動仍然存在較多限制,導致貨幣基差較寬且波動性較大。2015年“8·11”匯改之后,隨著我國境內外匯市場開放程度的不斷提升,人民幣貨幣基差不斷收斂。一是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雙向波動態勢明顯。此前單邊押注人民幣升值,持有美元便及時賣出的情況有所轉變,境內美元流動性出現極端緊張的情況大大減少。參與者類型越發豐富,供需更多元化,趨于平衡,改變了過去以結匯為主的局面,單邊踩踏行情大幅減少。二是境內外匯市場得到長足發展,市場深度和廣度有所拓展,參與機構的類型更為豐富。包括境外機構投資者、券商基金、財務公司等機構陸續加入銀行間市場,不同機構的交易需求和交易目的相異,促進了雙向交易。同時,外匯市場與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等聯動性增強,市場有效性提升,貨幣基差縮小。三是資本項目開放不斷推進。跨境資本流動從寬進嚴出轉向均衡管理,“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等改革舉措陸續推出;跨境融資限制也有所放寬,建立健全了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便利了大型企業集團跨境資金統籌使用,開展跨國公司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業務試點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得境內外資金融通及流動更為順暢,令境內外美元利差減小,也縮小了貨幣基差。人民幣貨幣基差波動特征愈加穩定,中美利差因素逐漸成為掉期價格波動的錨,市場有效性不斷提升。
展望未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持續深入,套期保值的理念將逐漸深入人心,機構和企業的資產負債管理、匯率風險規避的需求會不斷釋放,對交叉貨幣互換等衍生交易需求有望大幅增加。基于此,筆者認為,未來交叉貨幣互換市場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應進一步推進我國基差交易市場的建設,助力衍生品市場的長遠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