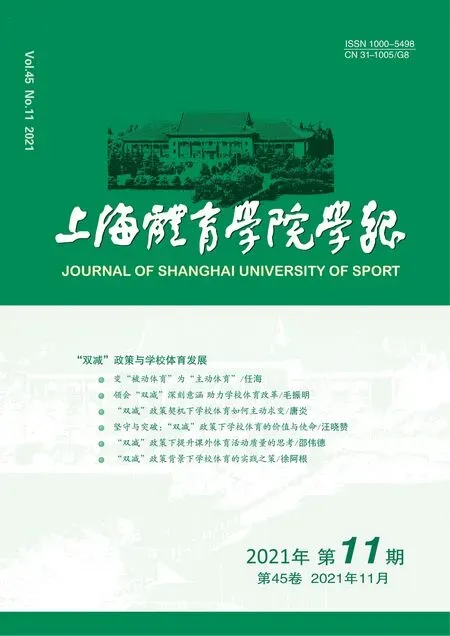體育旅游研究的歷史流變及其具身體驗轉向
謝彥君,吳 凱,于 佳
(1.海南大學旅游學院,海南海口 570228;2.海南大學旅游體驗研究與設計中心,海南海口 570228;3.東北財經大學旅游與酒店管理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究竟應如何認識體育旅游的本質?這個問題與旅游學術界始于若干年前并持續至今的“旅游是什么”的問題一樣重要,均屬于體育旅游研究的本體論問題。如何界定“體育旅游”以及在什么樣的基點上構建體育旅游的概念體系關系整個體育旅游知識體系的進化效率和知識貢獻的最終成果。關于體育旅游的基本概念,目前有不同的觀點和解釋。體育旅游是旅游的一個亞類,其所關涉的現象尤其是所觸發的效應是紛繁復雜的。正因為如此,在體育旅游研究早期階段,往往從其外部效應切入,導致很多學者尤其是國內學者或從市場、產業、產品、資源等不同面向對其進行界定[1],或從復合型產業的角度認識體育旅游[2];也有學者[3-4]提出“總和論”,認為“體育旅游是旅游者在旅游中所從事的各種體育娛樂、健身、競技、康復、探險和觀賞體育比賽等活動與旅游地、旅游業及社會之間的關系的總和”;還有學者[5]另辟蹊徑,提出體育旅游是教育活動的觀點。從這些定義所采取的角度可以看出:對“體育旅游”的認識,主要局限于體育旅游所產生的效益以及所關涉的范圍;對其教育功能的基本理解也影響到體育旅游的概念和功能界定。
在體育旅游研究的規模和深度逐漸得以提升的基礎上,對體育旅游的本質進行探索的本體論訴求才開始顯現。這一點在國外的體育旅游研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成就也更為突出。隨著體育旅游研究引入社會、文化等觀察視角,以及不斷采借其他學科已有的理論成果,如本真性理論、表演理論、凝視理論以及具身理論等,國外體育旅游研究領域逐漸形成了一系列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這為理解旅游世界中的體育旅游現象提供了富有洞見的詮釋。從這些成果看,“將體育旅游看作一種異地的具身體驗”這一理論命題日益得到越來越廣泛的學術認可,而大量的相關研究成果也構成了對這一本體論認知的知識基礎。然而,這一研究歷程至今并未得到有效梳理。“體育旅游是一種異地的具身體驗”這一足以引導旅游學術界研究實現理論轉向的本體論命題也并未被廣泛知曉,更談不上被普遍接受。鑒于此,本文在對國內外體育旅游研究文獻梳理的基礎上推演出體育旅游的這一本體論命題,從體育旅游研究的時間流變、范疇意涵與分類、研究視角等維度對其加以分析,將肯定或倡導體育旅游研究的具身體驗轉向作為圭臬,以期推動體育旅游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1 時間流變中的體育旅游研究
作為一種與身體運動機能相關聯的體育或運動(sports),它所指代的現象甚至其術語本身已經擁有相當悠久的歷史。從學術意義上研究它與旅游的關系,只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事情。根據筆者目前所能查閱到的文獻資料,最早將體育與旅游相關聯的外文文獻是1907年Nicholson[6]發表于美國《皇家陸軍醫療隊雜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rmy Medical Corps)上的《美國得克薩斯州的旅行和體育》一文,但該文實際上只是一篇分享個人海邊垂釣經驗的游記,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文獻。此后,在1911年的《地理學報》(The Geographical Journal)第37 卷第2 期上又刊登了一篇題為《旅行與運動》[7]的書評,但仍算不得一篇創新性的學術作品。直到1969年,Martyn[8]在《企業與社會》(Business and Society)上發表了《運動對國際旅游的影響》一文,才比較全面地從學術角度討論了運動與旅游之間的關系。這篇文章還富有遠見地強調了體育賽事參與者與觀賽人員在出行動機方面的差異。
1975年10月9日,在紐約舉行了為期1天的“運動和旅行”(Sport and Travel)會議。該會議是為了研究旅游和運動市場的相關問題而舉辦的,與會者回顧了以往在2個領域已經發生的相互影響,對未來的趨勢做了評估,并就如何銷售和推銷二者所共同構成的新型市場提出了一些建議。這次會議的舉辦標志著運動與旅游之間的市場融合已經初露端倪并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9]。此后,在一些大型體育賽事(如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舉辦期間,旅游業乘體育之勢成為學術界的重要關切點,并日益被納入體制性的學術研究視野,這種勢頭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達到了一個小高潮[10]。由以色列Wingate研究所的Mike Garmise所編撰的《戶外教育、休閑與體育旅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eminar and Workshop on Outdoor Education,Recreationand Sport Tourism),便使用了sport tourism一詞。自1993年Journal of Sport & Tourism(JST)創刊之后,這一用語便成為英語世界的規范用詞,差別僅表現為該刊的文章主要使用了sports 這一復數形式。例如,在Journal of Sport & Tourism1993年 第1 期 中,就 有4 篇 文 章(“Inaugural address,sports tourism international council”“Global understanding,appreciation and peace through sports tourism”“Sports tourism facility management functions”“Sports tourism international council:Review of activities”)在標題中直接使用了sports tourism這一術語。這一用法與該刊刊名中的“sport & tourism”形式之間的不一致,可能也是造成后來有關英語術語“sport tourism”和“sports tourism”爭議的根源之一。
進入21世紀后,國外體育旅游研究在規模和水平上都上了一個臺階:一方面,不僅論文數量激增,而且發表體育旅游學術成果的期刊數量也大幅度增加,僅英文期刊就超過50 種;另一方面,在這10年間,不僅相關領域的研究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科學實證的研究路徑得到普遍推廣,而且相關研究也不斷向縱深發展,其中的標志就是一些刊物專門組織了體育旅游特刊,集中展示相關研究成果。據不完全統計,在此期間,JST共出版體育旅游特刊11 期,主題涉及范圍相當廣泛,如:體育旅游,遺產、體育與旅游,體育“粉絲”和觀眾作為體育旅游者,體育旅游發展的可持續性,體育旅游的文化基礎,體育、旅游與國家標志,體育、旅游與奧林匹克賽事,體驗體育旅游,體育旅游目的地,體育旅游理論,參與型體育旅游。在此期間,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ESMQ)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IJSMM)和Tourism Economics(TE)3本期刊也推出了4期特刊,主題分別為:體育旅游——理論與方法;管理奧運體驗——挑戰與回應;體育旅游研究進展——營銷與管理;體育與旅游——經濟效應。這些特刊的推出極大地推動了學術界對體育旅游的研究,使體育旅游很快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領域,并逐漸以旅游知識版圖中一個分支的姿態引起人們的關注。
相較于國外體育旅游研究而言,國內的研究起步稍晚,在中文文獻中有關體育和旅游的話題起初也是分開討論的。在中國知網上所能查閱到的中文文獻中最早將旅游和體育相提并論的文章是王占春[11]1984年發表的《旅行、旅游與體育》,也將二者視為相關的“兩種”現象。盡管該文不算一篇規范的實證性學術論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為學校的體育教育立言,但值得關注的是,該文已經敏銳地注意到了體育與旅游的內在聯系:“旅行是體育的手段之一,但是,現在很少有人再提起旅行,它已被旅游所代替。其實這兩者有許多共同之處,卻又不完全相同。”“旅游也是一項十分有益的體育手段。通過旅游促進身心健康。人類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大城市的人口不斷集中,環境污染嚴重,體力活動減少,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不斷失去生態平衡,因此,許多人都希望有機會離開喧囂的鬧市,多接觸一些大自然,除了必需搭乘的交通工具外,多以步行、涉水、爬山等活動接受大自然的恩惠為享受。”這段表述已經觸及人們對旅游本質的認識。顯而易見,這種認識恐怕今天也并沒有更多人可以超越。在20 世紀80年代,另一篇將旅游與體育相提并論的是當時北京市旅游事業管理局研究室王仕平[12]發表于《旅游學刊》上的文章,主旨是“充分利用亞運會良好契機促進北京市旅游業的發展”,率先將體育賽事與旅游相關聯。可以看出,20 世紀80年代這僅有的兩篇涉及體育旅游的文獻都不是基于理論訴求的學術文章,而是面向社會實踐所提供的一種對策性建議。這種傳統延續到20 世紀90年代,以至于在此期間發表的將近20 篇文章中,只有曹締訓[13-14]、劉杰[15]和韓魯安等[16]將目光投向了體育旅游的理論問題以及知識體系構建問題。
進入21 世紀之后,國內的體育旅游研究呈現出數量上的爆發性增長。據不完全統計,在2000—2019年,國內共發表相關論文9 419 篇,國外只發表相關論文804 篇,相差懸殊(圖1)。從總體上看,國內外在體育旅游相關領域的發文數量均呈現上升趨勢,只是國內的增長速度更快。進一步審視國內體育旅游相關研究,逐年攀升的論文數量意味著“體育旅游”的主題不斷被關注和討論。然而,若從科學研究的類型看,以對策和規范研究為主的成果數量遠遠超過相關的基礎理論研究。這也集中暴露了國內體育旅游研究在理論訴求上并未達到應有的規模和水平。

圖1 國內外體育旅游相關論文發表數量Figure 1 Number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port tourism related publications over the years
2 體育旅游:術語、概念與分類
2.1 體育旅游的術語使用和概念界定
從前文對國內外體育旅游研究的梳理中可以看到,體育旅游這一術語以及相關概念界定并未在學術界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在國外,一直存在著術語選擇上的爭議;而在國內,存在西文翻譯至中文時文意表達的適當性問題。下面就此略作評述。
在英文文獻中,有關“體育旅游”的術語,主要有3種表達形式:sport tourism,sports tourism,sport(s)and tourism(其余非主要形式略而不論)。從文獻統計的結果看,這3 個術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占據的學術地位不同,其具體表現可以從表1和圖2看出。
對英文文獻進行梳理時會發現,在標題中以上述3 種術語形式出現的學術文獻數量在2000年前后呈現明顯的不同:在2000年之前,不管是從表1 所列的主要期刊,還是從所有英文期刊的情況看,都以sports tourism 這一術語的使用為主,sport tourism 次之,sport(s)& tourism 最少。在這一時期,sports tourism能夠占據壓倒優勢,要歸功于體育旅游專業期刊JST的主張與堅持:從1993年創刊到1999年,該刊發表的學術論文的標題中使用sports tourism多達63次,而使用sport tourism 僅3 次,sport & tourism 僅1 次。該 期刊作為本領域的權威期刊的這種堅持,也直接影響了其他期刊以及整個學術界的術語選擇傾向。因此,同期在其他期刊中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在標題中使用sports tourism的傾向也相當明顯。這種情況在2000年后出現了轉向:學術界逐漸拋棄sports tourism 一詞而選擇使用sport tourism,這主要源于期刊的多元性,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的期刊開始大量發表體育旅游的相關文章,也體現了人們要將sport tourism 打造成一個獨立而非組合概念的“決心”。這一趨勢也影響了JST的態度。從表1 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2000年之后,不僅全部期刊發表的文獻在標題中使用sport tourism 的頻率大大提高,并逐漸呈現壓倒性優勢,而且表1 所列舉的主要期刊,尤其是本領域的權威期刊JST,在術語使用上也已經轉而傾向于sport tourism 而非sports tourism。這一事實反映出國外學術界已經一致將sport tourism 作為一個專有術語使用,其中明顯體現出要將sport作為形容詞而非并列的名詞使用。這樣的術語選擇結果也很自然地在邏輯上呈現出將體育旅游視為多種多樣的旅游類型之一的傾向。顯然,經過近30年的努力,國外在體育旅游術語選擇上所達成的學術認同是體育旅游知識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性起點。

表1 1993—1999年和2000—2019年涉及“體育旅游”篇名的期刊術語使用情況Table 1 Use of terminology of journals related to the titles of "sport tourism" from 1993 to 1999 and from 2000 to 2019
早期國外學術界出現的有關體育旅游術語使用上的差異,一方面反映了體育旅游內涵的豐富性,另一方面則反映了不同研究者因關注視角的不同而引起的觀點差異。如Gibson[17]認為,sport更能凸顯體育旅游的整體性和類型特征。與此相反,Weed 等[18]認為,sports tourism 可以描述一系列多樣的、混雜的活動和體驗,有利于對體育旅游參與活動進行現象學探索。盡管人們所使用的術語不同,但其對體育旅游的理解并無本質性差別。
反觀國內學術界對體育旅游術語的使用,從體育旅游進入學術視野的最開始階段直到現在,呈現相對穩定、專一的態勢,“體育旅游”一詞基本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可和一致使用,英文則比較一致地對應“sport tourism”這一表達形式。由于“體育”一詞在當代漢語中已經形成了極其牢固且狹隘的概念意涵,因此,當在漢語中將“體育”與“旅游”相關聯并構成一個新的概念時,難免會使人們用傳統的漢語意涵解釋新的術語的內在意指。事實上,這種情況正在發生,并已經開始影響體育旅游的知識生產策略和知識體系化整合的路徑。
《現代漢語規范詞典》對“體育”一詞的解釋是“增強體質、促進健康等方面的教育,以各項運動為基本手段”。這一解釋是當今人們理解中文“體育”一詞最普遍、最一致的共識。也正因如此,偶爾會在中文文獻的“ 體育”一詞之后,發現標注的對應英文是physical education。當前,在謀求體育旅游作為旅游下屬的一個知識分支而不斷體系化的努力中,必須讓“體育旅游”這一概念的內涵擺脫這種狹隘的世俗化理解,還其本來面目,以便學術界順利形成在確定體育旅游研究對象、問題域、概念類屬、知識架構乃至學科體系方面的適當策略。
這里所謂還其本來面目,是指根據英文sport一詞的本義以及學術界多年來在探討sport tourism 相關問題時所形成的類型化知識架構,重新界定中文“體育旅游”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從認識論角度更為合理地確定體育旅游的知識譜系。
根據《牛津詞典》對sport 的解釋,其詞義主要有三:首先是“有規則的娛樂性競賽”,其次是“某種特殊的運動項目”,再次是在較為正式用法中用以表達“樂趣、消遣、娛樂、逗笑”意涵的詞語。在這3個主要含義中,最為突出的意指展現的是相關活動所具有的“愉悅性”或“娛樂性”本質,而這種愉悅性活動的實現方式的獨特之處僅在于規則的相對嚴格性。從這個角度去對比中文的“體育”一詞的含義發現,中文的“體育”帶有明顯的嚴苛性、規范性、教育意味,甚至隱約的國家主義色彩,娛樂性的意指已蕩然無存。這一點在將體育作為一種獨立的競技運動現象進而展開傳統意義上的考察時,并沒有什么學術上的障礙,但一旦體育與旅游“結緣”,就立刻暴露出中文“體育”一詞在概念層面的局限。這種情況從一些有關體育旅游的概念辨析的英文文獻中也可見端倪。
古特曼[19]有關玩耍(play)、游戲(game)、競賽(contest)和體育(sport)關系的概念性辨析,對深入理解英文“sport”一詞并進而厘定體育旅游這一術語的核心意指十分有益(圖3)。在古特曼的書中play 和game 都被翻譯為游戲,對照英文原文,本文統一將play 翻譯為玩耍,以便呈現play 和game 的區別。圖3展現了相關范疇的概念譜系關系:作為一種休閑行為,玩耍具有最寬泛的意指,在不同程度上包含著游戲、競賽、體育等多重或復合含義,甚至還與旅游有所交集。在這一概念之下,游戲是有組織、有規則的玩耍,競賽是有競爭的游戲,而以身體參與為主要特征的競賽是體育。作為4 個范疇的最高階形式,“體育”強調了身體參與和競賽的雙重意涵。當這種體育與旅游結緣形成新的旅游類型即體育旅游時,它必然根植于玩耍,并融合游戲、競賽、娛樂等多重內涵[20]。不過,即使體育旅游的內涵再豐富,作為旅游之一類并基于玩耍這一概念所具有的本質特征,它也必然同樣是一種以追求愉悅為目的的異地性休閑體驗[21]。

圖3 玩耍、游戲、競賽、旅游與體育范疇的內在關聯[19]Figure 3 Intrins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ategories of play,game,contest,tourism and sport
對上述概念進行辨析,一方面源于學術界對體育旅游內涵理解上的種種分歧,另一方面也力圖直指體育旅游現象的豐富性。從趨勢上看,盡管國內外學術界對體育旅游范疇的界定仍存在爭議,但總體上已經呈現一種對競爭的內涵弱化而強化體育旅游的玩耍或娛樂屬性的態勢。這一點值得特別關注。
2.2 體育旅游的分類
Gibson[17]依據參與和非參與的分類框架,將體育旅游分為參與型體育旅游(active sport tourism)、觀賞型體育旅游(event sport tourism)、懷舊型體育旅游(nostalgia sport tourism),其中后兩者屬于非參與型體育旅游。他由此提出了一個典型的體育旅游定義,即“個體臨時離開居住地,旨在參與體育活動,或觀看體育活動,或者表達對體育活動相關吸引物的敬仰而進行的休閑旅游”。不過Weed 等[18]認為,懷舊型體育旅游更多地表現為旅游動機,因而建議在參與型體育旅游和觀賞型體育旅游這個框架下加入共鳴參與(vicarious participation)的概念[22]。不可忽略的是,Gibson 對于體育旅游概念的界定和分類其實存在一定的形式邏輯問題,不僅違背分類的互斥原則,還存在循環定義的錯誤。此外還有學者如Gammon[23]根據旅游動機的構成,將體育旅游劃分為旅游體育和體育旅游兩類,二者都可以進一步分為硬(hard)參與和軟(soft)參與。
在傳統意義上,旅游者的身體參與程度是體育旅游概念界定和分類的主要依據。Lamont[24]和Shipway等[25]曾將環法自行車賽(Tour de France)中的那些參與比賽的人作為研究重點,不過他們也注意到環法自行車賽路邊那些聚在一起、行為滑稽可笑的觀眾。雖然他們同為體育旅游者,但由于類型不同,身體在其中的參與程度也有所差別。將不同類別的體育旅游置于以體育和體育旅游為兩極的連續體上(圖4)即可發現:參與型體育旅游的身體參與程度最高,是體育旅游的代表性類型,表現為旅游者加入特定形式的體育活動,常見的形式有沖浪、攀爬、皮劃艇等,還有很多與探險旅游(adventure tourism)和極限旅游(extreme tourism)相關的形式;共鳴參與型體育旅游和觀賞型體育旅游為中間的體育旅游類型,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身體參與,懷舊型體育旅游則為非參與型體育旅游,旅游者所關注的焦點不在體育活動,而是曾經開展體育活動的場所或社會關系[26]。越靠近體育范疇的體育旅游類型,越表現出身體主動和硬參與,而完全屬于體育范疇并無任何旅游成分的體育賽事及活動,不再屬于體育旅游的范疇;與之相對,靠近體育旅游范疇的體育旅游類型則趨于一般旅游類型,表現出身體被動和軟參與的特點。
圖4 所展現的關于體育旅游的范疇關系以及相應的分類框架,既強調了體育旅游者的身體參與特征,也明確了體育旅游的“旅游”屬性——體育旅游并非某種專業性、職業性的體育競技活動,其主成分是在異域環境中以身體參與為主的休閑體驗所能帶給人的運動快感。也正是由于其身體參與的特點,體育旅游與其他類型的旅游形式相比具有明顯的區別。

圖4 體育旅游的類型與身體參與程度Figure 4 Types of sport tourism and degree of physical participation
3 多維視角下的體育旅游研究
3.1 經濟、管理視角下的體育旅游研究
從經濟和管理的視角研究體育旅游,在國內旅游學術界顯得特別突出。對CNKI數據庫中的文獻進行檢索發現,文獻所屬學科多為商業、管理、經濟等領域(圖5),并多以為產業經濟發展提供對策為導向,從關鍵詞的分布也能進一步證實這一點,國內體育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策、產業、資源相關的主題上(圖6)。與此不同的是,國外相關研究往往將體育旅游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圖7),側重于對基本概念的界定,注重研究體育旅游中人的因素,探索相關個體和社會行為規律,并傾向于將體育視為愉悅、休閑的現象,理論探索的導向性十分明顯。

圖5 CNKI中體育旅游研究的學科分布Figure 5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of sport tourismresearch in CNKI

圖6 CNKI中體育旅游關鍵詞分布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sport tourism keywords in CNKI

圖7 基于Scopus數據庫的體育旅游研究所屬學科領域分布Figure 7 Distribution of subject areas based on sport tourism research in the Scopus database
自Abbott[27]提出“人們真正想購買的不是產品,而是通過活動獲得的滿意體驗”的觀點起,體驗服務逐漸成為企業關注的焦點,這一態勢在20世紀末開始成為一種新的潮流。在此期間,三部涉及體驗經濟和體驗營銷的暢銷書(《體驗經濟》[28]、《體驗營銷》[29]、《體驗為王》[30])應運而生,這說明通過恰當的體驗設計和管理為顧客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的理念正在被廣為接受。學術界對這一潮流的響應也相當及時而深刻,出現了大量的相關研究成果。Grove 等[31]運用劇場的隱喻,提出服務戲劇理論,借以思考“體驗”是如何被“營造”出來的。人們也注意到,體驗不僅涉及供給方的努力,也涉及顧客情感、價值和意義以及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基于此,在管理領域掀起了“共創”(co-creation)理念,即通過顧客與場所的雙向交互實現體驗[32]。前者將體驗作為商品或服務的一種附加值(added-value),后者將體驗視為對參與者具有情感、符號、轉換意義的一種東西。毫無疑問,上述基于企業經濟管理行為的這種體驗轉向也顯著地影響了體育旅游研究。例如,在Higham[33]看來,體育能更好地承受一個商品化的過程,提供給游客本真的體驗。Morgan[34]則從服務管理角度,提出一個整合上述2 個角度的體育旅游者體驗空間(experience space)模型,建構了如圖8所示的體育旅游者空間體驗模型。

圖8 體育旅游者體驗空間模型[34]Figure 8 The model of sport tourists' experience space
圖8 頂部是基于企業的拉(pull)的要素,包括體驗管理和體驗營銷2個方面。圖8的底部則是基于消費者的推(push)的要素,包括旅游動機、體驗收益(如興奮、放松、快樂等),這些心理因素既受到先在個人價值和意義訴求等立場性因素的影響,也受到相關群體社會地位和交互作用等因素的影響。在這個模型中,目的地是空間場所,旅游者是活動發動、實施的主體,二者通過社會互動和文化互動之后形成體驗。Morgan 的體驗空間模型的目標是通過人與場所、人與人的互動,實現Csikszentmihalyi所述的暢爽(flow)體驗。
在經濟和管理視角下的體育旅游研究表明,體驗不是單方面作用的結果,而是在旅游者和旅游企業打造的體驗空間的交互作用下實現的。這種主張是在人與環境的關系中探討旅游者的體驗產品問題,關注到了旅游者的主體性地位以及體驗產生的過程。盡管旅游企業的真正目的是顧客忠誠、反復購買這類能夠形成長期積極效應的旅游者經濟行為而非價值共創[35],但從學術的角度已經承認旅游者在體驗中發揮的作用以及體驗的過程性和整體性。
3.2 社會、文化視角下的體育旅游研究
社會和文化視角與經濟、管理視角雖然各自服從于不同的學科立場,但也是互相聯系的[36]。社會和文化視角正是在承認旅游者的主體地位的基礎上從旅游者的視角展開研究的。在社會、文化視角下的旅游體驗研究曾分別從本真性理論、凝視理論、表演理論、具身理論等范式中汲取營養。
本真性范疇最先由Maccannell[37]提出,經過學術界的不斷擴充和揚棄,逐漸成為旅游研究中的重要范式。在這種理論拓展過程中,Wang[38]在Cohen[39]的基礎上,基于“主觀-客觀”(主觀的自我、客觀的旅游吸引物)的二元對立框架,將本真性進一步細化為三類——客觀的本真性、建構的本真性和存在的本真性,由此豐富了Cohen 提出的單一維度的本真性概念。三維本真性概念分類的背后是一幅由關注旅游目的地轉向關注旅游者的圖景,可以概括為圖9 所示的基本概念的類型學架構,而這種關注點的轉向也給體育旅游內涵的重新確立帶來了新的契機。

圖9 本真性概念的類型學架構Figure 9 Typ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concept ofauthenticity
在圖9 中可以看到每一范疇所關注的焦點不同。客觀本真性主要關涉旅游目的地的真實,與之相對的存在本真性更多地關涉自我真實,正是在這一維度上它成為體育旅游者最重要的價值歸屬。 Rickly-Boyd[40]在攀巖活動情境下討論了存在主義本真,她認為,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攀爬活動更有利于體驗存在主義本真。Steiner 等[41]指出,存在主義本身沿襲了對快樂和自我進行人文解讀的哲學傳統。此時的旅游目的地不過是作為體育旅游者存在的背景而出現的,其真假問題不會影響旅游體驗的質量,而旅游地作為儀式和傳統的載體所彌漫的氛圍(aura)對獲得存在主體本真性非常重要[42]。這一點在體育旅游研究領域中表現最為突出。
在Urry[43]提出的凝視理論中,旅游世界與日常生活世界的差異被凸現出來,成為旅游凝視的動力。凝視賦予旅游目的地以浪漫化的色彩,旅游者也因此得到獨特的凝視體驗。凝視本質上強調的是一種由視覺占主導的單向觀看方式。這種視覺觀看方式帶來了理論解釋上的兩難境地:一方面,由于視覺的選擇性和建構性,有距離感的旁觀體驗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欺騙性質;另一方面,這種觀看之道凸顯了視覺感官而弱化其他感覺器官的作用。凝視的這種明顯帶有賦權色彩的觀看方式很容易導致對對象的非理性判斷。即便如此,在現實中這種情況卻十分常見。在體育旅游領域,人們對帶有某種圣地性質的運動場所(如雪山、陡崖、懸瀑、險灘)的迷狂般地追逐和在場體驗,其實是明顯的凝視行為所激發的現象。
表演理論也是研究者用以解釋體育旅游現象時的理論基礎。例如,有研究者[44]認為:“滑雪者在空中飛翔并表演各種動作,每天不會超過120~180 次這個范圍。”也有學者[45]以戈夫曼的擬劇理論為基礎,分析了那些懷著從眾、炫耀心理,通過參與馬拉松比賽并在賽場上以其“獨特”的表演方式實現自我展示的參賽者。對運動員而言,跑步就是一個表演場,運動技能、健美的身軀以及中產階級的男性氣概在其中被生產并且再生產[46]。按照戈夫曼的理論,人們在任何場所都面臨著前后臺表演之間的行為張力甚至沖突,在前臺的表演過程中帶有一定社會、文化價值觀念的制約,人并不能做到完全意義上的放飛自我,總要按照印象整飾的框架管理在場行為。在體育旅游活動中,由于身體的游戲性或玩耍性介入,表演理論對相關行為的解釋顯然具有新的理論空間,也需要做更多的理論拓展。對以上4種被體育旅游研究者廣泛應用的理論進行綜合可以看出,這4 種理論可能會因體育旅游者個體的身體卷入程度而對其行為形成各具特色的解釋(圖10)。

圖10 體育旅游研究中的范式轉換與身體卷入程度Figure 10 Paradigm shift and body involvement in sport tourism research
從圖10 可以看到不同理論范式所強調的焦點及身體卷入程度。其中,傳統的本真性理論強調客體主導,忽視主體的能動性,旅游者個體的身體卷入程度受制于客觀本真性的可感知狀態,因此,這種身體卷入程度為有限卷入——即使游客謀求的是存在本真性,其本真性感知也會受制于客觀本真性的現實狀態;凝視理論強調視覺主導,表現出身體的部分卷入特征;在表演理論中,雖然整體的身體被卷入,但身體往往作為表演的工具而存在,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基于表演范式的身體卷入是一種形式卷入。與之不同的是,起始于哲學并在認知科學等領域中取得較大發展的具身理論將身體整體(包括身心)視為經驗的感知渠道,因而體現出實質卷入的特點。如果從更高的層次來認識具身范式,具身范式存在對其他范式加以整合的潛質。因此,在體育旅游研究中,如果能夠用具身范式統領各種相關理論并推動理論研究進程,既可以促進旅游者更好地展示身體、移情于觀看的物象以及證明自我存在的本真性,也會有益于體育旅游的知識體系拓展。
4 體育旅游的具身轉向:一種新的本體論認識
具身理論作為解釋旅游體驗現象的核心理論之一,是從心理學的具身認知視角對旅游體驗的心理過程展開研究的。由于旅游場域景觀的多向度以及旅游者尋求認同或差異的旅游動機,具身理論在旅游體驗研究領域表現出強大的理論生命力。謝彥君[47]曾提出“旅游是體驗,體驗須具身”的命題,Small等[48]也提出“具身本體論”的范疇。隨著具身理論在旅游領域的不斷應用和深入探討,具身理論已經初具旅游研究新范式的特點,成為旅游具身范式[49]。旅游具身范式強調旅游者的主體性,關心身體的感覺以及身體與旅游世界的交互關系。
在哲學、社會學、心理學以及一些人文學科的研究領域,隨著語境主義、情境主義、常人方法論、符號互動論等理論的廣泛應用,身體在人類的情境體驗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成為解釋人類心理、社會、文化等范疇的重要概念。在旅游領域中,身體是聯結旅游者個體與旅游世界的通道[49]。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發現,感官感覺是旅游體驗中最基本的具身欲求。為此,一些學者轉而將研究更多地鎖定在騎行旅游、徒步旅游等身體體驗的主題上,如謝彥君等[50]認為徒步旅游體驗在本質上是一種具身化生成實踐。Speier[51]研究發現,瑜伽旅游者的具身實踐有利于保持身體平衡、感受身體內部變化、平衡身心等。然而,作為徒步、騎行、瑜伽等旅游形式的上位范疇——體育旅游,還沒有系統地從具身理論加以探討。事實上,因強調身體參與,體育旅游是典型的具身體驗的旅游類型。羅伯特·埃利亞斯和埃里克·鄧寧在《在不興奮的社會中追求興奮》(The Quest for Excitement in Unexciting Societies)中,假定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習慣化,與像足球、英式橄欖球、曲棍球和美式橄欖球這樣的體育運動的流行之間有一種相反的關系。Elias 等[52]進一步指出體育在這個文明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中的關鍵作用,借由體育有限度地釋放情感和張力,提供一種快樂的氛圍和一種可控的興奮,促進社會的和諧。《運動改造大腦》[53]中的研究也表明,鍛煉身體就是鍛煉大腦,運動可以對身體、大腦、人際關系3個方面產生積極影響。因此,很多體育旅游者把運動視為一種生活方式[54-55]。
體育旅游的這種身體在場甚至身心在場的總體特征使得具身理論在解釋體育旅游現象時獲得了空前的廣泛性和深刻性。進一步深入地對體育旅游相關研究文獻加以梳理發現,以具身體驗理論為支撐的體育旅游研究已經獲得了諸多重要的本體論命題,從而凸顯了一種具身體驗轉向的整體研究勢頭。下文對這些關鍵命題以及相關的研究領域的拓展趨勢逐一進行梳理和評述。這些不同的命題展現了體育旅游在性質、特征、意義以及效應方面的豐富性,也預示了未來體育旅游研究的多元面向。
4.1 體育旅游是以本體覺和運動覺為主的具身體驗
一般而言,旅游體驗涉及3種不同類型的感覺:感官覺、本體覺和運動覺。3 種感覺的結合使體驗中的身體能夠在旅游對象物中產生身臨其境的感受,并獲得真實且強度更高的體驗。Waitt 等[56]通過研究節事中的游客體驗發現,聽是神經的、心理的和文化的過程,傾聽的方式對于節日空間的意義和體驗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Schwarz[57]探查了不同參與模式的游客對自然聲音的不同偏好,發現聲音對旅游者的身體和心智有重要影響。嗅覺體驗有著悠久的歷史,如Adler[58]指出,在整個19 世紀,空氣療法的長期流行,伴隨著嗅覺體驗,持續地影響旅行目的地的時尚。與視覺的抽象品質相比,嗅覺提供了一個與環境之間的直接接觸。芳香可以激起對地方的記憶,有助于保持地方感,并且“在建構和維持主要的社會品位的區隔上起到重要作用”[59]。觸覺體驗同樣為旅游者所重視。在現代濱海旅游之前,海水浴是歐洲上層社會流行的健康理療方式,其對觸覺體驗的強調遠遠超過對視覺景觀的審美需求。即使發展到現代大眾旅游時期,濱海旅游的3S(陽光、沙灘、海水)主題也緊密聯系于觸覺感知。
由于旅游世界中景觀存在的多維度屬性,感官覺為旅游者提供了基礎的感知方式。體育旅游者對旅游世界的感覺并不完全或僅限于依靠感官覺,而是更主要地依賴本體覺和運動覺,如蹦極和激水漂流體驗中的身體體驗[60]。體育旅游的具身體驗因身體的強參與而成為一種深度休閑[61]。Chronis[62]指出,本體覺指在物理舞臺上的位置和姿勢感知,運動覺是對手臂、肌肉等個人身體運動的感覺。體育旅游與一般旅游體驗的具身感知相比,本體覺和運動覺更為突出。Lewis[63]對比了冒險旅游和都市生活中的身體形態,認為相對于現代生活中以視覺為主導的被動的身體,攀巖中的身體是動覺主導的自主的身體,攀巖旅游者以手腳等軀體動覺體驗代替了眼睛的觀看之道。因此,體育旅游中的具身體驗更具能動性,強烈的身體能動性伴隨著積極的身體體驗。圖11 展示了體育旅游中的身體感知層次。

圖11 體育旅游具身體驗中的身體感知層次Figure 11 The level of body perception in the embodied experience of sport tourism
視、聽、味、觸等感官覺是體育旅游基本的身體感知層次,如Shipway 等[25]引述受訪者的陳述,“有很多安靜、美麗的小路,穿過樹木,真是太適合騎車了,我不知道在山間騎行的感覺這么好”。在感官覺基礎上,以本體覺和運動覺為主的身體覺是體育旅游體驗的主要身體感知層次。這2種感覺不僅作為過程性體驗而存在,而且還是旅游者欲求的體驗目標,即對身體的探索。具體而言,通過身體的快感和痛感的交錯得以實現身體喚醒,進而實現身體暢爽體驗(flow experience)[50]。暢爽體驗是一種理想的內部體驗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對過程的體驗本身就是樂趣和享受,并產生對運動過程的控制感[64]。Rickly-Boyd[40]的研究則給出了一個攀巖的體育旅游者對暢爽體驗描述的例子:“當你在攀巖時,你沒有時間想別的事情,根本沒有時間思考。你僅僅是很高興地攀爬,甚至意識不到時間。”類似的情況在海上帆船體育旅游項目中也具有普遍性:“我感到水沖過腳和腿……,(手)讓帆與風保持美妙的平衡,當從一個浪頭滑下時,那種喜悅和感受是完美的。”[65]這些研究無不表明,各種高卷入度的體育旅游項目能使旅游者不斷在某種身體的自我超越中感受一種完美的暢爽體驗。
4.2 體育旅游是實現高層次旅游體驗的旅游類型之一
旅游體驗能夠形塑人們的個性和生活,但這種影響力的強度和效度會因不同的體驗類型而有所區別。根據既有的研究成果,旅游體驗對個體的積極作用可以分為“逃逸—轉換—發現—超越”幾個層次。逃逸(escape)作為旅游的動機之一很早就被注意到[66],但就其給旅游者所造成的影響而言,它只是為遠離沉悶或痛苦的日常生活體驗提供了希望。Chase等[67]提到人有回返過去的意愿,特別是今天的人們想從復雜而繁忙的環境中逃逸出來,返回到簡單的、較少墮落的過去。這種轉換為人們提供了恢復正常的身體和心理機能的機會。在這里,假期成為生活興趣的擴展而不僅僅是對生活的逃避,使游客成為更具主動性的實體,在對奇遇的追求和體驗中擴展知識、獲得意義,精神得以提升,自我得以實現。旅游體驗的這種動力機制使得旅游既是具有明確時空特點的身體旅行,也是尋求發現和改變的精神之旅[68]。在旅游中,旅游者如同一個游牧者,遠離靜態和異化的位置,在一個個旅游情境的轉換和奇遇的體驗中,勾畫出非線性的生活發展藍圖,并從中反思、解構、重建自我。
因身體參與的強度高于其他類型的旅游形式,因而體育旅游可能實現較高層次的旅游體驗。這種由身體參與帶來旅游體驗質量的提升與挑戰因素密切相關,因而可以采用“身體卷入—挑戰—技能”模型加以解釋[69]。在該模型中,挑戰與技能之間的均衡關系是實現旅游體驗的關鍵因素。無論何種形式的體育旅游都涉及不同程度的身體卷入。一般而言,身體卷入程度高,則挑戰難度大;身體卷入程度低,則挑戰的難度降低。挑戰與旅游者本身的技能水平相關。三變量的關系可以用圖12表示。
在圖12 中,根據身體卷入程度的不同可將體育旅游分為低身體卷入和高身體卷入類型。低身體卷入類型,如Gyimóthy[70]指出的“有時那些觀眾就是坐在那,等待按一下快門,記錄一下精彩瞬間,然后去跟家人、朋友回味”;而高身體卷入型是體育旅游中非常典型的涉及高強度身體參與的類型,如徒步、騎行、各種極限運動等。在圖12 中,由低挑戰、低身體卷入以及低技能水平組成的虛線正方形范圍代表了較低層次的體驗水平,對應的是低卷入型體育旅游;由高身體卷入、高挑戰以及高技能水平組成的實線區域則代表了較高層次的體驗水平,體育旅游中的參與型通常處在這一區域中。在高身體卷入類型中,旅游者的體驗經由挑戰和技能水平的均衡得以實現。在圖12 不同區域的位置上,旅游者因“挑戰>技能”或“挑戰<技能”得到超過預期或低于預期的旅游體驗,最終決定是否獲得暢爽體驗。

圖12 身體卷入—挑戰—技能模型Figure 12 Body involvement-challenge-skill model
4.3 旅游者與旅游情境交互作用形成體育旅游具身體驗
正如經濟、管理視角下的體驗研究所倡導的“價值共創”范疇一樣,體育旅游的具身體驗是在旅游者與旅游體驗情境交互的過程中實現的,并且這個交互作用過程持續存在。旅游體驗的情境分為時間情境和空間情境。Crouch[71]認為,旅游場所比日常場所更加豐富,與具身方式非常一致。Higham[33]將這一觀點具體應用于體育旅游情境并指出,如果“場所是充滿了意義的空間”,那么體育旅游就是充滿了旅游目的的運動。體育旅游提供了特別強的場所體驗,是一種能身心共在的旅游行為,同時也包含了對物理環境的美學理解。因此,具身體驗來源于身體、場景、身體與場景之間的互動三方面的協同作用[72]。
此外,游客體驗產生于當時具體的情境,同時也離不開之前生活經歷的影響,因此,可以從時間的角度將旅游情境分為前攝情境和當下情境。“每一個體驗都是在生活的延續性中產生,并且同時與其自身生命的整體相聯。”[73]這一點正如梅洛-龐蒂[74]所提出的那樣,“我們的身體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層次,習慣身體的層次和當前身體的層次”。在旅游體驗中,當下情境是由“當前身體”所感知的,對應于旅游世界,而前攝情境受到“習慣身體”的慣性影響,對應于旅游者的日常生活世界,從而在體育旅游體驗的時間情境與空間情境中形成了具身體驗的交互作用(圖13)。

圖13 體育旅游具身體驗的情境交互模型Figure 13 The tourism situation composed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embodied experience of sport tourism
在圖13 中,時間情境和空間情境是社會情境的2個維度,旅游者的身體處于情境的中心,這一旅游場域是旅游者作為游客身份需要調動運動覺、感官覺、本體覺進行感知的情境。相對而言,由日常生活世界的空間情境和前攝情境的時間組成的情境正是游客在旅游場域中具身體驗時的參照情境,但二者在不同的體驗類型中可以相互轉化,如下文提到的懷舊旅游體驗類型,感知情境就轉化為參照情境。有學者進一步從場所和交往的角度對其進行解釋。Weed 等[18]指出,在時空框架的基礎上,體育旅游包含了活動、人和場所的交互作用,游客跟當地人,也跟群體中的其他人進行交互,通過分享從而形成記憶深刻的獨特的共同體驗[22],塑造一種群體身份感,即Turner 所謂的共睦態(communitas)。Lamont[24]在分析環法自行車賽的研究中就指出這種騎車旅行不僅僅提供了個人成就感,分享自己的表現也是快樂中非常重要的成分。與此同時,社會和文化互動也在潛移默化地進行。體育旅游者將自己的文化背景與他們對活動或地點所承載的歷史文化意義的理解連接起來,從而使旅行成為一個追尋自我發現和精神意義的神圣游程[75]。在這一語境當中,體育場、體育館甚至可能被視為一個神圣的空間[76],被用來共享社會意義體驗。
此外,性別、種族、民族、國別、年齡、階級、殘疾程度等人口統計變量也往往被研究者納入體育旅游的情境研究當中,用以考察體育旅游具身體驗所呈現的人口學特征。Mayoh 等[77]特別強調通過體育活動,女性具身體驗的身份以及傳統的男性主導的社會對女性身體所形成的壓迫。類似地,Fullagar 等[78]從后結構女性主義的角度探究了澳大利亞女性游客的騎行旅游體驗,揭示了在舒適、安全和愉悅感知中身體的中心性。還有研究[79]發現,女性游客在旅游中的性行為和體驗在自我探索、抵抗和自我轉換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這些研究吸收了德勒茲、希林等人積極的身體觀,將身體視為生成的過程和事件而不是靜態的既定物,注意到身體既受社會系統的塑造,又構成了社會關系的基礎。因此,只有關注于“身體能做什么”而不是“身體是什么”[80],才能在身體與社會的復雜關系中錨定身體的能動性,從而增進人們對體育旅游作為一種社會活動所具有的更廣泛社會意義的感知。
4.4 體育旅游具身體驗中的懷舊體驗
盡管Gibson將體育旅游分為參與型體育旅游、觀賞型體育旅游、懷舊型體育旅游,但懷舊的情愫事實上更可能存在于每一分類中,而不僅僅獨屬于懷舊型體育旅游。若從認同與否的角度將懷舊和差異作為旅游需要的對立兩極置于一個連續譜的兩端,那么,體育旅游很可能更偏向懷舊的一端。原因在于,懷舊對體育旅游者的前攝情境要求比較高。這里的前攝情境不僅僅是游客過往的日常生活情境,更多的是一種源于職業、專業和興趣的情結。這與尋求差異型的旅游者截然相反。
換言之,懷舊體驗更多地關注由旅游世界中的懷舊景觀引起的能夠連接旅游者前攝情境中回憶、情感等內容。旅游世界的當下情境所起到的作用是通過體驗場景而連接到旅游者的當下身體。由于探新求異的旅游動機,因而差異體驗更多關注當下情境。此時,旅游者的前攝情境是作為參照情境而出現的。Gaffney 等[81]提出,體育環境有一種特殊的氛圍,過往的記憶通過視、聽、觸、嗅和味這5 個感官得以實現。此外,Gordon[82]指出,懷舊體驗中運動、情感和記憶聯系在一起,一個連接著記憶的場所就很容易激活懷舊情感。Ramshaw 等[83]對戶外冰球體驗的研究表明,懷舊情感跟冰球場的寒冷和家的溫暖都有關系。因此,體育旅游中的懷舊體驗不僅借助于當下情境的多感官喚起,而且還與旅游者的前攝情境有很大關系。
4.5 體育旅游具身體驗中的迭代體驗
即使是普通的游客,其在當下時空情境中的體驗也一直處于動態的變化之中,而體育旅游由于更多地可以溯源于規則性的游戲,因此,在時序意義上的行為和心理賡續、迭代就更為顯著。通常,旅游者的旅游體驗包括行前和游后2 個階段。在行前階段,旅游者的生理和心理狀態也都不是靜態的,旅游體驗也不是一個閉合過程,而是具有某種動力學特征,處于持續的進行[84]和建構[85]之中。這一點在體育旅游當中顯得更為突出。
對于體育旅游者而言,每一次具身體驗都處于時間和空間的流動中。作為中心的身體具有銘記這種流動性體驗的記憶。每次體驗都是基于上次體驗的累積效應,游客的身體既是體驗的感覺機體,也是體驗的目標,因而這種體驗的積累性或疊加性十分明顯。每次具身體驗都可能是對上次體驗的某種超越,從而構成了新的自我。正如齊美爾所言,這些形式為創造性的生命構筑了框架,不過創造性的生命很快又會超越這些形式[86]。體育旅游者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個“我是”的身份定位,通過體育旅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框架(形式),測試了“我能”,增強了某種能力,而返回日常生活中時,這個“我是”的身份定位便獲得某種程度的改變。簡言之,就是一個“劃定邊界—超越邊界— 重新劃定邊界”的迭代循環。 類似地,Grimshaw[87]基于梅洛-龐蒂的論述,指出身體通過掌握新技能而處在一個學習新意義的持續過程之中。身體在獲取新技能、新能力的同時,人體驗身體的方式也在持續轉換中。圖14 展示了體育旅游可能形成的心理和生理迭代的過程。

圖14 體育旅游體驗中的心理和生理迭代循環Figure 14 Iterative cycle of psychology and physiology in sport tourism experience
5 結論
從總體上看,體育旅游不僅是一項經濟現象,在現代社會的背景下,更多地成為旅游者親近自然、理解文化、發現自我的社會現象。體育旅游動機也不僅出于體育賽事的旅游拉力,更多地是作為旅游者本身的一種內在需要。因此,從旅游者視角探討體育旅游的本體論問題在現今的時代背景下更能體現理論創新的訴求。
在對體育旅游相關文獻進行定量分析和思辨的基礎上,本文抽象出體育旅游的本體論認識,即體育旅游是一種身心在場的異地具身體驗。這與以往從經濟、管理視角看待體育旅游的觀點不同,是一種新的本體論認識。對體育旅游者而言,身體在旅游體驗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僅是感知旅游世界的方式,更是體育旅游者實現身體體驗的欲求目標。體育旅游也因此成為以運動覺和本體覺為主、感官覺為輔的具身體驗。從某種程度而言,這是一種由身體記憶的、具有累積效應的迭代體驗。這種深度體驗是游客通過深度沉浸于某種運動性的時空體驗情境并與之交互而實現的,其中游客的身體處于時空框架的中心。在體育旅游的類型中,參與型體育旅游的身體卷入程度最高,因而是實現較高層次旅游體驗的類型。
在旅游具身范式的觀照下,身體成為實現旅游者主體性的重要因素。相較于一般強調感官體驗的旅游形式,體育旅游是典型的強調身體卷入的旅游類型,因而其具身體驗的層次和強度均處于高位。實質上,正是由于這種具身體驗位格上的獨特性使得體育旅游成為一種極富魅力的旅游形式。
作者貢獻聲明:
謝彥君:確定論文選題,設計論文框架,撰寫、審核、修改論文;
吳 凱:收集、分析文獻,設計論文框架,撰寫、修改論文;
于 佳:收集、分析文獻,撰寫、修改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