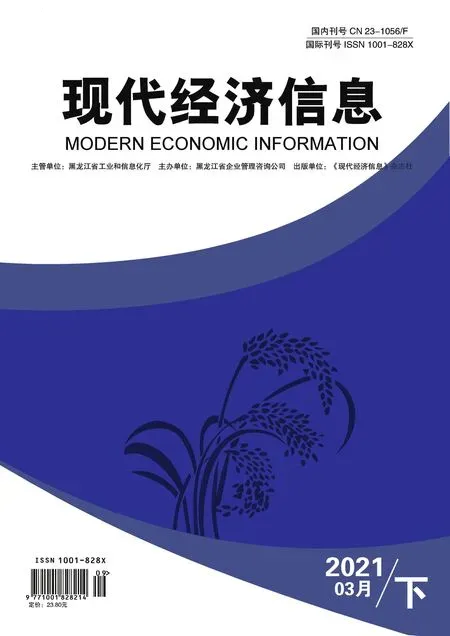醫改背景下公立醫院政府會計制度核算難點問題的思考
沈冬梅 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各公立醫院于2019 年開始實施新政府會計制度,身處醫改暴風眼使其會計核算也面臨更多挑戰。公立醫院面對藥品耗材加成取消、國家公立醫院績效考核、DRG、DIP等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等醫改政策,使得其會計核算特殊于其他事業單位,也更具有挑戰。本文結合實際工作,分析醫改政策下的會計核算遇到的難題,以期為其他同行提供參考。
一、醫保結算差額核算
(一)制度規定
根據《醫院執行 〈政府會計制度——行政事業單位會計科目和報表〉的補充規定》(財會〔2018〕24 號,以下簡稱醫療行業補充規定),公立醫院的結算差額科目核算“因醫院按照醫療服務項目收費標準計算確認的應收醫療款金額與醫療保險機構實際支付額不同而產生的需要調整醫院醫療收入的差額”。
此規定與2012 年開始執行的《醫院會計制度》中關于結算差額的定義無異,雖然結算差額自出臺后便飽受理論界抨擊,如張艷君、于潤吉(2017)[1]、陳友平(2014)[2]、梁秀林(2013)[3]均認為“結算差額”不能沖減醫療收入,而作為壞賬損失核算或使用事業基金對不能收回的應收賬款進行處置更為妥當,但在此輪政府會計制度改革中仍選擇結算差額沖減醫療收入。
(二)醫改背景分析
1.醫保付費(支付)方式改革。醫保付費(支付)方式改革的改革,各地進展不一,總額預付、單病種結算、DRG、DIP 支付等。付費(支付)方式的改革,清算規則也逐步演化,絕大部分的清算取數規則為全年醫保數據,使得各公立醫院必須到醫保年度的次年才能具體金額,給會計核算帶來巨大挑戰。公立醫院在次年收到清算款時,結算差額的核算規則面臨權責發生制拷問。實踐中每個單位的做法不一致,造成不同單位的醫療收入可比性較差,按照是否嚴格按照制度要求沖減醫療收入分成兩大類做法:
(1)減少醫療收入
結算差額核算的初始假定,應該是清算事項可以在醫保年度當年完成,故沖減醫保年度當年醫療收入是合理的。但在醫保付費(支付)方式改革的大環境下,醫療保險機構需要提取全年醫保數據進行清算,故清算時間推遲到次年。當各公立醫院在醫保年度次年獲取結算差額具體金額后,按照制度要求沖減醫療收入時,又會出現兩種做法:一是減少醫保年度(當年)醫療收入;二是減少清算年度(次年)醫療收入。
一是減少醫保年度(當年)醫療收入。部分會計人員認為按照權責發生制,第二年才清算出來的結算差額不能直接調整收到清算資金年度(次年)的醫療收入,而應通過“以前年度盈余調整”科目進行調整。此種做法的缺點是,醫保當年的醫療收入虛高、醫療盈余虛增。
二是減少清算年度(次年)醫療收入。部分會計人員認為,既然結算差額每年都會發生,且每年金額差異較小,結算差額調整收到清算資金當年的醫療收入。雖然收支匹配性差一點,但從長期來看對醫療收入、醫療盈余影響較小。此種做法的缺點,違背權責發生制原則,不同年度間結算差額數據差異較大的情況下會造成醫療收入、醫療盈余數據失真。
(2)不減少醫療收入
一是做壞賬損失。收到醫保清算款時,將不能收回的差額部分做壞賬損失處理沖減壞賬準備,實質上是將收不到的醫療收入作為醫保清算當年的支出事項。此種處理方式的缺點,不符合會計制度對結算差額的核算要求,虛增醫療收入、醫療活動支出。
二是留在應收賬款。收到清算款時,不能收回的差額部分既不減少醫療收入,也不做壞賬損失,而是留在“應收醫療款”借方。此種做法的缺點,應收醫療款已確定不能收回,不再符合資產的定義,應當申請資產處置。實踐中,由于醫療保險部門強制要求醫院沖銷應收賬款,此種做法已較少存在。
2.國家公立醫院績效考核。該項工作自2019 年拉開序幕以來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整個指標體系共55 個指標(2020 年版增至56 個)中有14 個指標直接取數自《全國衛生健康財務年報》,其中4 個指標與包含結算差額的醫療收入有關[4],各醫院基礎數據的可比性成為此項工作的重中之重。從第1 點分析來看,各公立醫院對結算差額的處理方式并不統一,甚至同一單位不同年度的處理方式也不一致的情況下,使得各公立醫院與醫療收入有關的指標在橫向、縱向比較時,數據可比性大打折扣,進而影響考核結果的指揮棒作用。
(三)思考
實踐中,在“醫院領導的阻力”、“醫療保險清算不及時”、“會計人員的糾結”等有關因素影響下,更多的公立醫院放棄使用結算差額科目[1],選擇不減少醫療收入的做法,只有少部分公立醫院選擇減少醫療收入。公立醫院結算差額會計核算的不統一,造成了不同醫院之間的數據可比性較差,有必要對會計核算方式進行統一。通過對各種做法缺點分析可以看出,現行醫改政策下各種做法都不能很好地反映醫保當年的醫療收入,理論界應當探討出一種符合現行醫改政策下的會計核算方式。
本文認為“結算差額”應當減少醫保年度醫療收入。“醫療收入”科目,核算的是公立醫院銷售醫療服務實現的收入,當醫院與醫保機構簽訂醫保定點協議時,醫保機構和患者就成了醫療服務的購買方,其中醫保機構支付記賬部分,患者支付個人部分。雖然按照物價規定項目收費標準計算的總額是確定的,但由于醫保定點協議中規定的醫保支付條款會造成最終結算金額與前者會產生差異,即最終合同結算價格存在不確定性。當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醫療收入的確認不能以按照物價規定項目收費標準計算的總額為準。此理解與《醫療行業補充規定》第十條“關于醫療收入的確認”規定不符,但本文認為第十條的規定本身就與其結算差額的定義和科目設置存在矛盾之處,若“結算差額”是“醫療收入”的下級明細,即兩者存在包含關系,則“醫療收入”的最終結算金額就不可能是“按照醫療服務項目收費標準計算的金額”。因此,本文認為可以借鑒企業會計準則對存在可變對價合同收入的確認原則,在合理預計結算差額的基礎上,確認當年的醫療收入(二級科目結算差額)。通過增設“應收醫療款-預估醫保結算差額”科目進行會計核算,減少醫保年度當年的醫療收入。結算差額確認后,月末不再進行按比例沖減收入,保留在“醫療收入”科目的下一級,期末一并結轉到“本期盈余”。
二、勞務派遣人員工資福利待遇核算
(一)制度規定
政府會計制度要求“事業支出”科目應按照《政府收支分類科目》中的“部門預算支出經濟分類科目”的款級科目進行明細核算,由單位承擔的各項人員支出也需按照不同的經濟分類科目進行核算。依據最新2021 年度《政府收支分類科目》,編制內在職人員、編制外長期聘用人員的支出在“工資福利支出”科目核算,而勞務派遣人員、臨工的支出在“商品和服務支出”下的“勞務費”科目核
算[5]。
(二)醫改背景分析
我國公立醫院用工形式具有多元化特性,主要體現在以事業編內為主,編外勞動合同聘用人員、編外勞務派遣人員、臨時工等為輔,其中勞務派遣的用工形式最為普遍。根據法律規定,勞務派遣員工僅限于“臨時性”、“輔助性”和“替代性崗位”使用。隨著醫改的不斷深化,公立醫院面臨編制不足、人民群眾對公立醫院醫療需求不斷增長的雙重壓力,醫務人員尤其是護士短缺問題嚴重。為了緩解供需矛盾,公立醫院只能通過大規模使用勞務派遣的用工模式補充護士、技師等主系列醫務人員,勞務派遣用工比例(勞務派遣用工形式的職工人數/總職工人數*100%)大大超過法律規定的10%[6],且用工協議一般為2—3 年,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臨時性”、“輔助性”和“替代性崗位”要求。
公立醫院的勞務派遣用工模式有一定的行業特殊性,繼續列支“勞務費”會計科目是否合理值得探討。
(三)思考
勞務派遣員工支出應納入“工資福利支出”核算。從目前醫療行業發展現狀和人力資源供需來看,公立醫院選擇勞務派遣用工形式在短時間內不會得到太大的改善。勞務派遣員工任職護士、技師等主系列崗位、數量占總人數的比例遠超10%、合同簽訂年限超過兩年,為公立醫院承擔了較多的醫療任務、為病人提供了較多的醫療服務,應按照會計核算中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將其工資報酬納入“人員工資福利支出”核算,而不是在“商品和服務支出”下的“勞務費”科目核算,以期更合理地反映公立醫院所有人力成本,以及與人員數量有關的人力資源效率分析指標,為醫院運營決策分析提供準確的決策依據。
三、藥品收支(零加成)核算
(一)制度規定
按照醫療行業補充規定,藥品收入、藥品費應分別在收入和支出的明細科目下進行單獨核算,要求兩者應具有匹配性。
(二)醫改背景分析
近幾年,隨著藥品加成、耗材加成的取消,藥品、耗材等物資的精細化管理變得越來越重要。但大部分醫院的信息化建設水平還處于信息孤島狀態,缺乏有效的互聯互通,例如收費系統、庫存管理系統之間缺乏互聯互通,由于取數時間差等原因導致部分年度公立醫院的年度藥品收入大于藥品費,收支嚴重不配比,這在藥品零加成的政策背景下顯得突兀、難以解釋。收支不配比、數據質量差,將不利于醫院進行運營分析管理。
(三)思考
收支配比程度的提高有賴于公立醫院的業財融合、信息互聯互通。為了提高業務收支的匹配度,需要將醫院“業務信息”和“財務信息”進行互聯互通,使得與業務信息高度融合的“財務信息”能夠更準確地反映醫院的經營情況,例如臨床醫生在業務系統開出醫囑后,相應的醫療收費項目與物資消耗進行一一匹配,并及時將相關信息傳輸至財務核算系統自動生成記賬憑證,收入和成本數據高度匹配,將不再出現藥品收入大于藥品支出的情況,會計信息的及時性、配比性都得到了提高。通過對高質量大數據的監控和分析,發現醫院運行中的問題并解決問題,實現醫院運營發展提質增效。
四、結語
新政府會計制度的施行,對公立醫院的業務流程改造和信息化建設都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公立醫院需要站在新起點,對標新要求做好會計核算、財務管理的基礎工作,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和財務管理水平。同時,希望財政部門、業務主管部門能進一步擴大政府會計制度實施的基層調研,?了解公立醫院在執行中的困難和想法,并結合行業特殊情況采取有針對性的方案,同時通過案例的推廣提高會計制度執行的統一性,增強會計信息的準確性、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