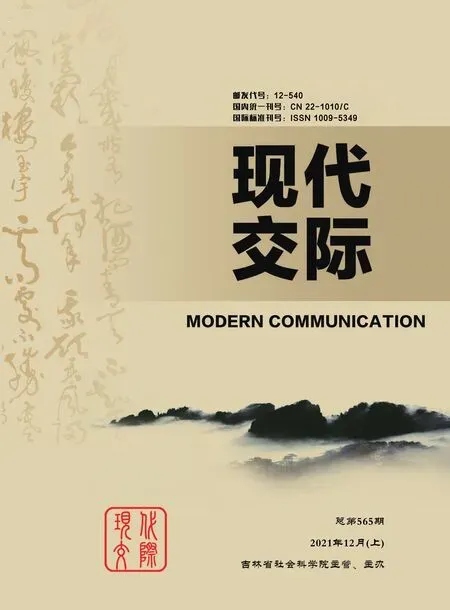“社區+差異化”健康志愿服務模式構建研究
沈秋歡
(南京中醫藥大學 江蘇 南京 210046)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將“健康中國”上升為國家優先發展戰略。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天津市社區時對志愿服務做出重要指示:志愿者事業要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同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肯定志愿服務者在疫情防控、社會治理中的作用。社區健康志愿服務在為老服務、健康促進等多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形成了“居民健康+志愿服務”的資源優勢疊加效應。然而,社區居民日益增長的健康服務需求與有效供給之間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探討如何優化城市社區健康志愿服務供給模式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一、文獻綜述
志愿服務是公民個人基于道義、信念、良知、愛心和責任,利用自己的時間、技能、資源、善心為他人、社區和社會提供的一種公益性服務。健康志愿服務,即涉及與健康相關的志愿活動。從健康志愿服務的內容來看,涉及范圍較廣,如精準扶貧中的健康志愿服務參與,在國家健康扶貧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在養老服務需求中,開展以“老年人服務老年人”的服務模式,滿足了老年居民多樣化的健康服務需求,實現了老年人健康自我管理。隨著互聯網、大數據、新媒體等現代技術和媒介的發展,基于互聯網資源利用的健康志愿服務技術的創新研究也是一個聚焦點。[1]有些志愿者團隊為科學管理而構建“樂助”社區健康志愿服務APP平臺。醫護人員及醫學類大學生是健康志愿服務的重要力量,在新技術、新媒體的利用中也做了大量探索。陸人杰等(2019)從“主位訴求”角度,提出建立“新媒體與健康教育協同發展”醫院志愿者管理模式。整體上看,目前的研究多為健康志愿服務實踐活動工作經驗的總結,對志愿活動具體項目設計運行情況的介紹,缺乏基于公共管理視角對互聯網時代健康志愿服務的需求、供給、成效等問題的回應;規范的研究方法運用較少。
二、社區健康志愿服務的現實困境
1.互聯網時代的挑戰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新媒介等的普及應用,既為健康志愿服務的賦能增效提供了新機遇,也對服務的治理升級、制度升級提出了挑戰。現代互聯網技術,通過對數據資源的挖掘、整合、決策、利用,極大地發揮數據優勢,使精細服務、精準服務、個性服務的需求識別、供需匹配、高效服務成為可能。健康志愿服務與互聯網技術的融合是創新志愿服務的趨勢,對構建社區健康志愿精準服務的長效機制有重要意義。與此同時,互聯網技術催生的智能社會建設對健康志愿服務項目開發創新、服務方式創新、服務模式創新、服務渠道創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實踐中,社區健康志愿服務目前還面臨著諸多問題,如:參與的渠道較為單一,主要依靠單位組織;服務的專業性程度不夠,在特定專業技術和與服務對象的溝通專業能力方面尤其突出;可持續性和常態化供給能力不足,志愿服務活動呈現短期化、運動化式的特點,缺乏常態化、制度化、可持續性的供給已經成了健康志愿服務中的一個難題;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生活方式的改變,公眾對健康志愿服務的總量和需求都在發生變化。[2]借助互聯網技術、發揮技術服務的優勢,尋求實踐問題解決的新路徑,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方向。
2.服務對象需求評估的不足
目前在理論研究和實踐層面上,健康志愿服務都聚焦于服務者(供給側)角度的考察,考察較為精細,完善,包括健康教育志愿者服務參與、管理等機制研究,與衛生健康相關的志愿服務品牌項目建設,健康相關的志愿服務對志愿者(尤其是大學生志愿者)的教育效果等。從范圍更廣的志愿服務的相關理論和實踐經驗總結來看,也側重從服務者(供給側)的角度考察個體、人力資源特征、生命歷程、社會情境等影響志愿服務的因素,從全過程角度(吸納—培訓—績效—團隊等)探討志愿服務的組織管理及志愿服務產生的結果與影響,如個體層面的心理收益和在社會治理層面的意義。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層面的研究,都很少從被服務者的需求角度來考量健康志愿服務的資源分配。精準掌握健康志愿服務需求,是實現供需對接、解決供需脫節、創新健康志愿服務方式、實現健康志愿服務資源最優化利用的前提。但是,現代健康理念涵蓋了疾病治療和保健預防,內涵范圍很廣,需求范圍大且多樣,這大大增加了精確評估社區居民健康需求的難度。
3.供需偏差現象
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社區菜單式志愿服務,志愿服務項目化運轉與管理,在志愿服務的供給輸出方面極大提升了供給內容的精準性,由此促成了服務效能的提升。不可否認的是,在志愿服務的實踐中,對志愿服務供給側需求評估不足容易產生供需偏差現象。公共管理學家薩拉蒙志愿失靈現象分析的框架中提到,特殊主義和業余主義是志愿部門的兩項重要弱點。[3]志愿組織資源投入時會傾向集中關注某些特殊亞群體,造成服務覆蓋面不足和重復服務之間的雙重矛盾;而業余主義則強調了供需不匹配情況的實踐困境,例如對更需要醫療補助或就業訓練的人群提供道德全解和宗教服務。哪怕僅僅是從服務供給側來看,志愿組織的組織方式、服務類型與志愿者期待之間也有一定的偏差。從南京市370名社會公眾的調查結果來看,公眾對公益志愿類活動參與意愿整體較高,除了捐獻遺體器官、造血干細胞,對相關活動的參與意愿程度在50%以上。但是,公眾對志愿活動的服務方式和類型要求多樣化,有受訪者希望公益志愿類活動和參與者自身需求相結合,比如通過競走的方式,促使參與者強身健體,也能順便幫到他人,希望公益志愿類活動和環保掛鉤,在幫助他人同時為改善環境出一分力。
三、基于“社區+差異化”的健康志愿服務供給模式構建
1.健康需求評估
“社區+差異化”健康志愿服務供給模式構建的第一步是健康需求評估。健康志愿服務的供給需要以居民需求為導向,這就需要建立需求評估機制,可以更加準確地把握社區居民的需求狀況,從而最大限度地解決供給與需求錯位問題,推動志愿服務組織由松散型向組織化、志愿服務活動由階段性向常態化轉變,實現志愿資源有效整合、志愿服務規范有序。由于現代健康理念涵蓋了疾病治療和保健預防領域,健康需求范圍也增大且多樣化了。從整體上看,可以將居民健康需求分成健康保健型和疾病治療型兩大類。健康志愿服務應在對這兩大類健康需求評估的基礎上精準開展。[4]在現實中,精確評估社區居民健康需求是一個難題,需要建立一般性評估和重點性評估結合的多輪評估機制。
“一般性”健康需求評估針對全體社區居民,按照現代健康理念,從生理、心理、社會功能三個維度出發,結合對居民健康素養現狀的評估,了解普通居民健康促進的一般性、日常性需求;在此基礎上,更有針對性地提升目前在健康志愿服務中開展較多的健康教育工作質量,在后續服務中有針對性地加強干預力度。“一般性”的居民健康需求可以歸入“健康保健型”需求類別中。“重點性”評估針對社區中需要重點健康幫扶的對象,結合健康中國建設和新時代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推進,以及健康志愿服務現有的有限資源,重點幫扶對象主要為危重患者及家屬,尤其是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患者和危重患者家庭。以江蘇省為例,由于在“十三五”期間精準脫貧取得突破性進展,截至2019年12月31日,江蘇省脫貧率達到99.99%以上,目前還剩6戶17人未脫貧。因此,健康扶貧重點對象主要轉變為相對貧困的對象,其識別的途徑包括:在有關部門建檔立卡的家庭,通過街道、社區平臺的了解、社區居民訪談,在“一般性”健康需求評估中的篩查,慈善公益社會組織中的登記備案等。“重點性”的居民健康需求可以歸入“疾病治療型”需求類別中。這些患者除了需要接受醫療機構的正規救治外,對健康志愿服務的需求程度相對較高。
2.搭建“社區+”服務聯動平臺
“社區+差異化”健康志愿服務供給模式構建的首要環節是搭建“社區+”服務聯動平臺。在現有的健康志愿服務實踐中,社區更多的只是作為鏈接社區內部居民和外部健康志愿服務供給者的“聯系人”。實際上,社區是健康志愿服務的供給者和接受者協調對接的最基層、最直接單位,在健康志愿服務實踐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最大程度發揮社區平臺應有的核心作用、鏈接內外的關鍵樞紐作用,將社區平臺打造為對接居民需求、健康志愿服務資源的集合體、居民健康志愿服務的供給載體,在優化、升級、構建健康志愿服務模式中具有重要意義。
從社區健康志愿服務的現狀出發,在現代健康理念的基礎上,以居民一般性的健康促進需求和疾病患者支持服務的需求為精確指引,建設“社區+”服務聯動平臺,這需要借助互聯網和現代信息技術建立社區健康服務需求信息庫。信息來源是針對社區居民一般性評估和重點性評估相結合的多輪健康需求評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等共享社區的居民健康信息等多種渠道。通過收集、分析和處理社區居民健康需求的信息數據,能識別社區居民的健康保健型和疾病治療型的具體需求、健康幫扶重點對象及其需求,并能根據現有狀況探測社區居民未來的健康需求趨勢。[5]同時根據社區居民的需求狀況進行分類,為不同類型需求的社區居民提供差異化服務,實現服務資源與需求精準匹配,為克服普惠制供給不足打下基礎。
3.統籌健康志愿服務供給資源
“社區+差異化”健康服務供給模式需要有效整合目前參與社區健康志愿服務的社會組織和相關事業單位,如醫療機構、醫學院校、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健康服務機構、相關企業、醫務社會工作者等具有專業背景的個人、政府等多元主體和多方資源。整合供給資源,社區服務聯動平臺要進行統籌,根據社區居民需求分類,為健康保健型和疾病治療型的居民和家庭在供給主體、供給內容、供給方式上提供差異化組合。[6]在供給主體資源上提供社會組織、政府、市場的多元組合機制;實現基于精神慰藉、醫療照護、日常生活照料、健康知識宣教四項內容的多元組合機制;在供給方式上以無償志愿服務為主,合理開發低償方式及多元組合機制。
4.完善社區健康志愿服務的精準化管理制度
目前,盡管很多社區將志愿服務納入社區日常管理,但是課題組實地考察發現,部分社區對志愿服務的管理依然較為松散、粗放,既缺乏長遠規劃,也缺乏精準化的管理方式和制度規范的建設。“社區+差異化”供給模式的構建,包含了健康需求評估—健康志愿服務資源統籌—健康志愿服務開展—健康志愿服務評估四個重要環節,是一種全過程、項目化、菜單式的精準志愿服務模式,其順利開展有賴于社區志愿服務由松散型向規范化、由粗放型向精準化管理制度的轉變及相關制度的建設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