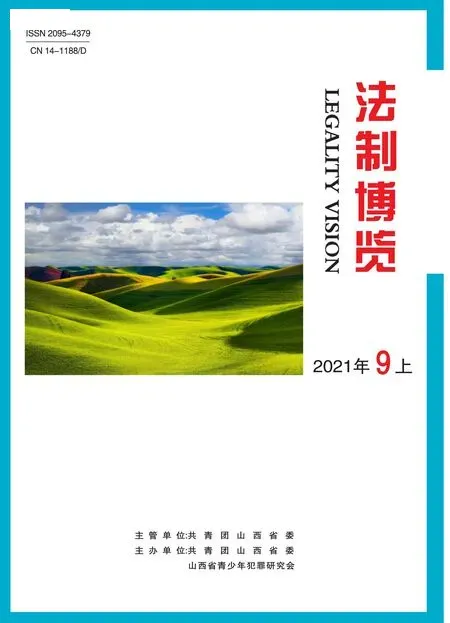我國《民法典》基本原則規定的體系選擇
——以“綠色原則”為例
吳小評
(中共上海市浦東新區委員會黨校,上海 201210)
《日本民法典》在“基本原則”規定中只明文規定了三個基本原則:公序良俗、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而我國《民法典》在“基本規定”中明文規定了八個基本原則:合法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平等、自愿、公平、誠實信用、合法、公序良俗、綠色。為什么同是《民法典》,明文規定的基本原則數量會差異這么大?
一、《民法典》基本原則體系的新發展
查閱世界各國不同時期的《民法典》,發現較早時期的《民法典》往往不在首章明文規定民法基本原則,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追求法典形式上的高度統合,構建一個“總則—分則”的封閉體系,在邏輯上總則必須能絕對統合分則。《民法典》是供司法適用的,所以概念必須精確化,邏輯必須絕對嚴密。而且,民法基本原則的理念和精神都已體現在一些具體規則之中,所以根本無需在首章中明文規定。二是近現代以來較早制定《民法典》的國家往往是法治比較發達而且具有良好私法傳統的國家,在這些國家,民法基本原則所體現的理念和精神早已深入人心,根本無需在《民法典》中明文規定。這種早期做法的典型代表是1900年的《德國民法典》。
但是,當代《民法典》的主流做法是明文規定民法的基本原則,這種新的體系最早始于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在當代以后被許多國家所采用并發展。2008年《歐洲示范民法典草案》“臨時綱要版”指出:“當代民法應確立多元化的原則體系,可以包括的基本原則不止15項,如正義、自由、保障人權、經濟福祉、團結和社會責任、保護消費者以及其他需要保護的人、理性、效率等等。”[1]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變化,原因在于社會現實日趨復雜、多樣,在傳統私法理念之外出現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價值,這就需要《民法典》以更加靈活、更有彈性的體系將這些多樣化的價值聚合并明文宣示。這種新的體系觀不再像1900年《德國民法典》那樣一味地追求概念的精確和邏輯的嚴密,而是更注重時代需求,更注重價值思考、價值平衡。
二、我國《民法典》基本原則的規定發展了當代新民法體系
日本在二戰后修改的《日本民法典》,就采用了這種當代新民法體系,增加了民法基本原則的規定。我國在1986年《民法通則》中全面系統地規定了民法基本原則,2020年頒布的《民法典》延續了這種做法。無論是《民法通則》還是《民法典》,我國明文規定的民法基本原則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數量更多,內容更為系統全面,可以說發展了上述當代新民法體系。之所以如此,是由我國特定的歷史和國情決定的。中國古代法律“重刑輕民”,刑事法律發達,民事法律落后。新中國成立以后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在法律上又“重公輕私”。民法屬于私法,公、私法的劃分從原則上說,凡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都屬于私法關系,而具有等級和隸屬性質的關系屬于公法關系,私法關系的參與主體都是平等主體,國家介入其中也是以特殊的民事主體身份行事,而公法關系中必然有一方是公權主體,其參與社會關系也仍然要行使公權力。改革開放之后,民法才開始發展。改革開放之前,民法只有《婚姻法》一部法律。改革開放之后,我們開始實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民法才有了生存的土壤。改革開放43年,民法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由弱變強的過程。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屬于民事立法方面的后發國家,缺乏悠久的私法傳統,所以在《民法典》中系統而全面地規定民法基本原則,無論是傳統的私法原則,還是適應現實需求的一些新原則,都是非常必要的。
三、“綠色原則”入典:當代新民法體系的充分體現
(一)“綠色原則”入典的背景
當今社會,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資源浪費的現象很嚴重。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大量的生活用品被閑置或丟棄,奢侈品消費占比越來越大,人們的攀比意識增強,節約意識較差。同時,在生產領域,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提高國民生產總值,過度開發現象也愈演愈烈,生態環境沒有得到充分保護。資源問題、環境問題,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全球問題,如不及時重視和解決,后果將不堪設想,人類社會已從工業文明階段進入到生態文明階段。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括對綠水青山、美好生態的向往,而資源與環境問題也是目前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因。在此大背景下,節約資源、保護生態問題不僅是公法問題,《民法典》也必須從私法角度作出回應。因此,作為21世紀《民法典》的代表,我國《民法典》充分體現了“綠色原則”,在基本原則、物權、合同、侵權責任中都貫穿了生態保護的理念和精神,其中最根本的當然是在總則編中,將“綠色原則”作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加以規定,這一規定在世界范圍內具有開創性和超越性。
(二)“綠色原則”入典的正當性
《民法典》第九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在《民法典》制定過程中,就“綠色原則”是否應入典的問題,大家也曾經有過一些爭論。反對者的主要理由包括以下幾點:一是認為環境保護問題是公法問題,因此不應作為民法的基本原則規定,該原則入典是混淆了公法和私法的界限和功能;二是此原則的內涵并不確定,無法在具體規則中體現出來;三是此原則無法在司法實踐中適用,因此更具宣示性,而不具有實際意義。[2]其實,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從《民法總則》(《民法總則》中已有“綠色原則”的規定)施行以來司法實踐的情況看,反對者的這幾個理由都不能成立。
首先,現代民法和近代民法的重要區別就在于,現代民法更有“社會本位”思想,所有權神圣、合同自由等私法自治原則要受到一些限制。公法和私法的劃分有意義,但二者并不是毫無聯系的,而是有連接點的。例如,民法中有一些涉及公權力行使的規范,如《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二條、第二百一十三條和第二百二十三條對政府機關的行政登記及收費作出了規定,第二百一十八條對政府登記機關的信息公開提出了要求。這些規定在民法中的存在并沒有改變民法是私法的性質,反而說明有時公權的行使和私權的行使是有連接點的。同樣,“綠色原則”入典,為《民法典》與環保方面的公法提供了很好的連接點,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環境保護法律體系的協調統一。
其次,“綠色原則”的內涵具有一定的確定性,而且其確定性并不比私法自治、公序良俗等傳統民法基本原則的確定性差。從《民法典》分則的內容看,“綠色原則”已經充分體現在各部分的具體規則中。例如,在物權編中,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業主應當遵守法律、法規以及管理規約,相關行為應當符合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要求。”合同編中,第五百零九條第三款規定:“當事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應當避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第六百一十九條規定:“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的包裝方式交付標的物。對包裝方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據本法第五百一十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應當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裝;沒有通用方式的,應當采取足以保護標的物且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包裝方式。”在侵權責任編,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條規定:“侵權人違反法律規定故意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造成嚴重后果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
最后,從2017年10月1日《民法總則》實施之后的司法實踐看,以“綠色原則”為依據作出的司法裁判并不少見,而且呈逐年上升趨勢,這一點通過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中搜索即可知。因此,“綠色原則”具有較強的司法適用性,并不僅僅具有宣示性。
四、結語
我國《民法典》中基本原則的規定,采用并發展了當代新民法體系觀,“綠色原則”入典就是這一體系選擇的充分體現,“綠色原則”從性質、確定性、司法適用性等方面看均具有入典的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