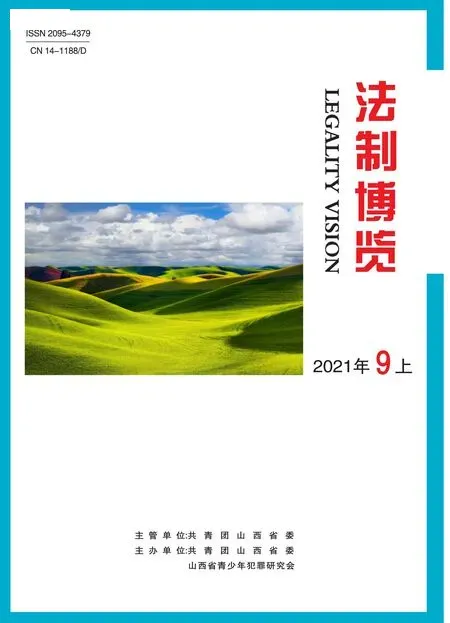《民法典》與《民事訴訟法》的調和
——以訴的制度、審理程序和證據制度為例
張國峰 張旭娜
(河南英泰律師事務所,河南 鄭州 450000)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將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與民法總則等法律整合,成為我國法律體系的基礎法律。法律生命力在于施行,《民法典》需在實際情境下進行應用,才能發揮其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基礎性與綜合性作用。因此,將《民法典》適用于民事訴訟中需遵循合理的訴訟程序,做好二者之間的協調工作,將《民法典》的具體規定作為訴訟案件的衡量標準。
一、協調的基本思路
《民法典》的實施應與民事訴訟工作保證協調一致,具體體現為在實際民事訴訟中展現出方向的一致性。但在某些情況下,《民事訴訟法》與《民法典》會出現要求內容不一致的情況,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后續判斷。《民法典》已施行數月,其與《民事訴訟法》的協調問題需要及時解決。同時,兩部法律應在協調之外再做對接,在《民事訴訟法》獨立存在的基礎之上衡量,判斷《民法典》的程序路徑與方法,設立新程序路徑以落實《民法典》所規定的權利與義務。民事訴訟程序的設定應適用《民法典》的規定,因訴訟對象的不同展現出民事訴訟程序設置上的區別。
二、訴的制度方面的協調
訴的維度包含主體與客體兩種,這兩種都與《民法典》關聯緊密[1]。《民法典》中明確規定了實體的權利與義務,同時決定了主體與客體兩方面的內容。由此可見,《民法典》與《民事訴訟法》協調與對接的首要層面便是訴的主體與客體方面的協調。
(一)訴的主體
《民法典》中,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總有其享有和承擔的對象,二者在實體法中的地位影響二者在程序法中的地位,即在《民事訴訟法》中的地位。實體法中所規定的權利與義務均能作為程序法所指導的民事訴訟事件的糾紛內容[2]。《民法典》作為最新頒布的實體法,雖整合了數部法律的內容,但并非簡單的加和,而是在原有法律體系中有所擴展與進步。這些擴展與進步的內容常為權利與義務層面的擴展與進步,需在《民事訴訟法》中有所體現。例如,《民法典》對權利與義務的擴展意味著訴的主體擴展,能夠幫助民事訴訟中更加清晰地確定當事人的地位(例如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非法人組織)。而且《民法典》中擴展的權利與義務還會影響到民事訴訟中第三人的范圍。例如,《民法典》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相關規定作出了擴展,明確指出該權利可流轉的特性。這種擴展使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能夠以第三人的方式參與民事訴訟,因第三人的參加也必將對土地糾紛案件的解決產生影響。
(二)訴的客體
在訴的客體層面上,《民法典》對《民事訴訟法》的影響更為深遠,需要協調與對接的內容更多。具體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協調與對接可訴范圍。從理論研究的角度出發,任何在法律中有所規定的權利與義務都應在程序法中找到對應的訴訟程序對其進行解決。例如,《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條規定,成年子女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確認親子關系的訴訟請求,即意味著訴訟程序應為該項權利的確認提供路徑。但在實踐過程中,可訴訟的權利與義務需在實體法中進行明確規定,如果沒有,就需要法院法官引入邏輯推理與法理推論對其進行判斷,但如此又存在較大的責任風險。由此可見,只有《民事訴訟法》及其指引的民事訴訟程序與《民法典》中所規定的權利與義務互相對應后,才能有效為審判者提供依據,切實保障民事主體的實體權利。
另一方面,訴訟標的、訴的客觀合并、訴的變更、訴的選擇、禁止重復訴訟等制度運作的影響及協調、對接。與《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訴訟標的產生相關性的是《民法典》中規定的實體請求權。訴訟標的會決定訴的和并、變更與選擇,也會影響重復訴訟的選擇依據與訴訟效力的判斷范圍[3]。例如,在借貸糾紛中,常出現本金請求權與利息請求權訴訟標的存在差異的問題,表明訴訟標的受《民法典》與《民事訴訟法》之間區別的影響而展現出差異。再例如,《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條明確指出,當事人的違約行為若使對方的人格權產生了嚴重的精神損害,受損害方選擇請求其承擔違約責任的,不影響受損害方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種規定中的“不影響”指的就是兩類請求權之間差異,民事主體可以此主張兩種請求權。
三、審理程序方面的協調
《民法典》與《民事訴訟法》協調問題的重點之一便是《民法典》中的禁令制度與《民事訴訟法》中的對應制度之間的關聯。如果二者并未建立關聯、《民法典》中的禁令制度并未在《民事訴訟法》中有所體現,就應對后者進行調整,以進行協調與對接。例如,《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條明確指出,民事主體有證據表明對方正在侵害主體的人格權且會因此而產生傷害,有權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法院責令對方停止有關行為。《民法典》的這一條例并未明確設定具體實施過程中的程序結構,若要根據其進行設定,便要考慮人格權禁令相應的程序是否應具備獨立性,它與《民事訴訟法》中的“行為保全”概念是否存在區別,如果不同,后者又應如何協調與對接。從《民法典》的具體規定可知,法條并未表達出人格權禁令是否具備獨立性,不具備保全的意向,所以并不能滿足該規定的初衷、概念以保全結果為目的的條件。同類型的禁令還包括人身安全保護令、知識產權保護令等,這些禁令均與程序意義上的行為保全存在含義差別,因此可將禁令裁決設置為準訴訟程序,可將程序中是否采用公開原則、直接原則等訴訟審理原則的決定權交給法官,由法官根據案件的具體需求決定。這樣既能保證程序的效率性與公正性,也能夠保障程序設定的合理性。
四、證據制度方面的協調
適用《民法典》的過程必然包含民事訴訟過程中的事實認定階段,從而涉及證據制度的認定。在證據制度層面的協調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證據方法的協調
我國證據法中明確規定了合法證據的幾大類型,所以證據方法即為具體證據的歸類問題。例如,《民法典》包含子女撫養話語權的規定,當子女年齡已滿8周歲時,應詢問子女個人意見作為撫養權劃分的主要判定依據。子女只在訴訟過程中陳述自己的被撫養意見,但是子女既不是證人,也不是當事人,僅為訴訟事件的參與人,其陳述內容不屬于證據,當真實性存疑時可通過證據驗證陳述內容。再例如,《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條中明確指出,禁止在建筑物內向外拋擲物品,若因此造成損害,則應依法追究責任并予以賠償。因此在實際訴訟程序中,公安部門對異物拋擲者的調查結果屬于類型特殊的書證,用以在事件發生后認定事實,類似于報道性的公文書。從這種意義上看,公安機關的公文書可以通過訴訟程序進行質疑。
(二)證明制度的協調
證明制度是我國法律體系中認定事實、檢驗證據真實性的主要方法。《民法典》與證據制度之間存在較為緊密地聯系,能夠證明《民法典》中規定的請求權附屬的要件事實。《民法典》的出臺優化了我國法律證明制度,能夠有效提升其體系化建設質量。《民事訴訟法》需根據《民法典》對證明制度的影響適當協調與對接。《民法典》在證明責任相關法條中新增了許多內容,拓展了責任分配的操作空間,《民事訴訟法》與具體的訴訟程序需根據《民法典》的變化進行適當調整,以保證新規中的規范能夠在實踐中獲得有效應用。例如,法院應在舉證當事人舉證時進行說明,清楚講解其舉證后果。書證提出的申請、鑒定費用的繳納、文書真實性的證明均應該根據《民法典》對訴訟程序的影響進行相應調整。
綜上所述,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協調問題較為復雜,應根據實體法的具體變化適當調整程序法的內容或訴訟程序。具體的協調方法需根據《民法典》的內容、民事糾紛的具體情況進行調整,能進行局部修改的時候盡量控制修改比例。如果不能采取修改法條的方式予以解決,也可以在學理的角度進行微調,或者在審判思路方面進行調整。本文以《民法典》和《民事訴訟法》之間的協調工作為主要研究角度,探究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間的互動、協調關系,以此為今后實踐過程中的調整,為我國《民法典》的解釋與應用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