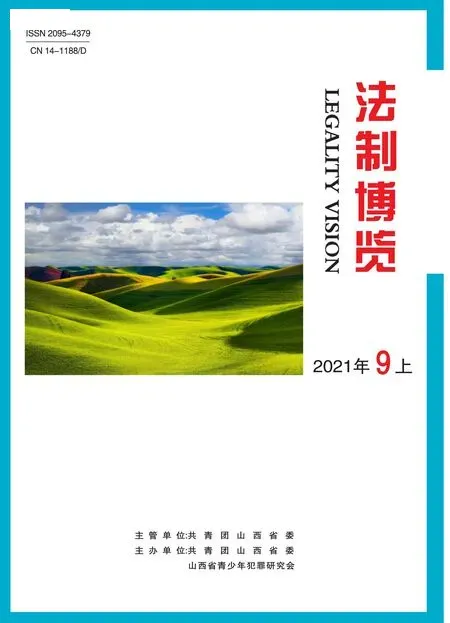從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看優化營商環境難題
譚金星
(恩施市人民檢察院,湖北 恩施 445000)
2016年以來,恩施市人民檢察院共受理審查起訴非法占用農用地罪案件39件,通過對涉案主體身份及發案原因分析,發現該類案件中,行政單位、企業為建設市政工程、修建道路等而觸犯刑法的案件呈上升之勢。此類案件中暴露出的林地審批政策限制多、刑法出罪設計空白、企業發展環境難題等,應當引起重視。
一、問題的提出
恩施市某局涉嫌非法占用農用地一案中,因省道某路段山高彎急,路面、安防損壞嚴重,經恩施州發改委批復立項,國家交通運輸部撥付專項資金對該路段進行擴建改造,由恩施市某局組織實施。自2018年3月始,該局多次向林業主管部門咨詢業務指導和報批占用林地手續。因該路段經過某省級自然保護小區,須經專家評審、申報、公示等程序通過生物多樣性影響評估后方可報批占用林地手續。因考慮到該項目國家交通運輸部撥付的專項資金在兩年內未被使用會被收回,該局決定在繼續辦理占用林地手續的同時開工建設,并于2019年3月開工建設該工程。2019年6月,自然保護小區生物多樣性影響評估報告獲批后,該局再次上報占用林地手續,但根據《國家林業局關于依法加強征占用林地審核審批管理的通知》規定,“對已經發生的違法占用林地建設項目,應當在依法進行行政處罰和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后,依法補辦征占用林地審批審核手續。”恩施市人民檢察院對該局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后,該局繼續申辦林地手續,但因項目涉及林地中部分林地變更為I級保護用地,根據《國家林業局第35號令》規定“各類建設項目不得使用I級保護用地。”因此截至目前,該項目仍未辦得林地審批手續。經勘測,2019年3月—2020年10月,該項目共占用林地共計254.65畝。
該案中恩施市某局為建設全州重點項目工程,經單位集體決策采用未批先建方式占用農用地,觸犯刑律。案件中出現的“未批先建”怪象其實普遍存在。在行政單位辦理林地審批尚且如此艱難的情況下,市場主體的艱難處境可想而知。恩施市人民檢察院辦理的恩施某公司非法占用農用地案中,該公司在修建養殖示范基地過程中,超出《使用林地審核同意書》審批紅線,非法占用林地17.1555畝,導致被占用林地上原有植被嚴重損壞。該公司作為恩施州人民政府招商引資引進的生態農業企業,推行“公司+家庭農場”合作養殖模式,改變了當地傳統的產能低下、污染嚴重的養殖模式,在增加當地集體經濟收入、提供就業崗位、帶動農戶脫貧增收方面有較強的帶動作用。案后回訪時企業主反映,占用林地難獲審批仍是企業后續擴大經營規模的難題。
僅在該院辦理的39件非法占用農用地案件中,行政單位為了推進市政工程建設,在未取得林地審批手續的情況下非法占用農用地的案件就有5起;公司企業在擴大生產經營過程中,未取得林地審批手續或者超審批紅線使用農用地的案件就有12起。這些案件從犯罪構成上看入罪并無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恩施市某局非法占用農用地案件并非個案。這類案件中涉案主體之所以觸碰刑律,并非為謀取單位或個人利益,恩施市某局作出決定,也是基于對涉案工程涉及“四縣五鄉”的通行安全、精準脫貧、區域經濟發展的考量,在積極履行報批手續的同時,選擇“未批先建”或“邊批邊建”。涉案主體往往是在兩難之中作出選擇,因此他們在此類案件中的過錯程度,值得推敲。雖然檢察機關對這類案件大都以犯罪情節輕微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但筆者認為,絕不應止步于此,除了探索林業審批機制設計中存在的問題,也應探究刑法在出罪機制設計上的空白。
二、出罪機制的探索及面臨的困難
(一)涉林用地重點項目建設報批的反思
以恩施市為例,在申報材料齊全的情況下,林業部門應當在10個工作日內完成相關手續的辦理,但實際上從準備申報材料到通過林地審批的時間遠超過此。筆者通過調查發現,原因如下。一是林地實行定額管理,一個地區的定額有限,一旦超出,將無法通過審批;二是申報材料涉及多部門,缺一不可,許多建設項目未取得某項手續就無法申報林地審批手續;三是林地分級管理嚴格,尤其是一旦涉及特殊用途林,審批過程將更加復雜。比如《國家林業局第35號令》規定“各類建設項目不得使用I級保護用地”;《湖北省天然林保護條例》將全省天然林、人工林中公益林全部納入保護范圍,并明確禁止在保護范圍內建設發電項目等。筆者就實現林地審批的加速,提出以下意見。一是地方政府需提前謀劃,強化與林業、發改等部門的溝通,對當地重點市政、公益項目占地提前布局,做好重點項目林地使用保障。二是對不同建設項目類型進行區分,成立重點項目建設服務小組,提前從項目立項、項目選址介入。三是實行綠色通道制度,對影響民生的重點項目,開通綠色通道,采取特事特辦,優先安排現場勘查等審批程序,盡量縮短審批時間。四是對上報上級部門審核審批的重點項目,及時跟進服務,實行專人對口負責,與省、市主管部門協調溝通,全程跟蹤了解審批進展情況,解決審批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時補報補正材料,促使項目盡快獲得審核審批。[1]
(二)刑法但書的出罪邏輯
司法實踐中對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存在過度刑罰化和重刑主義的傾向。現有的出罪邏輯,來自我國刑法第十三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按照但書條文的邏輯,只有行為已經符合犯罪構成才能按照但書規定出罪,但書規定是犯罪構成體系以外的刑事政策性出罪機制,那么如何劃清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界限就成了我們思考的問題。
司法實踐中,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應首先對違法程度的可罰性進行評價。最有代表性的如日本的“一厘煙草”事件。1909年11月,日本一位63歲的農民,在自家消費了約2克自己種的煙葉后,檢察官以沒有上交專賣局、違反《煙草專賣法》為由起訴。一審認定農民行為違法,但以罪行輕微為由宣告無罪。1910年6月20日,東京控訴院裁定被告有罪,判處罰金10日元。10月11日,大審院頒下判詞,認為若一個違法行為屬細微且幾乎沒有實際危害性,就不能認定有罪,裁定上訴得直,被告無罪。
上文提到的非法占用農用地案件中,涉案主體占用農用地用于修建市政工程、公益性項目,占用的農用地面積較大,與“一厘煙草”事件在量上有明顯的區別,很難評價成違法行為細微,在適用刑法但書規定出罪時面臨著尷尬,這也是為何在司法實踐中對該類案件作出相對不起訴的原因。其次,社會危害性的評價也是類似案件出罪時的“攔路虎”。犯罪是一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即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這是犯罪最基本、最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征。類似的非法占用農用地案件,即使行為人有再多不得已的理由,在客觀上都切實違反了土地管理法規,并且對被占用的農用地造成了損壞,社會危害性是真切存在的。那么,我們在評價這類案件的社會危害性時,能否將項目建設的必要性、項目建成后帶給社會及公眾的利益、涉案主體開展原地或異地補植復綠修復生態環境等因素考量進來,進行一種形式的“折抵”,再綜合計算案件社會危害性。在現行刑法體系中,不難判斷,這種計算方式,因為過于主觀缺乏統一的標準,在司法實踐中缺乏操作的可行性。
三、小結
應當說,刑事實體法出罪的路徑并不平坦。要實現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的實質出罪,就要本著保障人權的價值追求,把不具有實質違法行為、不具有刑法可罰性以及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2]比如涉案主體已經盡到應盡義務,卻因林地審批政策限制多,形成客觀審批障礙后無法及時辦理林地審批手續的案件,在辦理時將是否值得動用刑法進行處罰納入考量,而將一批形式上有罪,而通過實質解釋后不具有可罰性的案件,做無罪處理。唯有此,才能從源頭上預防此類案件的發生,為企業經營發展創造一個寬容的法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