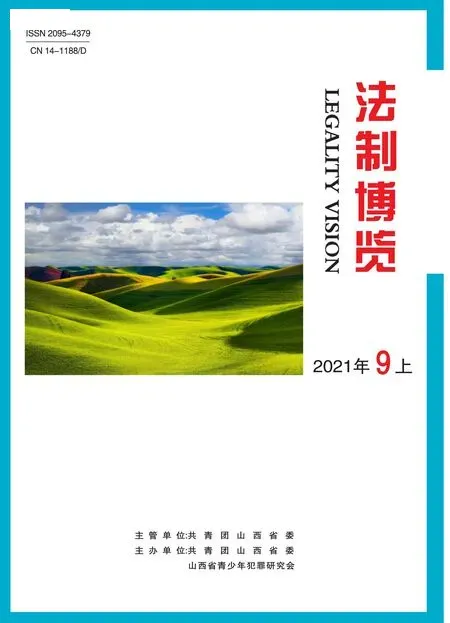關于騙取貸款案件審理情況的調研報告
邢景文 梁國武 曾曉鈺
(鎮平縣人民檢察院,河南 南陽 474250)
騙取貸款罪名的設定對于降低金融風險,保護社會信用尤其是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與相對人之間的信用關系起到了應有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相應的司法解釋,司法實踐中對于行為人騙取行為的認定,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錯誤認識的認定,以及重大損失的認定,成了案件辦理過程中最具爭議的問題,厘清上述問題,對于司法實踐正確認定騙取貸款罪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1]近年來,鎮平縣檢察院第二檢察部門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嚴懲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分子,為保障金融安全,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騙取貸款犯罪案件審理基本情況
2019年至2020年3月,鎮平縣檢察院第二檢察部共受理騙取貸款案件5件6人。
(一)騙取貸款犯罪案件特征分析
一是發案形式具有累積性。基于犯罪行為的隱蔽性,犯罪行為從實施到案發大多經歷較長時間,審結的騙取銀行貸款犯罪中,多數貸款均沒有收回,當犯罪行為無法掩蓋而暴露的時候,經濟損失也往往無法挽回。被告人采取指使他人分散貸款的方式,冒名或者頂名使用貸款,部分信貸人員為謀取私利,甚至與不法分子相互串通,內外勾結,編造虛假信息資料,騙取貸款。
二是法定代表人涉及犯罪多。所涉案件被告人大多涉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因主要是當前小微企業的公司治理制度不完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個人財產與公司財產混同,被告人以個人或公司名義騙取貸款后用于公司經營,后因經營不善致貸款無法歸還而案發。
三是犯罪方法均系虛假簽訂合同騙取貸款。主要表現為虛假簽訂房屋買賣合同或產品購銷合同,偽造公司財務報表或虛報公司財務狀況,以及提供虛假房屋產權證明或虛假收入證明等。
(二)騙取貸款犯罪案件原因分析
一是貸款調查不到位,資信評定不夠深入細致。由于縣城人際交往圈狹小,人情關系多,部分銀行工作人員在對貸款進行資信審查和信用評級時,受到人情關系干擾,存在把關不嚴、走形式、任意發放貸款的現象,僅憑借款人提供的身份證明、印章等證件就辦理貸款手續,對保證人代為履行能力缺乏足夠的了解,從表面上看似乎手續嚴密、完善,但實際上極易出現冒用他人身份證件,頂替他人貸款的現象。
二是貸后監督檢查機制不健全,貸款管理滯后。銀行針對的貸款人員對象廣、分布散、行業雜,而信貸工作人員又不足,客觀上削弱了信貸工作人員對貸款的檢查與到期清收能力;行業監管部門的監管制約作用失效,稽核檢查不落實,對貸款后的檢查不到位,致使貸款逾期也無人問津;個別部門或領導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理解不深刻,片面追求發展經濟,“重服務、不管理、輕打擊”的觀念仍然存在,為不法分子實施犯罪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
三是監管體系有待進一步健全。金融機構風險意識不強。沒有正確處理加快業務發展與防范風險的關系,片面強調信貸業務拓展,對貸款業務缺乏有效的監督和檢查,部分信貸人員迫于信貸任務考核壓力,往往對貸款申請材料亮“一路綠燈”。金融穩定形勢復雜嚴峻。統一監管體系尚未形成。金融風險防范多頭管理、監管渠道尚未暢通,部分風險監管責任不明確。
(三)騙取貸款犯罪案件構成分析
“以欺騙方式獲得金融機構貸款、承兌、信用證等,給金融機構、各大銀行帶來嚴重損失或其他嚴重狀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和相應罰金,給金融機構和各大銀行帶來重大損失或特殊嚴重情節的處3-7年有期徒刑或拘役。”[2]這一條款便是對沒有非法占有目的騙取貸款、承兌等行為的相關規定。對于騙取貸款罪的定義分析,筆者認為指的是個體或單位不嚴格遵循銀行和金融機構以及國家所制定的相關規章制度,運用隱瞞事實、虛構情節等方法獲得金融機構貸款,并導致金融機構產生嚴重損失或情節的非法行為。其構成為:
一是侵犯國家相關金融管理制度和金融機構財產權雙重客體。
二是客觀角度為貸款人不按照政府制度和相關規定,采用欺騙的方式獲得貸款,并給放貸單位造成重大損失或情節嚴重的非法行為。
三是騙取貸款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備責任能力的人或單位。
四是騙取貸款罪的主觀角度是故意構成,明知違法而為了獲得貸款而為之。
二、審理貸款犯罪案件的工作建議
(一)加強金融犯罪多元化預防格局。金融機構應當重視管理,做好內控,特別是貸款發放管理,應該逐步回歸理性渠道。一方面要加強風險研判,嚴格依法依規審批發放貸款、信用卡,加強對機構人員的職業操守教育及風險管控意識,促進金融從業人員規范履職、金融機構合法合規經營;另一方面,要改善金融服務質量,創新金融服務產品,要從形式判斷為主轉為實質研判為主,在發放流動資金貸款及承兌匯票時應從包括行業前景、企業實力、風險大小等實質因素作為判斷依據,合理推薦貸款產品進行金融創新。[3]其他部門應積極參與到金融風險防范社會宣傳體系,采用接地氣的方式,運用現代信息科技便利群眾信息獲得的手段,普及金融、法律知識,及時進行犯罪風險提示,增強民眾識別騙局、判斷風險的能力。
(二)推進信用體系建設。縣域各金融機構大力普及征信常識,提高居民和企業的信用意識,并針對信用良好的企業或個人,優先安排信貸投放或提供優惠利率。進一步完善金融業統一征信平臺,將保險等信息納入征信平臺,將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及線上融資平臺等征信記錄全面納入征信系統的覆蓋范圍。探索將民間借貸信息納入征信系統,使金融機構在更大范圍內掌握企業和個人的負債信息。形成“政、銀、企”征信信息共享平臺,降低因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信用風險,保障信貸資金安全。
(三)構建協調監管機制。明確縣域各金融監管機構的權責劃分,強化縣域金融執法力度,嚴厲打擊金融犯罪行為,規范治理民間借貸市場,維護縣域金融穩定。通過設立“黑名單”,打擊惡意逃廢債行為,形成“政、銀、法”聯動體系,對于惡意逃廢債的企業主,運用社會輿論監督失信行為,運用法律武器形成高壓態勢,強勢遏制逃廢債行為的發生。[4]同時,充分發揮金融聯席會議制度的作用,形成監管合力,協調好監督與發展的關系,共同應對金融風險。
(四)優化案件辦理流程。加強深化檢察人員職業分類管理,形成系統的流程標準規范體系。制定流程規范體系,是案管部門進行流程監督和控制的前提。高檢院應當在《檢察執法規范》的基礎上設計符合新刑事訴訟法要求的、更加細化的辦案流程標準規范。在部門間的流程銜接上,需要設計具有可操作性的案件分流機制,實現點到點的銜接,這樣易于流程細化管理和監控。這就要求建立科學的辦案人員信息管理,使辦案人員的辦案特點、現有辦案數量和進度都能得到信息化的展示,并定期更新。
三、結語
隨著我國各行各業的快速發展進步,經濟取得了較大的增長,與此同時金融犯罪的情況則時常出現,針對騙取貸款罪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這一違法行為發生的概率,針對騙取貸款罪的立法意義、犯罪構成和司法實踐中應當注意的問題進行分析,有利于我國法律的進一步完善。我們在繼承優良傳統和總結以往經驗的同時,努力探索審理工作的新方式、新方法,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把案件審理工作不斷提高到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