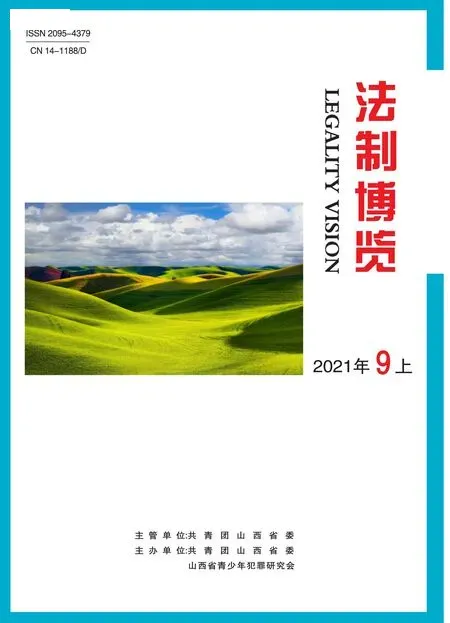當前高新科技領域知識產(chǎn)權保護問題及對策建議
聞雁鋒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872)
一、高新科技領域知識產(chǎn)權保護現(xiàn)狀
近年來,我國持續(xù)加強知識產(chǎn)權保護,部署推動深化改革,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guī),政策、行動、規(guī)劃并施以貫徹與執(zhí)行,取得了顯著成效。
一是制度建設日趨完善。頂層設計方面,出臺《關于強化知識產(chǎn)權保護的意見》,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經(jīng)濟、技術、社會治理手段強化知識產(chǎn)權保護。法制建設方面,修訂《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知識產(chǎn)權法律,進一步提高侵權行為處罰力度,提高違法成本,并對侵犯商業(yè)秘密行為、互聯(lián)網(wǎng)領域不正當競爭行為等知識產(chǎn)權侵權行為作出相應規(guī)制。在優(yōu)化營商環(huán)境方面,通過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yè)促進法》等一批法律法規(guī)鼓勵中小企業(yè)研究開發(fā)擁有自主知識產(chǎn)權的技術和產(chǎn)品,提升保護和運用知識產(chǎn)權的能力。同時,在國家知識產(chǎn)權局的指導支持下,推動地方知識產(chǎn)權立法工作,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個省市均出臺了地方性知識產(chǎn)權保護法規(guī)。
二是知識產(chǎn)權授權確權的質量和效率均得到有效提高。據(jù)最新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2019年,商標注冊平均審查周期已經(jīng)縮短至4.5個月,高價值專利周期審查壓縮至17.3個月。目前,我國專利申請、商標注冊數(shù)量逐年上升,并且躋身于國際前沿。截至2020年6月底,我國國內(不含港澳臺)發(fā)明專利有效量達199.6萬件。2020年前10個月,我國發(fā)明專利申請量達123.2萬件,同比增長11.2%,PCT國際專利申請受理量5.5萬件,同比增長23.5%,均實現(xiàn)了疫情影響下的逆勢增長。2018年我國專利密集型產(chǎn)業(yè)增加值達到10.7萬億元,占GDP的比重達到11.6%[1]。當前,我國知識產(chǎn)權工作正在從數(shù)量增長向質量提高轉變,在高鐵、核能、新一代移動通信、航空航天等領域,研發(fā)掌握了一批自主知識產(chǎn)權關鍵技術,有力推動了中國經(jīng)濟的轉型升級,加快了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chuàng)造的轉變。
三是知識產(chǎn)權審判體系進一步健全。今年1月,我國第四個知識產(chǎn)權專門法院在海南自由貿(mào)易港設立,至此形成了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chǎn)權審判庭、知識產(chǎn)權法庭、32家高級人民法院、4家知識產(chǎn)權法院以及部分中級、基層法院共同組成的知識產(chǎn)權審判新格局。據(jù)《中國知識產(chǎn)權保護與營商環(huán)境新進展報告(2019)》顯示,2019年全國法院新收各類知識產(chǎn)權案件48萬余件,審結47萬余件,收結案增幅突破40%。我國已成為審理知識產(chǎn)權案件尤其是專利案件最多的國家,也是審理周期最短的國家之一。
二、高新科技領域知識產(chǎn)權保護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商業(yè)秘密保護存在的痛點
在當今全球化競爭格局和全國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潮流的大背景下,一方面,各國企業(yè)已把人才視為核心競爭力之一,而在人才引進過程中往往隱藏著侵犯商業(yè)秘密的風險。實踐中不少企事業(yè)單位在看重人才技術背景的同時,卻忽略了其自帶的技術、方法和數(shù)據(jù)等信息是否落入了商業(yè)秘密的范疇,從而招致一系列商業(yè)秘密侵權的國內外糾紛。另一方面,隨著國際經(jīng)濟、科技競爭愈演愈烈,在軍工轉民用、科研技術轉化以及對外經(jīng)濟、技術交往等方面融合了國家安全的問題,這也為商業(yè)秘密保護工作增加了難度。因此,若能建立牢固的商業(yè)秘密和國家安全的保護意識,并能有效甄別商業(yè)秘密,不僅能為企業(yè)在國內外商業(yè)秘密糾紛案件抵御訴訟風險,盡早形成企業(yè)內部的管理防御機制和應訴策略,還能為國家經(jīng)濟、民生的安全加上一份保障。
然而,我國商業(yè)秘密保護的現(xiàn)狀是,首先法規(guī)層面,雖然在行政、刑事和民事的各個保護形式都有相應法律法規(guī),但各領域之間缺乏銜接性、系統(tǒng)性的統(tǒng)一。制度層面的弊端也影響到司法的實踐,不僅三審合一的審判體制沒能得到有效落實,公檢法等行政、司法的各個保護機構之間也缺乏統(tǒng)一性,極大影響了案件的處理特別是刑民交叉類案件的辦案效率。因此,肩負有特殊使命的國安部門,為了滿足自身特定職責需求,極有必要介入并建立相對獨立的商業(yè)秘密系統(tǒng)性保護機制。
其次,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對專業(yè)性較強的商業(yè)秘密的鑒定大多依靠鑒定中心出具的意見,然而目前我國商業(yè)秘密相關的鑒定中心普遍處于缺乏統(tǒng)一管理,各自為戰(zhàn)的狀態(tài)。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一是機構類型復雜,除了法院、檢察院和司法行政部門認可的機構,還有一些社會機構,整體缺乏統(tǒng)一的包括人員統(tǒng)一的準入、培訓規(guī)定等制度,從而實踐中出現(xiàn)鑒定專家可能是臨時受聘者等鑒定人員資質各異、良莠不齊的情況;二是缺乏統(tǒng)一的行業(yè)自律組織和制度,缺乏領導和管理;三是缺乏統(tǒng)一的技術標準,導致可能出現(xiàn)同一個案件不同鑒定機構出具多份鑒定結論,結論之間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情況,不僅增加審判的負累,還削弱了鑒定結論的可信力和公信度,嚴重損害司法公正和法律權威。這種混亂多年來一直掣肘商業(yè)秘密的司法鑒定工作,是行業(yè)內有目共睹的痛點,亟待具有標準統(tǒng)一性、結論權威性的鑒定中心的出現(xiàn)。
(二)其他存在的問題
除上述問題外,我國知識產(chǎn)權的保護還存在一些其他方面的挑戰(zhàn)。例如人民法院知識產(chǎn)權的審判力量不足,新興技術帶來的新型知識產(chǎn)權客體保護、證據(jù)的認定困難等問題,以及我國知識產(chǎn)權法官、執(zhí)法隊伍整體業(yè)務素質需要提高等問題。
三、高新技術領域知識產(chǎn)權保護相關的對策建議
(一)完善知識產(chǎn)權制度立法
在中美貿(mào)易摩擦的背景下,加強知識產(chǎn)權保護的任務需要制度先行。一是吸收轉化與美國階段性協(xié)議中的知識產(chǎn)權條款。協(xié)議的知識產(chǎn)權條款整體上符合我國深化知識產(chǎn)權制度改革、加強知識產(chǎn)權保護的戰(zhàn)略方向,除了與我國現(xiàn)有法律規(guī)定基本一致的條款外,還有部分較之我國國內法更具體、保護要求更高的條款。對此,我們需要站在現(xiàn)實國情的基礎上合理轉化、修改、補充國內知識產(chǎn)權法律及相關配套制度。[2]二是構建針對商業(yè)秘密的系統(tǒng)性保護機制,推進包括三審合一制度在內的商業(yè)秘密保護在民事、刑事和行政領域的統(tǒng)一協(xié)調和銜接,包括制定和頒布商業(yè)秘密訴訟特別程序規(guī)范,改進相關訴訟證據(jù)規(guī)則體系,切實解決其中的刑民先后、管轄法院配置等問題。
(二)健全商業(yè)秘密保護體系
準確地對商業(yè)秘密進行鑒定是保護商業(yè)秘密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因此商業(yè)秘密鑒定中心的權威性、專業(yè)性至關重要。針對眼下各類鑒定中心參差不齊的情況,建議借鑒知識產(chǎn)權保護中心的設立經(jīng)驗,由地方司法部門牽頭,在現(xiàn)有鑒定中心網(wǎng)絡基礎上,整體布局調配,在省市級內建立統(tǒng)一制度管理的司法鑒定中心體系,由司法行政部門統(tǒng)一登記管理。首先,從人員上,明確技術門檻要求和準入制度,確保鑒定人員的專業(yè)性;其次,統(tǒng)一系統(tǒng)內各鑒定中心內部管理秩序,包括鑒定流程、規(guī)則等;其次,還應當統(tǒng)一技術鑒定本身的標準,做到同一案件同一結果,促進審判公平。
針對知識產(chǎn)權審判系統(tǒng)人員不足的情況,法院系統(tǒng)仍應加大知識產(chǎn)權人才的培養(yǎng)和引入,繼續(xù)探索法院布局,協(xié)調集中管轄和最高人民法院授權管轄,以及時應對未來可見還會逐年增加的知識產(chǎn)權訴訟案件。
(三)國安部門發(fā)揮國家大安全管轄角色
繼以知識產(chǎn)權保護為主題的集體學習之后,習近平總書記緊接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堅持系統(tǒng)思維構建大安全格局,為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提供堅強保障。”由此可見,知識產(chǎn)權保護與國家安全之間是密不可分的關系。
綜上所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國安、公安和檢法等各個機關應當各自充分發(fā)揮其司法執(zhí)法特色,并靈活聯(lián)動,重視和加強對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的商業(yè)秘密等知識產(chǎn)權的保護工作。眼下,應盡快探索建立一套適應國家經(jīng)濟、科技發(fā)展和維護國家戰(zhàn)略安全的知識產(chǎn)權系統(tǒng)性保護機制,引導社會企業(yè)發(fā)展,為企業(yè)排憂解難,并付諸實施,使其有效深入到市場各個企業(yè)細胞中去,為我國高新技術的培育營造安全、穩(wěn)定的環(huán)境,為國家經(jīng)濟的持續(xù)、穩(wěn)定的發(fā)展提供有力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