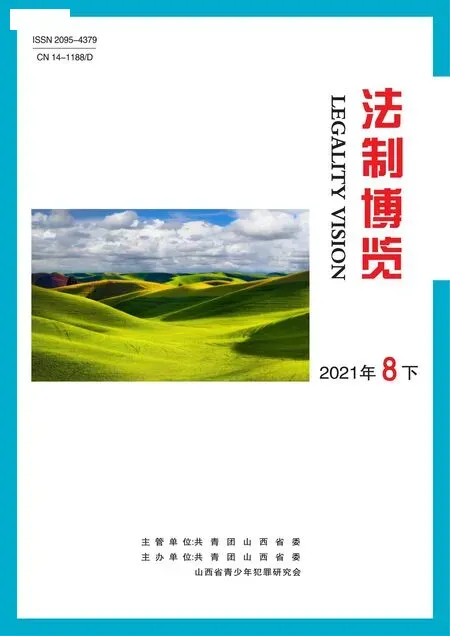洞穴奇案維持有罪判決的原因
王濤至 王 艷
(1.湖南人文科技學院,湖南 婁底 417000;2.天津中醫藥大學,天津 301617)
一、案情介紹
探險協會會員們一同去參與登山活動,可當他們進入石灰巖洞時不幸發生山崩,巨大的巖石掉落堵住了唯一出口。救援隊伍營救任務也異常艱難,在救援的過程中,山崩奪走了10名救援人員生命。5人被困山洞且僅帶了少量食物,洞穴里的人通過無線電與外界聯系得知在救援人員來之前在洞穴里有被餓死的可能性。面對死亡的威脅威特莫爾提議從5名探險隊員中抽選1人吃掉來維持其余人生命。其他4名探險者起初不愿意采納這種殘忍的做法,但最終一致同意了抽簽殺人的提議。而就在抽簽選人開始前提議人威特莫爾認為實施如此恐怖的計策應該再等待一個星期,但剩下4名探險者仍都堅持繼續履行,同時要求威特莫爾對拋擲色子的公平性表態,威特莫爾沉默并沒有表態。不幸的是恰巧選中了威特莫爾作為犧牲者。4名探險隊員殺死威特莫爾并吃掉他后得以存活。被救援隊伍營救后,等待他們的是法律的審判。[1]
二、不構成緊急避險的原因
(一)人的生命權平等
緊急避險作為一種責任阻卻事由,能夠把對無辜者的傷害行為加以正當化。是否構成緊急避險要看是否構成緊急避險的成立要件,基于本案分析,得出不構成緊急避險的結論。因為緊急避險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失不應大于所避免的損失。保護其余4名被告的生命權與侵犯受害者的生命權并非大于的關系。生命權是平等的,1個人的生命與4個人的生命同等珍貴。雖然每個人的人生都具有不同的意義,但每個人的生命權都是相同的,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人的生命權利無高下之分。并不能用數量來衡量,也無法用數字來計算。人的生命權利高于一切,法律所保護的生命權與法律所保護的其他權利不同,生命權是特殊權利,一經放棄便永久消滅,無法恢復。[2]殘暴地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不能用緊急避險的煙霧來掩蓋。
(二)洞穴中平等的自然人不具備犧牲生命的義務
在移開洞口的過程中,有10名救援人員犧牲。塔利法官認為用10名探險隊員的生命去挽回5名探險隊員生命是一場劃算的交易,所以用威特莫爾的生命去換其余4名探險隊員的生命也是合適的。筆者認為這一觀點的錯誤性在于只分析了數字比例,而忽視了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原理。救援人員與被困人員有相應的權利與義務關系,自然人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受到侵害或者處于其他危難情形的,負有法定救助義務的組織或者個人應當及時施救。特定的職務、業務要求的義務以及對危險源負有監管、控告而產生的作為義務。救援人員在救援任務過程中需要承擔風險。其實質在于行為人具有保障他人安全的義務,他人的安全依賴行為人。而洞穴中的被害人并不需要承擔救援隊伍的義務。
(三)未達到采取緊急避險的程度
在抽簽決定剝奪威特莫爾生命前,每個人都能認識到剝奪他人生命是違法行為。4名被告沒有達到吃人才能存活的地步。這就說明沒有到達采取不得已手段的臨界點。從本案來看殺人似乎并不是最好的選擇,除此之外有其他許多方法可以代替殺人,威特莫爾撤回協議是因為他認為可以再等一個星期,在這一個星期內可以等虛弱的人自然死亡或者可以吃掉自己身體不重要的部位,此觀點是合理的。即使有學者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但也說明他們并沒有到十萬火急應當采取緊急措施來避險的程度。
(四)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相矛盾
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當這4名探險隊員對受害者動手時,受害者采取合理措施反抗可否構成正當防衛?筆者認為符合正當防衛的構成要件。威特莫爾可以進行正當防衛。那么如果4名探險者也構成緊急避險,豈不是法律允許這5個人相互廝殺?所以4名被告構成緊急避險結論是荒謬的。斯普林含姆法官將我們帶入這4名被告的視角中,在這4個人的眼中殺掉受害者是合理的選擇。他們并非想要殺人,而只是基于一種自衛的原因,因為替代殺人的選擇就是死亡。認為這樣做符合緊急避險。吃掉自己的手指或腳趾無異于是煎熬,要想存活需要吃掉實際意義的手臂和大腿,在不打麻藥的情況下吃掉自己的這些部位無異于是一種折磨。基于上述的一個論點,在當時的情況下,最好的結果就是以犧牲一部分人為代價,讓更多的人存活。因為面對災難會存在兩種情況,要么死一個人,要么一起死。而筆者認為這樣的結論說服力不足,能夠分擔災難的方法是有人愿意自我犧牲。這一觀點只是從有利于被告的角度出發提出的一種抗辯。如果沒有人愿意自我犧牲,那么全部死亡似乎是更好的選擇,受害人威特莫爾本人也有強烈的生存渴望。假想我們是受害者威特莫爾,從他的角度來看,你并不認同這樣的抗辯理由,忍受一周或更長的痛苦折磨不如選擇死亡好,那么這4名被告為何不去選擇死亡,而是選擇殺我?這讓我感到厭惡,不能克服內心的恐懼把自己當作犧牲品。所以我們應尊重威特莫爾,然而從不同當事人的視角來思考,得出的觀點又會不同。研究法律要以中立的第三人的視角來思考問題。不能陷入當事人思維,是否能成立緊急避險也要做出客觀且公正的評價。受害人威特莫爾沒有自我犧牲的同意,4名被告只能通過其他方面來分析受害者的死亡結果是否正當化。
三、道德角度不構成出罪基礎的原因
(一)道德角度免責不成立
首席法官特魯派尼認為法律條文不允許有任何例外,任何人故意剝奪了他人的生命都必須被判死刑。筆者認為殺人行為顯然違反法律。但一個違反法律的行為不一定構成犯罪。因為一個行為違反了法律不應當理所當然地認定為是犯罪,要看是否侵犯了法條背后所保護的法益,就算侵害了法益的行為也不能被草率地認定為是犯罪,還要看是否有責任阻卻事由。法益作為入罪的基礎,倫理作為出罪的依據。從道德角度是否值得鼓勵,值得鼓勵那理所當然不構成犯罪。例如女子遭強奸的過程中反殺施暴者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應當認定為正當防衛。被強奸的女子殺人行為雖違反法律,從法益保護的角度來分析:強奸罪保護法益是婦女性自主權,故意殺人罪保護的是他人生命權,生命權比性自主權更加重要。但從道德的角度來分析面對不法侵害應敢于反抗、勇于反抗。這是道德所鼓勵的行為,所以不構成犯罪。[3]在本案中洞穴里的4名被告為了自己的生命而侵犯他人生命的行為顯然并不是道德所鼓勵的,而是道德所譴責的。所以這4名被告在道德角度免責不成立。饑餓不能成為盜竊罪免責事由,為了食物殺人自然也不能成為故意殺人罪的免責事由。[4]
(二)道德與法律層面都應認定被告有罪
福斯法官提出案發時他們在聯邦法律管轄下,一個案子也許可以從道德上脫離法律秩序的約束,如同其地理管轄脫離法律秩序的約束。假設當時山洞中因與世隔絕而別無他法,遠離法律約束只是道德去調節的話,會有道德高尚的人愿意自我犧牲挽救他人生命,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挽救他人的生命,這是值得我們敬佩的英雄,之所以值得我們敬佩是因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能勇于獻出生命的人并不多。而當所有人都不愿獻出生命之時,我們沒有權利讓他人為我們犧牲生命,只靠道德是沒有辦法去調節的,每個人道德水平都不同。然而法律作為最低限度的道德,違反了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就應當認定為犯罪。法律雖然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但在一定程度上會保護威特莫爾的生命。道德與法律不可分割,一個人無權任意處分另外一個人的生命。作出無罪判決違反法律立法精神。殺人要受法律約束,為了個人存活而剝奪他人生命是一種殘忍、野蠻的行為,違背人性,不能被人接受。同時也是對死者生命權的否定。人的實踐活動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認為管轄權異議,那么作出的無罪判決就無從談起。法官作出的判決要符合民眾的樸素道德情感,為了生存而殺害他人如果判決無罪顯然與民眾的樸素道德情感相違背。
四、抽簽殺人協議無效性的原因
(一)抽簽殺人協議違反法律
協議成立的前提是協議內容合法有效,而威特莫爾提出的協議一旦履行,看似扔骰子的概率是公平的,實質上這是以生命權為籌碼的賭博。所以抽簽殺人的協議是無效的,不能通過抽簽的合法行為來掩蓋殺人的非法行為。此協議不允許當事人意思自治且并非法律的制定過程,更不是法律的實施過程。因為所有的自由都應受到限制,人沒有承諾自己生命的自由。生命權是人權的基本權利,公民依法享有生命權不受非法侵害的權利,人的生命權不得拋棄或轉讓。所以威特莫爾提出抽簽殺人的協議自始是無效的。無效的協議撤回就不具備意義,撤回協議并非適用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程序。五人一同登山且被困山洞屬于高度緊密的共同體,在緊密的共同體中,行為人實施的是非常危險的行為,5名探險隊員之所以敢去實施登山這一行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寄希望于彼此相互依靠、保護。否則孤立的個人是不敢去實施這類行為的,緊密共同體成員之間有相互救助義務。區別于成人之間一起約會、游泳、散步等這些松散的共同體。在松散的共同體中各行為人沒有負責保障他人安全的義務,因為這類活動風險小,屬于日常生活行為。5名探險隊員在緊密的共同體中每個人都具備保護對方安全的義務,任由他人侵害他人生命,自己可能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5]被害人威特莫爾創設了法律所不允許的風險,就應當有消除的義務,撤回協議未能積極有效地阻止共同犯罪繼續實施,被害人威特莫爾不成立犯罪中止。換言之,威特莫爾與其他4名被告均成立故意殺人罪,是共犯[6],由于法律責任主體消失所以不承擔責任。
(二)抽簽殺人協議非被害人承諾
此時受害人并非是想要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拯救他人。因為協議并非對死亡結果的肯定,而是對死亡可能性的肯定。如果每個人都同意,那么對于個人而言就有80%的概率存活,有20%的概率死亡。[7]如果威特莫爾提出犧牲自己來拯救他人這是合理的,但此時受害者并非想犧牲自己,而是希望能增加自己存活的概率。其余4名被告把威特莫爾殘忍殺害與分尸,并無視威特莫爾最后一次明確意思表示再等一個星期,違反了被害人的承諾,應當有罪。
五、結論
人類社會在不同的自然環境與人文背景下孕育出了形式各異的法系,不同法系都具有差異性,然而不同法系的共同點是對生命權的尊重與保障。《洞穴奇案》是偉大的虛構案例,也許在現實生活中不會遇到如此棘手的案件,但此案背后的道德與法律關系、自由價值與正義價值的關系值得我們深思。《洞穴奇案》判決也是對法官判案能力的考驗,面對復雜案件,會使人陷入進退兩難的境界。這4名探險者的行為確實已經構成故意殺人的事實,而殺人者死,很簡單的道理法官要區分故意還是過失,是主犯還是從犯,是幫助犯還是教唆犯,區分有無責任阻卻事由。法官這樣推導恰恰說明法不是教條的法,也不是冰冷的文字,更不是機械推導。
關于《洞穴奇案》中的被告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判決。正義的定義在每個人心中也不同。形成不了統一的標準,就如同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人們無論對正義內涵如何理解,法律制度的構建是重要的,制定出法律我們就應遵循。法律是人類社會最后一道防線,是文明世界與獸性世界的最后一道城墻。一旦法律終結,暴力就會開始。所以人們只有對法律堅定地遵守才能使法律形成自己的力量,而不會因個人的道德或政治立場不斷反復搖擺。法官要追求公平正義,發現法律不合理之處,要合理運用自由裁量權,兼顧法律與道德,從而平衡價值沖突。滿足人民對于公平正義的追求。人們遵守法律的規定,及時發現法律規定中可能存在的不合理的部分,立法者傾聽民意修改法律與時俱進做出調整才能促進我國法治化建設快速發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