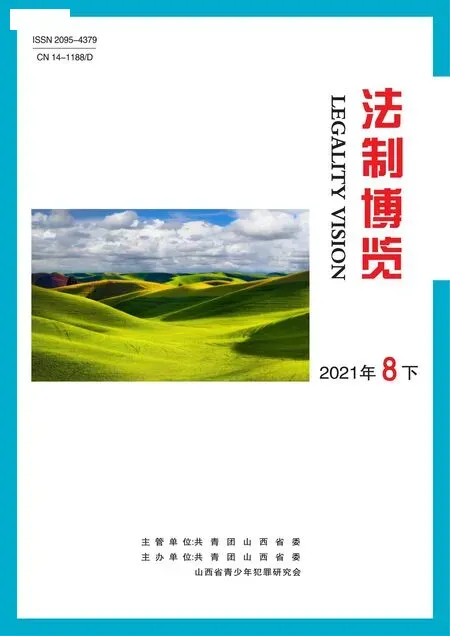基于《民法典》角度的意思自治與法律行為探討
夏立新
(撫順職業技術學院(撫順師專),遼寧 撫順 113122)
法律內容必須與社會發展相適應,只有這樣才能將法律的價值發揮到最大,使其為社會發展貢獻力量。《民法典》在中國經歷了一個比較復雜坎坷的發展歷程,直到2021年1月1日才正式實施,成為法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內容。《民法典》的頒布和施行,確立了法律行為的基本意義,使法律更加制度化、體系化以及嚴密化,解決了當前法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而法律行為作為其中最基本的內容,所宣揚的意思自治理念是一種全新的發展體系,在未來的應用過程中應該呈現一種怎樣的意義和價值,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一、體例維度:法律行為制度的體系價值
(一)“典范性法源”與法律行為
縱觀我國現有的法律,第一個以“法典”命名的是《民法典》,可見其在我國法律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這也并不意味著其他法律缺乏法典的相關功能和作用。比如:在1997年修訂的《刑法》雖然沒有被命名為“刑法典”,但所發揮的功效仍然和《刑法典》一樣。從定義上來講,法典具有其自身的作用和功能,這是它區別于其他法律的典型特征。但除此之外,還可以從法律淵源序列層面進行深入解讀和分析,將這一層次的內容上升到法源問題上。
關于民法的法源序列,《民法典》于總則編之“基本規定”部分設置了兩個重要的條款。第一條款:“其他法律對民事關系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這一內容提出《民法典》的基本地位,即相對于特別民法而言,具有一定的基礎性。第二條款:“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這一條款建立在法源序列基礎上進行對比,主要涉及國家法與習慣法在邏輯上的規范適用以及銜接關系,與國家法調整對象存在一定差異。
(二)總分則體例結構與法律行為
從體例結構角度分析法律行為制度,可以結合“憲法—民法—民法典”三者的關系進行研究分析,還可以從《民法典》總分則體例結構角度進行觀察解釋。伴隨著《民法總則》的先行頒布,為《民法典》總則編提供范例,在此基礎上法律行為制度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也日益顯現。但隨著《民法典》各分編合體的頒行,改變了《民法典》總則編的地位,總則作為各分編的目錄,為使用者提供了內容參考,以此來將各種民事權利連貫起來。在此基礎上《民法典》總則編規定法律行為制度只是對民法通則立法慣性的延續。[1]
除此之外,還可以利用法律行為、民事權利、民法基本原則三部分來理解總分則體例結構中的《民法典》總則編,在不斷解釋的過程中具有很多可用價值。由此而言,法律行為制度的體系價值也可以借助這三個關鍵詞進行分析和研究。法律行為制度主要體現意思自治、人格平等以及誠實信用三個關鍵點,本著自愿、平等、誠實、不違反強制性規定以及不違背道德標準的原則達到相對應的目的。就其定義來講,人格平等是前提,一旦在實際跟進中出現問題,從意思自治角度出發可以借助法律行為的作用,制定相關的規則制度進行強化和維護。而提出的不違反強制性規定,不違背道德標準、社會規則的出現能夠為意思自治提供有效的邊界,規定法律行為在合理的范圍內存在。
二、構成維度:意思表示規范的體系效應
(一)意思表示與法律行為的關系
《民法典》對法律行為進行明確規定:借助意思表示變動民事法律關系的行為,但對意思表示和法律行為之間的關系并沒有明確規定。《民法典》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有如下表述:民事法律行為能夠基于雙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一方的意思表示成立。這一表述的意思在于如果缺乏意思表示,則法律行為很難發揮作用,只有存在意思表示,才有提及法律行為的必要。雖然已經明確提出雙方存在關聯,但是具體是什么關系仍然需要進行深入研究和分析。[2]
由于對意思行為和法律行為的關系不明晰,所以出現很多結論。有的觀點提出等同論,認為二者意思一致,作用一致;有的觀點提出構成論,認為意思表示是構成法律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兩種觀點雖然存在一些差異,但從根本上可以體現出意思表示作為法律行為成立前提的地位。如果借助《民法典》的相關內容,具體闡述其中的關聯性,可能會發現其中的復雜性。從《民法典》第六章對“民事法律行為”進行詳盡論述。首先,在相關法律條文中明確規定了意思表示和法律行為的生效時間,二者時間節點不一致。其次,對法律行為的效力障礙也進行明確規定,強調意思表示生效不同于法律行為。
(二)意思表示解釋規則的特殊地位
通過對《民法典》頒布以前法律現狀進行調查發現,很多法律已經明確規定了相關的法律行為規則,這些為《民法典》法律行為奠定了穩定的制度基礎,促使《民法典》可以依托相關法律實現不斷更新和升級。從意思表示內容進行分析,在《合同法》中有一些規定,具體內容還需從《民法典》中進行獲取,這是《民法典》值得業界人士學習和重點研究的內容之一。具體內容見《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條規則。通過進行有效對比,《民法典》中去除了《合同法》中關于合同解釋的相關內容,只涉及意思表示解釋的相關內容。在這一問題上,存在合理性、專業性和科學性,符合相關規定。在意思表示解釋內容上區分“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解釋”和“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解釋”,把二者所包含的實際意思作為相關的適用前提。除此之外,法典中還涉及對意思表示的目標進行相對應的規范。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如果判斷相關的協議、遺囑意識表示,必須以相關《民法典》中相關的法律條款為依據。既強調意思表示的相關內容,又規定意思表示的先行界面。
三、效果維度:處分行為規范的體系發展
(一)處分行為效力的規范適用問題
在《民法典》未正式頒布以前,物權行為理論一直是相關領域認識爭論的焦點。從1999年的《合同法》到2007年的《物權法》,雖然在不斷發展過程中,根據現有情況和形式進行相對應的完善,但是因其涉及內容較多,仍然作為比較難處理和解決的問題。伴隨著《民法典》的頒布和推行,物權行為理論中的處分行為問題已經成為其中急需解決的關鍵問題。一方面,在處分行為的合理性方面進行深入探討,相關法律法規中指出,如果物權行為具有直接變動既有物權的效果,那相對應的物權行為就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反之亦然。因此,要想確保其存在合理,必須保證其具備充足的存在理由,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突顯物權行為的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在處分行為的規范性方面進行深入分析,《民法典》將買賣合同解釋第三條內容收入其中,但合同法并未進行相關操作,造成買賣合同的效力已經與處分權關聯性不大。[3]
在處分行為效力問題上,也有學者認為《民法典》已經存在明確區別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的立場。
(二)擔保法體系重整與處分行為
要想財產法發揮作用,必須遵循一定的處分行為規則。本文從這一層面提出具體的研究內容:功能主義思路下物權變動公示對抗規則與處分行為的關系。如:在動產抵押問題方面,抵押人和抵押權人根據相關的規定達成抵押協議,簽署抵押合同,一旦在規定日期內合同生效可直接形成動產抵押權,這里面也涉及對抵押人所有權的處分合意內容。不僅如此,雙方一旦存在違反規定的行為,抵押權人有權根據抵押合同要求抵押人進行抵押權的登記,在這一方面抵押合同具有承擔相應后果的作用。由此來說,面對不同的財產問題選擇不同的生效模式和手段,里面包含的負擔和處分行為各不相同。以《民法典》中提出的物權變動模式為基礎,所制定的合同具有一定的復合性,既涉及創設新生債務的分擔性內容,又包含變動權利的處分性內容。
除此之外,雖然復合特征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其處分效果并不涉及對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要想獲得相對應的效力,需要經過相關的公示程序才能夠完成。但在這一問題上,一旦抵押人和抵押權人進行動產抵押權登記,這一內容是否和抵押合同中的處分合意相一致,是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