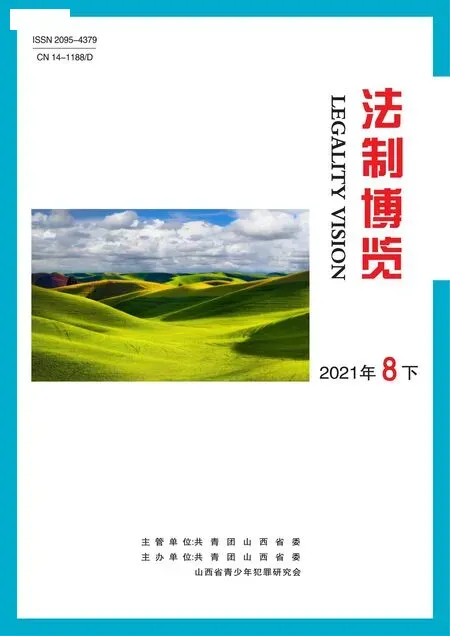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律保護(hù)模式探究
袁慕貞
(廣東彭代強(qiáng)律師事務(wù)所,廣東 東莞 523000)
近年來,我國(guó)的大量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申遺成功,也使國(guó)家的歷史文化底蘊(yùn)進(jìn)一步在世界范圍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正因?yàn)榉俏镔|(zhì)文化遺產(chǎn)有其歷史流傳的因素,所以有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借此模糊權(quán)利主體,甚至于信口雌黃,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特殊價(jià)值和歷史地位抹除,意圖損害我國(guó)的形象。因此,如果僅僅以傳統(tǒng)的形式口頭申訴,顯然無法獲得認(rèn)同。在新時(shí)代,各種現(xiàn)代國(guó)際法的制定層出不窮,也進(jìn)一步將法律制度保護(hù)的重要性擺上更高層面。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中,我國(guó)同樣需要與時(shí)俱進(jìn),不斷地探索產(chǎn)權(quán)法律保護(hù)的新形式,才能讓別有用心之人偃旗息鼓。本文對(duì)此進(jìn)行系統(tǒng)闡述。
一、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概念和特征
(一)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概念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在教科文組織有關(guān)公約中有具體闡釋,意為“不以實(shí)體的表現(xiàn)形式出現(xiàn),但能給世界發(fā)展或民族發(fā)展帶來精神引領(lǐng)和價(jià)值啟迪的影響”。而我國(guó)也同樣對(duì)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有著清晰界定,基本上和世界接軌,對(duì)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因傳遞無形價(jià)值的影響大小而分類,并且進(jìn)行了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稱與歷史文化的羅列,設(shè)置了專門的部門宣傳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在專門的官網(wǎng)上擴(kuò)大非物質(zhì)遺產(chǎn)保護(hù)的概念滲透,足可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具有極其重要的價(jià)值。
(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特征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總共有幾個(gè)特征。其一是豐富而多元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因?yàn)榉俏镔|(zhì)文化遺產(chǎn)并不是實(shí)體呈現(xiàn)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抽象表現(xiàn)內(nèi)容,能夠被人的主觀判斷加工。正因?yàn)槿绱耍俏镔|(zhì)文化遺產(chǎn)在不同地域、不同身份和不同民族的人視野中有著區(qū)別,在不斷地藝術(shù)加工和渲染后形成了不同的形態(tài)[1]。例如蘇繡是我國(guó)重要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但是在江南地區(qū)蘇繡常以色彩含蓄令人流連,而在北方地區(qū)卻將蘇繡表現(xiàn)成色彩瑰麗明亮的雍容感。這是因?yàn)樘K繡被帶到北方官宦家族后經(jīng)過了服裝改革,在繪畫上經(jīng)過一些畫家的主觀想象,形成了新的視覺效果。其二則是鮮活而動(dòng)態(tài)的群體顯現(xiàn)價(jià)值。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能夠長(zhǎng)久留存,正是因?yàn)槠湓谌嗣裆睿袕V泛的生活基礎(chǔ),投射出了一定的情感,不僅僅是古板地表現(xiàn)出來,而且因不同群體的實(shí)踐又發(fā)生改變。也因?yàn)檫@種情感的驅(qū)使,導(dǎo)致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并不是一成不變地保留下來,同時(shí)會(huì)衍生出與之相關(guān)的各種實(shí)體物質(zhì)和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用來紀(jì)念和展示,豐富了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藝術(shù)內(nèi)容。
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的必要性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在價(jià)值觀引領(lǐng)和營(yíng)造人文底蘊(yùn)方面有著重要作用,而當(dāng)今時(shí)代因?yàn)橐越?jīng)濟(jì)物質(zhì)建設(shè)為中心主導(dǎo)的觀念滲透,有大量商業(yè)主體意圖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當(dāng)成牟利的工具,這樣就會(huì)喪失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與生俱來的純潔性。因而必須加強(qiáng)對(duì)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力度。其次,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作為衡量國(guó)家軟實(shí)力的一個(gè)重要因素,雖然能彰顯國(guó)家的發(fā)展價(jià)值,但是隨著科學(xué)化的發(fā)展,世界各國(guó)都將維護(hù)軟實(shí)力的科學(xué)手段作為競(jìng)爭(zhēng)的核心,對(duì)各國(guó)多元融合的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展開分析。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僅僅是我國(guó)軟實(shí)力的科學(xué)維護(hù)過程的縮影,很好地彰顯了我國(guó)在科學(xué)制度體系建設(shè)與品牌管理方面的優(yōu)勢(shì),使我國(guó)的公開形象變得更加矚目。
三、當(dāng)前我國(guó)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產(chǎn)權(quán)法律保護(hù)存在的問題
(一)權(quán)利主體不清晰
盡管我國(guó)越來越重視對(duì)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hù),但是就如何保護(hù)卻并沒有相對(duì)規(guī)范性的綱領(lǐng)文件形成。即便是有關(guān)部門對(duì)關(guān)于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產(chǎn)權(quán)法律保護(hù)投入了思考,但是卻并沒有結(jié)合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真實(shí)情況,在保護(hù)制度上進(jìn)行調(diào)整和完善,更多的是按照基本的制度流程形式化地進(jìn)行制度內(nèi)容設(shè)計(jì),欠缺一定的公信力[2]。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產(chǎn)權(quán)主體存在模糊不清的界定情況,這是制度內(nèi)容設(shè)計(jì)最為不妥的地方。由于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形成有一定的歷史地緣因素,因而要準(zhǔn)確判定其權(quán)屬關(guān)系,就必須設(shè)立嚴(yán)格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通過對(duì)不同主體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上是否達(dá)到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分析,從而準(zhǔn)確地得出結(jié)論。但是在有關(guān)的法律中,僅僅是認(rèn)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歸創(chuàng)造者,這與實(shí)體物質(zhì)的著作權(quán)保護(hù)法內(nèi)容并無太大區(qū)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不同于實(shí)體物質(zhì),難以找到具體的創(chuàng)造者,在歷史的長(zhǎng)河中經(jīng)過了無數(shù)人的雕琢,更加難以確定首次創(chuàng)作者的身份。因而,從這一標(biāo)準(zhǔn)來判斷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權(quán)利主體,顯然不合時(shí)宜。
(二)保護(hù)期限的設(shè)立不匹配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價(jià)值是會(huì)隨著時(shí)間流逝歷久彌新的,它并不受時(shí)間空間的限制,具有不確定性,需要相關(guān)法人或其他組織長(zhǎng)期地享有權(quán)利并挖掘和探索新的實(shí)踐價(jià)值。但是現(xiàn)代著作權(quán)法明確規(guī)定了專利的保護(hù)期,與這一目標(biāo)背道而馳。當(dāng)今社會(huì)是互相聯(lián)系的社會(huì),我國(guó)在謀求世界認(rèn)可的過程中不斷融入全球化趨勢(shì),才能不被惡意詆毀和中傷。因而,如果按照國(guó)際公約標(biāo)明的專利著作權(quán)法來執(zhí)行,我國(guó)很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就必須在有限時(shí)間內(nèi)暴露在公共領(lǐng)域進(jìn)行實(shí)踐,但是這樣一來就很容易受到商業(yè)化的浸染,不利于維持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特性。
四、完善我國(guó)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律保護(hù)的建議
(一)明確權(quán)利主體
根據(jù)《著作權(quán)法》的規(guī)定,權(quán)利主體在創(chuàng)造完成一項(xiàng)作品后即享有著作權(quán)。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在歲月長(zhǎng)河中經(jīng)過眾人的合力而雕琢出來的美玉,其創(chuàng)造者存在廣泛性和群體性。如果依賴著作權(quán)法的現(xiàn)行規(guī)定,我們難以清晰準(zhǔn)確地找到權(quán)利主體。因此在權(quán)利主體的判斷過程中,哪些主體來代表發(fā)源地民眾行使該權(quán)利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二)設(shè)立匹配的保護(hù)期限
《專利法》規(guī)定發(fā)明的保護(hù)期為20年,實(shí)用新型和外觀設(shè)計(jì)保護(hù)期為10年。《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期為作者終生及其死后50年,法人或其他組織保護(hù)期為50年[3]。超過這個(gè)期限就會(huì)成為社會(huì)公共資源,不再得到法律的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會(huì)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而不斷傳承、發(fā)展的,對(duì)其的保護(hù)無疑更偏向于無限制的保護(hù)期限。正是這樣,在時(shí)間上現(xiàn)代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制度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上存在沖突。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設(shè)置的保護(hù)期限遠(yuǎn)遠(yuǎn)短于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所需要的時(shí)間。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由于其產(chǎn)生年代久遠(yuǎn),對(duì)社會(huì)適應(yīng)能力較弱。如果在得到短暫保護(hù)后就暴露在公共領(lǐng)域中,會(huì)受到市場(chǎng)和社會(huì)的沖擊,不利于其發(fā)展。
(三)健全行政法救濟(jì)制度
行政法救濟(jì)制度是一種以行政手段調(diào)節(jié)宏觀統(tǒng)籌質(zhì)量的制度措施,它主要立足于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的行為主體,為維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產(chǎn)權(quán)發(fā)揮監(jiān)督與執(zhí)法的合力。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制度保護(hù)不能僅僅局限于制度內(nèi)容的清晰和細(xì)化,更為關(guān)鍵的是加大對(duì)非法行為的打擊,渲染制度保護(hù)的氛圍。因而,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制度建立過程中,除了要梳理具體的權(quán)利主體,還要為保護(hù)權(quán)利主體和監(jiān)督權(quán)利主體、其他組織的行為配備執(zhí)法隊(duì)伍和監(jiān)管組織,對(duì)不同執(zhí)法人員的權(quán)利清晰劃分,將行政復(fù)議和行政訴訟的機(jī)制良性搭建,而且在此基礎(chǔ)上引入公益訴訟的制度,能夠進(jìn)一步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的公益性和社會(huì)效益?zhèn)鬟f出來,減少商業(yè)的介入。
(四)采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模式
從立法實(shí)踐來看,分為三種法律保護(hù)模式:一種是運(yùn)用現(xiàn)行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制度保護(hù),如美國(guó)、澳大利亞等國(guó)家;一種是建立特殊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進(jìn)行保護(hù),如巴西、泰國(guó)等;還有一種是建立專門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保護(hù),如日本、韓國(guó)。我們應(yīng)該建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模式:一是建立健全注冊(cè)登記制度;二是通過認(rèn)定傳承者并通過資金幫助傳承人提高從藝、生活條件,提高傳承人的社會(huì)地位;最重要的是注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播和推廣,促進(jìn)公眾的參與。
綜上所述,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迫在眉睫。作為長(zhǎng)期以來歷史實(shí)踐所形成的精神文化符號(hào),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時(shí)代價(jià)值是巨大的,對(duì)于傳遞國(guó)家的人文底蘊(yùn)有著積極的作用。因此,在對(duì)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hù)過程中,必須要結(jié)合新時(shí)代的發(fā)展特點(diǎn),規(guī)避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在保護(hù)中受到的商業(yè)化元素的影響,以社會(huì)行為文化滲透作為調(diào)節(jié)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力度的核心。制度保護(hù)是新時(shí)代鮮明的產(chǎn)物,又能衍生出一定的行為文化,進(jìn)而激發(fā)出保護(hù)者的責(zé)任意識(shí),必須進(jìn)行相關(guān)策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