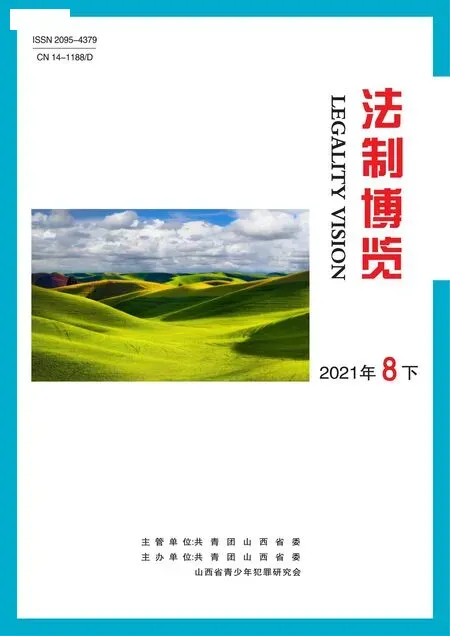司法實踐中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適用研究
薛榮娟
(中共洛陽市委黨校法學與科技文化教研部,河南 洛陽 471935)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簡稱《反家庭暴力法》)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國家庭暴力的發生率,特別是各地人民法院陸續簽發人身保護令,將人身保護令案件作為獨立案件進行審理,極大地彰顯了人身保護令制度在家事審判改革中的重要價值。[1]2021年1月1日起,在《民法典》的保駕護航下,如何進一步完善家事審判領域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成為我們當下尤其需要思考的問題。
一、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
我國每年各級婦聯收到的有關家庭暴力的投訴均達到4萬-5萬件,約占婚姻家庭類投訴的四分之一。[2]《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規定人身安全保護令的保護主體不僅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等近親屬,也包括其他具有親密關系的人。從性質上來看,“人身安全保護令”屬于一種民事強制措施。從意義上看,該項制度的實施體現出了對《反家庭暴力法》的落實和完善,是我國建設法治國家、法治社會進程中的重要一步,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體現。該制度不僅體現了我國立法“以人為本”的原則,對我們維護家庭美滿、社會穩定具有重要作用,而且還能夠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廣泛輿論,起到教育作用,對于在全社會范圍內倡導形成和諧友愛的家庭關系具有很強的適用性。
二、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的實施現狀及困境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20)》顯示,2020年我國共審結婚姻家庭案件185萬件,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2004份。以“人身安全保護令”“家庭暴力”為關鍵詞,以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實施之日起至2021年3月1日為時間區間,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共檢索到3349篇法律文書,平均每年約670篇。通過對這些裁判文書的梳理,我們也發現了不少問題:發達地區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簽發數量要遠遠多于不發達地區;申請人和被申請人多為夫妻配偶,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情況偏少;還有就是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駁回率高達20%左右。這都說明,我們在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實施的過程中還面臨著諸多困境。
首先,法律制度不健全。當前我國沒有相應的司法解釋或實施細則對人身安全保護令進一步細化,該法的具體內容也存在著諸多不合理的地方。[3]一方面,人身安全保護令的適用范圍太小,導致法官在司法實踐中只能把考量因素限定在“共同生活”這個框架里,而把現實中并未同居或共同生活的男女朋友、前配偶等都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該法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情況是否緊急分72小時或24小時之內簽發保護令或者駁回申請,但是對于“緊急情況”的范圍并未作出說明,對于簽發條件中的“面臨家暴現實危險的情形”也意指不明,完全需要法官依靠自己的主觀判斷作出裁定。
其次,舉證責任不清晰。有數據顯示,在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案件中,有64%是申請人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證據的案件。一方面是因為家庭暴力中受害者往往處于弱勢地位,不敢收集證據。加上傳統社會“家務事旁人不便插手的”的社會理念深入人心,導致受害人舉證困難;而且《反家庭暴力法》并未對家暴證據的采集做出具體規定,也沒有配套的司法解釋來幫助施行,法官只能根據現有證據規則作出判斷。而現行法律規定舉證主體一般是“誰主張誰舉證”,[4]且在證據的采納認定方面也沒有充分考慮家庭暴力案件的特殊之處,實際意義不大。
最后,違法成本低,追責難度大。從當下社會條件來看,《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的“一千元”處罰額度太低,成本太低,“15日以下的拘留”時間太短,對施暴者達不到懲戒效果。而且這里所說的“拘留”主體是法院還是公安機關,并沒有明確的指向;“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雖然上升到了刑罰的力度,但是《刑法》并未對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的行為明確罪名,該行為應該提起自訴還是公訴,是由法院檢察院還是由公安機關來偵查,都沒有明確的說法。
三、完善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的路徑選擇
(一)健全法律制度
要繼續完善《反家庭暴力法》,積極修改制定其他配套法律制度。例如,要對普通保護令和緊急保護令進行更加明確詳細的劃分;除了對受害者人身的保護,建議增加財產保護令,對夫妻共同財產和受害人的個人財產進行必要的凍結或保護;現有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簽發只注重對受害者個人的保護,建議利用計算機網絡和天眼系統及“雪亮工程”,對受害者和施暴者以及執法者的行為進行追蹤;放寬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方式,除了目前規定的書面口頭申請,要照顧到那些被施暴者拘禁的受害者,增加電話、郵件等特殊申請方式;另外,建立社區監督小組,保證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后續落實;同時要加強與其他部門法特別是《刑法》的銜接和協調,加大懲治力度,設置相關罪名,把嚴重違反人身保護令制度的行為入刑并提高刑期,加大處罰力度。同時要設置必要的救濟條款,對施暴者進行教育,加大宣傳力度,多管齊下。
(二)明確證據規則
一是擴大證據認定范圍。除了現有的告誡書、傷情鑒定意見、出警記錄等可以作為家庭暴力發生的證據,我們還可以將手機信息截圖、受傷照片,醫院的就診記錄、診斷書、收費單據,公安機關的出警記錄、訊問筆錄、告誡書,施暴人員的恐嚇信、保證書或悔過書、日記,還有比如社區領導、鄰居,特別是作為家暴見證者的、有一定辨識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證人證言等,只要這些證據能夠在時間和空間上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就完全可以采納認定,不能太拘泥于法律條文。二是轉移舉證責任。三是降低申請人的證明標準。我國現行民事證據采取的是“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也就是證據的證明力從概率上要達到75%,這個標準對于一般的民事案件來講已經算嚴格了,對于家庭暴力這種具有特殊性的案件來說更是難上加難。[5]實際上,人身安全保護令只是一個預防性措施,并不具有懲罰性和對配偶雙方利益的終局處置性,對它的認定并不需要如此高的蓋然性。因此,法院在處置此類案件時的證據采納標準應該適當降低,無須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只要達到普通人的標準就行,通過對法律價值判斷和對自由裁量權的運用,做出對保護令申請人有利的裁定。
(三)加強執行力度
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一直未在司法實踐中充分發揮作用,主要是因為執行不力,需要從三個方面加強。首先,對于人民法院來講,對于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簽發要求過于嚴格,限制過多。建議放寬條件,成立人身安全保護令專案小組,由婚姻家庭法領域內經驗豐富的法官組成,專門受理審查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對于符合緊急保護令情況的案件適用簡易程序,盡快簽發。其次,法律在制度設計上應該有所改善,將人民法院、公安機關和基層組織在家庭暴力案件處置中的各項權力明確下來,避免出現“九龍治水”的局面。特別是對于公安機關來說,一直以來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執行主體是人民法院,但是法院的司法警察又沒有實際的執法權,很多案件的進行需要公安機關的大力配合。因此,要對基層公安人員進行深入的普法培訓,使其深刻認識到家庭暴力并不是“家務事”,將“家庭暴力”和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的偵查處置納入公安機關的內部考核體系,切實提高每一位基層公安干警執法的敏感度。[6]同時,也要充分發揮其他輔助執行主體的功能,構建多方聯動切實有效的執行機制;此外,社區、單位以及其他社會組織也應該結合自身的特點和優勢,全面加入反家庭暴力的行列中來,進行普法和監督工作,互相配合、互相促進,從而保障《反家庭暴力法》和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在全社會范圍內的貫徹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