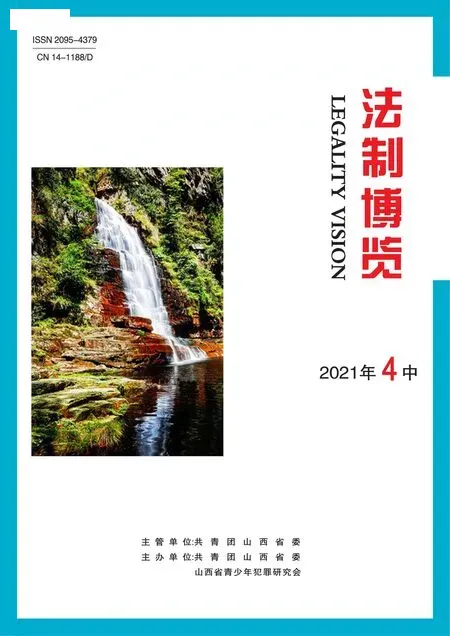檢察環(huán)節(jié)必須強(qiáng)化對(duì)客觀性證據(jù)的審查和把關(guān)
鄔賢彬 黃婷婷
(1.重慶市彭水縣人民檢察院,重慶 409699;2.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重慶 409000)
有觀點(diǎn)認(rèn)為,“辨認(rèn)筆錄、鑒定意見(jiàn)”應(yīng)當(dāng)納入客觀性證據(jù)類之中。筆者不贊成此觀點(diǎn),因“辨認(rèn)筆錄、鑒定意見(jiàn)”是人進(jìn)行主觀上的認(rèn)知而得出的結(jié)論,容易受到司法工作者主觀認(rèn)識(shí)水平高低的影響,也可能受到認(rèn)識(shí)錯(cuò)誤和人為操作的影響,故“辨認(rèn)筆錄、鑒定意見(jiàn)”應(yīng)當(dāng)屬于主觀性證據(jù)類。僅有被告人供述的案件,司法機(jī)關(guān)不得僅依據(jù)被告人單方面的供述認(rèn)定有罪,必須有相應(yīng)證據(jù)支撐,形成完整的證明鏈條,才能達(dá)到證明所要求達(dá)到的標(biāo)準(zhǔn)。在檢察環(huán)節(jié),要格外重視對(duì)客觀性證據(jù)的審查,學(xué)會(huì)運(yùn)用結(jié)合主觀性證據(jù)和客觀性證據(jù)二者的不同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證明目的,形成完善的證據(jù)鏈條。
一、偵查環(huán)節(jié)在運(yùn)用客觀性證據(jù)中存在一定缺憾
(一)不重視客觀性證據(jù)對(duì)于開(kāi)展偵訊工作的價(jià)值
“重主觀、輕客觀”等謬誤觀念根深蒂固,很多案件前期的偵查重心被放在了對(duì)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審訊上,而偏廢了對(duì)客觀性證據(jù)的運(yùn)用。這些信息有多種來(lái)源:文件和記錄、電腦數(shù)據(jù)、對(duì)被害者以及證人的詢問(wèn),以及對(duì)調(diào)查結(jié)果的審查,包括DNA、彈道特點(diǎn)、指紋、血跡和其他痕跡物證。總的來(lái)說(shuō),這些信息被稱為“案件事實(shí)信息”。上述列舉的案件事實(shí)信息,也即是在本文所闡述的客觀性證據(jù)。根據(jù)萊德教授的觀點(diǎn),優(yōu)先獲取和評(píng)估案件事實(shí)信息,是開(kāi)展偵訊活動(dòng)的必要前提,否則偵查人員就容易犯先入為主的錯(cuò)誤,嚴(yán)重影響詢問(wèn)及后續(xù)訊問(wèn)工作的效率。[1]
(二)不重視客觀性證據(jù)在證據(jù)體系中的重要作用
對(duì)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關(guān)鍵細(xì)節(jié),得到客觀性證據(jù)的佐證,就能起到較好的證明效果,這也符合客觀唯物主義的法則。比如,許多罪名的構(gòu)成要件中包含犯罪嫌疑人主觀上的“明知”,認(rèn)定主觀“明知”不能單靠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實(shí)踐中還需要重視綜合運(yùn)用客觀性證據(jù)和主觀明知的推定規(guī)則。
(三)不重視犯罪現(xiàn)場(chǎng)在偵查取證中的重要作用
在司法實(shí)踐中,許多現(xiàn)場(chǎng)勘驗(yàn)檢查活動(dòng)“形式化”嚴(yán)重,極少能提取與犯罪有關(guān)的痕跡、物證。如重慶某縣檢察院審查起訴的容留他人吸毒罪類案件當(dāng)中,時(shí)常發(fā)現(xiàn)偵查機(jī)關(guān)未對(duì)現(xiàn)場(chǎng)進(jìn)行勘驗(yàn)檢查的情形。而在容留他人吸毒的現(xiàn)場(chǎng)中,一般可以提取犯罪嫌疑人用于吸毒的工具、吸食毒品后的殘?jiān)⑴c吸毒人員指紋、DNA等痕跡物證或者生物樣本,可以更好地印證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案件事實(shí)。
二、檢察環(huán)節(jié)如何加強(qiáng)對(duì)客觀性證據(jù)的審查和把關(guān)
(一)充分發(fā)揮檢察機(jī)關(guān)法律監(jiān)督和引導(dǎo)偵查的作用
檢察官在審查案件的過(guò)程中,應(yīng)當(dāng)重視客觀性證據(jù)在證明體系中的價(jià)值和作用。要規(guī)范退回補(bǔ)充偵查程序,不能條款式地列舉,要細(xì)致地進(jìn)行說(shuō)明。要切實(shí)提升退回補(bǔ)充偵查文書的說(shuō)理性,要讓偵查人員明白為什么要補(bǔ)、補(bǔ)充的方向和需要補(bǔ)充的內(nèi)容,真正做到退回補(bǔ)充偵查文書的可操作性和指導(dǎo)性。對(duì)于未提取的重要的客觀性證據(jù),要及時(shí)說(shuō)明補(bǔ)充理由,協(xié)調(diào)偵查機(jī)關(guān)補(bǔ)充取證;要積極主動(dòng)開(kāi)展自行補(bǔ)充偵查工作,對(duì)于極易滅失、不易恢復(fù)的客觀性證據(jù),應(yīng)及時(shí)進(jìn)行自行補(bǔ)充偵查。
(二)堅(jiān)持客觀性證據(jù)審查模式,避免先入為主
先對(duì)犯罪嫌疑人進(jìn)行有罪推定是錯(cuò)誤的證據(jù)審查模式,主觀上先認(rèn)為被告人有罪,再去人為地發(fā)現(xiàn)和尋找證據(jù),這本就屬于一種錯(cuò)誤的證據(jù)審查模式。歷史經(jīng)驗(yàn)表明,冤假錯(cuò)案的發(fā)生往往與司法人員先入為主的錯(cuò)誤思維有密切聯(lián)系。在司法實(shí)踐中,檢察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摒棄有罪推定的錯(cuò)誤觀念,秉持客觀中立的立場(chǎng),轉(zhuǎn)變捕訴環(huán)節(jié)的證據(jù)審查模式:要以客觀性證據(jù)為審查判斷的出發(fā)點(diǎn)和落腳點(diǎn),結(jié)合口供、證言等主觀性證據(jù),搭建完整的證明體系,全面審查與犯罪嫌疑人有關(guān)的有罪證據(jù)、罪輕證據(jù)和無(wú)罪證據(jù),著重審查證據(jù)之間的合法性、關(guān)聯(lián)性和真實(shí)性。
(三)注重審查現(xiàn)場(chǎng)勘驗(yàn)、檢查筆錄、電子數(shù)據(jù)等證據(jù)
因犯罪活動(dòng)自身的隱蔽性,許多案件除被告人的口供之外難以獲得其它證據(jù)加以佐證,尤其當(dāng)被告人不認(rèn)罪時(shí),案件更加難以處理。故而,在審查起訴環(huán)節(jié),檢察官一定要注重審查在犯罪現(xiàn)場(chǎng)遺留的痕跡線索。俗話說(shuō),雁過(guò)留痕,風(fēng)過(guò)留聲。任何犯罪行為都會(huì)在犯罪的現(xiàn)場(chǎng)留下痕跡、線索,這些痕跡、線索就是推演犯罪行為、還原案件真相的關(guān)鍵證據(jù)。甚至可以說(shuō),即使現(xiàn)場(chǎng)完全不留下任何證據(jù),也是犯罪嫌疑人反偵察能力強(qiáng)的一種表現(xiàn)。故,重視現(xiàn)場(chǎng)遺留的痕跡、線索對(duì)于檢視犯罪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四)注重運(yùn)用現(xiàn)場(chǎng)勘驗(yàn)、檢查筆錄還原犯罪現(xiàn)場(chǎng)
犯罪現(xiàn)場(chǎng)是掌握犯罪線索的第一手資料。從某種意義上來(lái)講,犯罪現(xiàn)場(chǎng)是犯罪發(fā)生過(guò)程的“攝影機(jī)”,它是一個(gè)“不會(huì)講話的見(jiàn)證者”,而我們需要盡力做的就是讓犯罪現(xiàn)場(chǎng)“開(kāi)口講話”。這非常考驗(yàn)我們司法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的工作經(jīng)驗(yàn)和業(yè)務(wù)能力。還原犯罪現(xiàn)場(chǎng)的意義和價(jià)值之一就是使司法工作人員更容易接近事實(shí)真相,推演犯罪過(guò)程,得出相對(duì)可信的結(jié)論。如重慶某縣檢察院辦理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當(dāng)中,犯罪嫌疑人安某供述其在一條村級(jí)道路上,車輛發(fā)生溜車,從被害人李某身體上碾壓而過(guò),車尾頂?shù)綁Ρ诤笸O隆@钅潮粔旱购髾M躺在公路中央離車輛左前輪20公分處。安某為逃避法律責(zé)任,駕車逃離案發(fā)現(xiàn)場(chǎng)。據(jù)安某供述,被害人李某尸體在車輪不遠(yuǎn)處,若要駕車駛離現(xiàn)場(chǎng)則必須從李某身上碾壓過(guò)去,造成二次碾壓。但根據(jù)現(xiàn)有證據(jù),并不能證明安某的二次碾壓行為。因此,找到證實(shí)安某有二次碾壓行為的客觀性證據(jù)至關(guān)重要。而現(xiàn)有證據(jù)中,尸體檢驗(yàn)報(bào)告從傷痕鑒定中無(wú)法得出李某被二次碾壓的結(jié)論。理論上,只有采取另一種方式判斷安某是否有駕車二次碾壓的行為:即通過(guò)現(xiàn)場(chǎng)重建。具體操作方法如下:根據(jù)犯罪嫌疑人所駕駛的車輛損傷痕跡與被撞墻壁痕跡,按照事故發(fā)生時(shí)的車輛狀態(tài)停放車輛,再使用與被害人身高體型相符的人體模型放置在車輛前方20公分處,重建現(xiàn)場(chǎng)環(huán)境,通過(guò)偵查實(shí)驗(yàn),推演車輛能否在不碾壓人體模型的情況下向前通過(guò),最終得出相對(duì)可靠的結(jié)論。
(五)注重審查物證的收集、提取、封存、保管、移送程序
規(guī)范物證的收集提取、封存、保管、移送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意義極其重要,未按照法律規(guī)定,對(duì)物證進(jìn)行收集提取、封存、保管、移送,可能會(huì)影響該物證的證明力,嚴(yán)重者甚至?xí)沟迷撐镒C喪失作為證據(jù)使用的條件,觸發(fā)非法證據(jù)排除程序,導(dǎo)致關(guān)鍵證據(jù)被排除。檢察官在審查案件時(shí),要聚焦證據(jù)的來(lái)源和收集程序,著重進(jìn)行審查把關(guān)。類似的規(guī)定絕不局限于前文列舉的部分,客觀性證據(jù)的收集程序在刑事訴訟活動(dòng)中一直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上述規(guī)定中所蘊(yùn)含的精神應(yīng)適用于所有客觀性證據(jù)的取證,未另設(shè)規(guī)定的罪名,并不意味著其他罪名的物證收集程序具有隨意性,相反,更應(yīng)當(dāng)將上述法律規(guī)定中所蘊(yùn)含的“依法、客觀、準(zhǔn)確、公正、科學(xué)和安全”的原則貫徹到收集取證和證據(jù)審查程序的全過(guò)程。
(六)完善協(xié)調(diào)配合機(jī)制,提升客觀性證據(jù)審查判斷能力
檢察機(jī)關(guān)還應(yīng)進(jìn)一步加大對(duì)物證型專業(yè)人才的培養(yǎng)力度,建立物證類檢察專業(yè)人才智庫(kù),為破解基層辦案難題提供指導(dǎo)和支撐,以緩解物證技術(shù)人才短缺之現(xiàn)狀。檢察機(jī)關(guān)、公安機(jī)關(guān)雙方在《刑事訴訟法》上的職責(zé)分工不同,但需要在刑事訴訟活動(dòng)中彼此配合。公安機(jī)關(guān)擅長(zhǎng)對(duì)案件的前期摸排、偵破,而檢察機(jī)關(guān)則擅長(zhǎng)對(duì)案件事實(shí)的法律定性和對(duì)證明標(biāo)準(zhǔn)把關(guān)。為強(qiáng)化二者間的工作合力,一方面檢察機(jī)關(guān)、公安機(jī)關(guān)雙方要健全協(xié)調(diào)聯(lián)動(dòng)機(jī)制,打通案件信息分享交流渠道,建立檢警統(tǒng)一的業(yè)務(wù)信息系統(tǒng);另一方面檢察機(jī)關(guān)、公安機(jī)關(guān)要加強(qiáng)案件交流、案例研討、聯(lián)合調(diào)研,統(tǒng)一司法觀念,爭(zhēng)取達(dá)成重視客觀性證據(jù)的理念共識(sh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