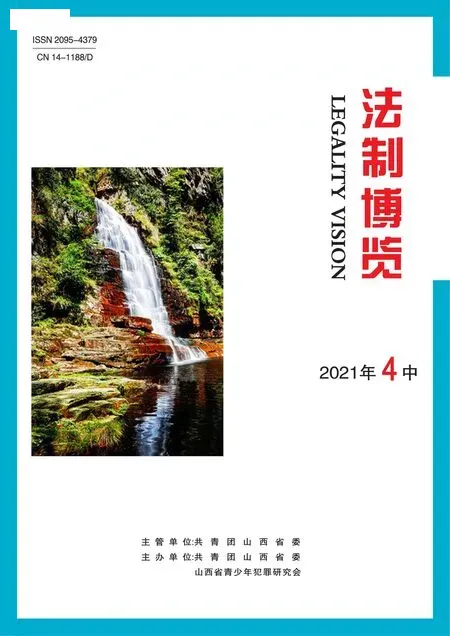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涉眾型案件中的適用
吳菊萍 田 婧
(1.海鹽縣人民檢察院,浙江 嘉興 314300;2.德清縣人民檢察院,浙江 湖州 313200)
一、引言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當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三大主要任務之一,直接連通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1]。“公正為本,效率優先”應當是認罪認罰制度改革的核心價值取向[2]。近年來,公檢法案多人少矛盾愈加突出,刑事訴訟證據裁判要求和證明標準增高,公正司法的成本在加大。然而,由于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愈加隱蔽,通過網絡實施的涉眾型案件越來越多,偵查機關收集證據的難度越來越大。特別是涉眾型犯罪涉案人員眾多、被害人數眾多、涉及地區廣,帶來取證難度大、辦理時間長,偵查、起訴、審判階段均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訴訟效率低,司法資源浪費嚴重,且追贓挽損難度大,被害人損失難以挽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重要的刑事訴訟制度貫穿刑事訴訟始終,在偵查階段即鼓勵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促進案件繁簡分流,為案件進一步偵查及偵破提供基礎。不僅如此,認罪認罰還能為嫌疑人帶來實體上的從寬處理以及程序上地從快、從簡;同時,檢察機關、法院也通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縮短了辦案期限,提高了辦案效率,優化司法資源配置;實體上的從寬以及值班律師的介入亦為嫌疑人提供了充足的人權保障。辦理涉眾型案件中充分地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能為此類案件的辦理帶來便利,也讓該制度在實踐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認罪認罰制度在涉眾型案件中適用存在的難點和問題
(一)審查難度大、訴訟效率較低。由于涉眾型案件具有涉案人數眾多、受害人數眾多、犯罪事實眾多,以及取證難度大等特點,必然帶來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時審查難度大、訴訟效率低的問題。從本院往年辦理的涉眾型案件的期限看,涉眾型案件在偵查階段往往經過二延,在檢察機關也往往經過二延二退,到了審判階段法院也往往需要延期審理,有些案件到審判時被告人已被羈押長達1年,甚至更久。
(二)追贓難度大,退贓率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退贓退賠能夠在事后彌補被害人的損失,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在量刑上,對其從輕或減輕處罰合乎常理[3]。事后積極退贓、賠償損失與積極挽回損失的行為是減少預防刑的情節[4]。在司法實踐中絕大多數的涉眾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退贓率卻不高,主要原因有:第一,主犯未被抓獲,從犯作為下層人員所分配到的利益不多或者分配到的利益早被揮霍一空,沒有能力退贓。第二,有些主犯雖被抓獲,但其早已將錢款轉移至海外,有能力卻不愿退贓或只退部分。第三,現有法律對于退贓在量刑上從寬的規定不明確,導致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猶豫不決。退贓作為一種酌定的量刑情節,屬于可以從輕,從輕幅度依賴審判人員的主觀裁量。且司法實踐中不嚴格區分“全部退贓”和“部分退贓”在量刑上的不同,籠統地以“可酌情從輕處罰”置之,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法律的指引功能,提高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退賠積極性。
(三)嫌疑人反偵查意識強,認罪認罰率較低。涉眾型案件多數以集團、團伙形式出現,內部管理嚴格,層級分明,對參與的成員進行統一培訓,設有嚴格的內部規章制度,甚至傳授對抗偵查、審查的手段和方法。故而多數犯罪嫌疑人歸案后對抗審查,拒不供認。
三、涉眾型案件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
(一)分化瓦解、逐個擊破。法律應盡少促成犯罪同伙之間可能的團結[5]。在這里,貝卡利亞認識到共同犯罪團結合作所造成的危害和影響,認為處罰共犯時,法律應盡可能地破壞共同犯罪人之間的團結。毫無疑問,鼓勵共同犯罪人之間互相揭發,便是非常有效的手段[6]。在涉眾型案件中可根據組織內部不同層級進行分化瓦解,對參與度低、涉案金額低、參與時間短、最終可能適用緩刑的底層人員,偵查階段加大釋法說理力度,爭取這些人員坦白、認罪認罰,并對其采取非羈押的強制措施。其次,對于中層的管理人員,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有緩刑可能的人員,可進行適當的證據開示,引導其認罪認罰。最后,對于主犯應加強釋法說理工作,并一定程度上限縮“量刑平衡”,給予其較大程度的從寬,積極促成其認罪認罰。
(二)積極促成退贓,最大程度挽回被害人損失。涉眾型案件辦理過程中要尤其注重退贓退賠工作,在偵查階段要及時扣押、凍結相關的涉案財物,以防未歸案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其家屬將贓款轉移。起訴階段,檢察人員在認罪認罰精準量刑時應體現退賠程度與從寬幅度的正向關聯。
(三)檢警合作,提前介入,提升訴訟效率。切實發揮重大案件提前介入和檢察官辦公室的作用,在偵查階段,派檢察官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在批捕審查時將需要補證的問題梳理并以補證提綱的形式移送偵查機關,并督促偵查機關及時補證。爭取在案件移送起訴時相關證據都能取證到位,確保起訴階段不需要退補、延長,提升訴訟效率。
(四)合理運用“分案處理”,提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效率價值。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客觀原因,一個案件中的嫌疑人部分認罪認罰部分不認罪認罰,也存在全部的犯罪嫌疑人都認罪認罰,但是一部分認罪認罰的嫌疑人不愿意適用簡易程序,根據相關司法解釋,上述兩種情形禁止適用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只能適用普通程序。201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規范刑事案件“另案處理”適用的指導意見》中的第二條對另案處理的概念進行了規定,該意見規定將共同犯罪及關聯性犯罪中不能并案審理的案件,通過法律的規定與共同犯罪或關聯性犯罪中其他的被告人單獨處理。實踐中司法機關為了便于查明事實、節約訴訟成本一般將共同犯罪案件并案處理,但是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背景下的涉眾型案件,如果存在部分犯罪嫌疑人愿意適用簡易程序,部分不愿意適用簡易程序的,再進行并案處理無法體現認罪認罰程序價值,實踐中可以對此種情形進行分案處理,對于愿意適用簡易程序的犯罪嫌疑人適用簡易程序進行審理,對于不愿意適用簡易程序或者不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則由同一審判組織適用普通程序分案進行審理。
(五)限縮適用“量刑平衡”,激勵主犯認罪認罰[7]。兩高三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中第二條規定要按照主從犯在犯罪中作用大小等準確裁量刑罰,保證量刑平衡。量刑平衡的設置實際是為了刑罰量配置的公正與合理,一般情況下,在量刑時既要實現刑罰的均衡,滿足社會公眾的公平感,又要兼顧刑罰的個別化,有利于被告人復歸社會,兩者不可偏廢。我們所追求的量刑平衡是一種相對的均衡,并非絕對的數值上的等同。同一個案件中的不同嫌疑人因其所起的作用不同、獲得的利益不同,歸案后的認罪態度不同等,會有不同的量刑。現實情況中因為“從犯”“脅從犯”屬于法律規定的應當從輕、減輕的法定量刑情節,一般實踐中對于從犯都會“降檔”處理,且從犯只需要對自己所參與的部分犯罪事實負責,即便從犯不認罪認罰,主犯認罪認罰,從犯的量刑一般不會高于主犯的量刑。故,筆者認為在實踐中為激勵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認罪認罰,可適當加大對其從寬幅度,只要不過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