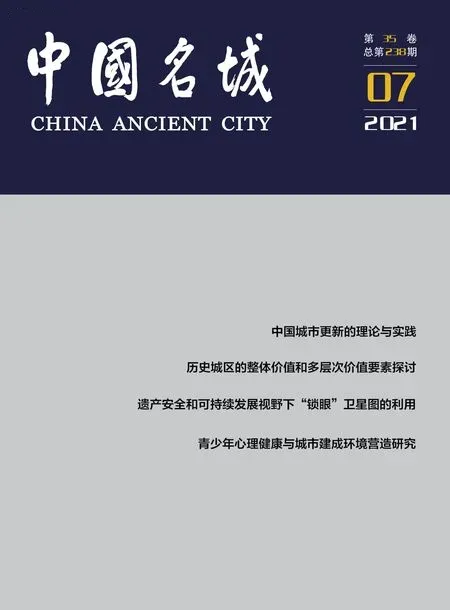國外逆城市化的研究
霍露萍
(西安外國語大學經濟金融學院,西安 710128)
引言
城市發展階段經歷了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個不同的變化過程[1],逆城市化是城市發展的必經階段。隨著中國城市發展進程的加快,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大城市中心區出現了人口密集、交通擁擠、環境污染、房價上漲、城市管理混亂等“城市病”現象。在城市化進程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企業為降低成本,追求利益,開始向中心區外圍遷移,形成一種工業郊區化現象;隨著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道路交通條件的改善,中心區人口逐漸向外遷移,形成人口郊區化現象;人口在外圍居住的需求增加,外圍住宅區建設加快,形成住宅郊區化現象。這些現象被學界稱為相對于城市集聚的離心分散化現象,實質上也代表了大城市地區已經開始了疏散化(逆城市化)進程或趨勢。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最發達的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在城市集聚發展的同時逐漸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逆城市化發展對于城市發展而言是一把雙刃劍。逆城市化發展對城市發展的有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逆城市化降低了中心區的人口密度,提高了大城市地區外圍的人口密度,使人口密度分布趨于更加均勻的狀態;其次,疏散了勞動密集型和污染嚴重的工業企業,降低了環境污染;最后,金融、貿易等效益更高的服務業取代了原有的工業,從而提高了中心區土地利用率,并促進了中心城區商業金融、貿易、房地產業的發展。反之,逆城市化對城市發展的不利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四方面:首先,逆城市化增加了通勤距離,增大城市通勤流量,進而增加了交通壓力;其次,逆城市化導致城市向外不斷蔓延,侵占了城市邊緣區的優質土地,破壞綠地、林地等資源,導致生態環境失去平衡;再次,人口外遷和郊區城市基礎設施配套不匹配,導致人戶分離現象大量存在,增加了人口管理難度;最后,鄉村規劃滯后于人口外遷,導致土地利用功能分區與布局在疏散化出現后相對混亂。國外學者對于逆城市化的內涵界定具有很大的爭議,并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以Berry為代表的學者認為逆城市化是人口的分散過程。第二階段在21世紀初,以Mitchell為代表的學者認為逆城市化是一種城市等級的轉變,人口由城市向農村流動[2]。第三階段以Feinerman為代表的學者認為逆城市化是鄉村振興的實現方式[3]。中國大城市地區已經出現逆城市化的現象,國內學者對于中國大城市地區逆城市化的研究較少,甚至有的學者不認同中國已出現逆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具體而言,中國對于逆城市化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不同進展階段呈現不一樣的解釋。第一種解釋至20世紀末,大多學者對國外逆城市化問題的轉述,未形成一定的理論體系,并提出為避免逆城市化現象的出現,中國應控制大城市發展,合理發展中小城鎮的觀點。第二種解釋認為逆城市化是一種郊區化或“非轉農”現象。第三解釋認為逆城市化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必然選擇[4]。所以,對于逆城市化問題的研究至今也有40多年的歷史,而其作為城市發展階段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對于中國城市發展具有顯著影響。2018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亦提出,將城鎮化和逆城鎮化兩個方面都要致力推動,以此表明逆城鎮化對于中國現階段城市發展具有重要影響關系。基于此,本文通過梳理國外學者關于逆城市化問題的研究進展,對于中國正確認識逆城市化問題具有一定的意義。文章從逆城市化的內涵界定、形成的動力機制、研究的內容等方面進行論述。
1 逆城市化的內涵界定
1.1 逆城市化的概念
Berry在1976年提出美國城市化歷程中的一個轉折點已經來臨。逆城市化已經取代城市化而成為塑造這個國家居住模式的主導力量。Berry根據Tisdale在1942年提出的城市化概念,推理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指出逆城市化是一個人口分散的過程,它暗示著一種從較集聚的狀態到低集聚狀態的過程。逆城市化的特點是小規模、低密度、異質性的下降,在國家相互依存的半徑范圍內迅速擴大。1978年,Daniel Vining、Thomas Kontuly在《大都市地區人口分布的國際比較》一文中指出,“在20世紀70年代前后,工業化國家中心城人口的數量隨著這些國家的邊遠地區和外圍地區人口的流動逐漸下降,且這種下降趨勢一直在持續……在許多地方已經形成了人口的邊緣化和農村地區的凈流動。”[5]A. J.Fielding在1982年分析了1950—1980年西歐人口再分配情況,并以法國為例,從人口流動的視角實證分析得出,逆城市化并不是城市人口減少的結果,也不是郊區化的更大范圍,更不是經濟衰退的暫時影響[6]。隨著逆城市化現象逐漸顯現,其他學者也對逆城市化進行了相關界定。大多數學者認為逆城市化的概念并不等同于城市化,而是指郊區地帶以外大都市區域的低密度擴張。Moreno在1987年通過研究西班牙的人口分布得出初期的逆城市化以中小城市的人口增長為特征[7]。Champion將逆城市化定義為城市人口和經濟向偏遠高質量環境的擴散[8]。Domingo等通過研究1975年至1986年西班牙瓦倫西亞省的人口分布情況,發現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及退休人員大多居住大城市的郊區[9]。Arroyo認為大都市地區人口的重新分布是城市層次和等級的轉變,并且是向更少的等級和多級關系轉變。Panebianco、Kiehl研究發現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城市居民人口向鄉村流動已經成為一種突出的現象。這種在美國和歐洲共同體出現的人口統計上的變化被人們稱為“逆城市化”現象[10]。Mitchell認為逆城市化是指在城市等級制度下的移民運動,即大量人口從城市遷移到農村[2]。Kahsai、Schaeffer通過實證分析得出20世紀50年代之后瑞士核心城市的人口增長十分緩慢,并于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期之間達到了逆城市化的高峰[11]。Feinerman等指出美國等發達國家人口由城市向農村的流動,即逆城市化現象已經十分顯著[3]。可見,大多數國外學者認為,逆城市化就是人口從城市流入農村的一種運動,而且城市人口增長速度低于農村人口的增長速度。
1.2 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及疏散化的比較研究
1.2.1 城市化、郊區化與逆城市化的異同
Hope Tisdale在1942年提出城市化是人口集中的過程,并且以兩種方式進行:集聚點的增加和個體集聚規模的增加,它暗示著一種從低濃度狀態到更集中狀態的過程,并指出城市化是空間人口集中的過程,通常被測量為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百分比的相對變化[12]。Fielding認為都市地區不論是城市化還是郊區化,都是以人口分布情況作為分析的出發點來判斷[13]。“落戶城市化”是凈遷入人口與總人口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隨著大城市(包括大都市區)總人口份額的增加而增加。而“落戶逆城市化”是凈遷入人口與總人口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它是隨著包括大都市區在內的最大城市人口遷移率高于其他規模的人口的遷移率[8]。“大都市區城市化”是以郊區為代價,大都市區人口逐漸聚集在中心城的過程。而“大都市區的郊區化”是中心城市的居民人口逐漸向郊區流動的過程[14]。
1.2.2 郊區化與逆城市化之間的異同
從凈遷入人口和總人口之間關系看,城市化表現為凈遷入人口與總人口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并隨著大城市地區總人口份額的增加而增加[8]。城市化是以郊區為代價,大都市區人口逐漸集聚在中心城的過程[12,14]。然而,由于郊區化的發展,都市地區人口再分配研究逐漸成為分析的重點內容[13]。逆城市化表現為凈遷入人口與總人口規模的負相關關系,它是包括大都市區在內的最大城市人口遷移率高于其他規模的人口遷移率[13,15]。城市化、郊區化和逆城市化的過程通過城市生命周期和極差城市化模型聯系在一起[16-18]。郊區化和逆城市化均屬于城市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二者的不同之處有兩點:一是郊區化和逆城市化是城市化過程中的兩個不同階段,先有郊區化,后有逆城市化;二是二者產生的原因不同,郊區化是城市化自然形成的結果,而逆城市化是城市化過程的必然產物。二者對于郊區的發展均有積極的推進作用。
1.2.3 郊區化、逆城市化及疏散化之間的關系
郊區化和逆城市化均被包含在疏散化之中。離心疏散表現為由人口從鄉到城的單向流動轉變為城鄉雙向流動的過程,即大城市地區出現了中心區人口增速低于外圍地區人口增速,而外圍地區人口密度不斷增加的現象。對于這種現象,國外相關研究者將其區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即郊區化和逆城市化。郊區化是指城市化地區內部從中心市區向外圍郊區的分散過程;逆城市化屬于城市化地區向非城市化地區的分散過程[19]。
工業化的發展帶來了農村人口遷移,從而導致城市化的發展,大城市地區的發展通常是以郊區和非都市地區人口的遷移為主。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離開城市,這首先導致了郊區化,接著是逆城市化。人口遷移的初衷是為了獲得工作或教育。然而,隨著時間的推進,人們開始追求更舒適的生活環境。這種遷移是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居民生活周期的變化共同導致的。
2 逆城市化的動力機制
造成逆城市化現象的驅動因素有很多方面,通過梳理文獻可分為以下4種。
一是交通、通訊和工業技術的發展促進人口遷移。當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原有人口向市中心集聚轉向外圍地區的集聚。如交通技術的快速發展,促使人口由中心向外圍遷移,改變了原有的人口分布格局。Nathaniel Baum-Snow通過研究1950年至1990年間美國大都市區人口和中心城市人口的變化,評估了新的有限高速公路的建設對中心城市人口下降的貢獻度,估計得出通過中央城市的一條新公路將其人口減少了大約18%。但是如果沒有建立州際公路系統,中心城市總人口將增長約8%。而隨著網絡的全面覆蓋,人們可以實現在家辦公的便利條件,不用再選擇在較為昂貴的市中心居住,轉而選擇在郊區居住。企業在考慮成本的基礎上,會選擇在遠離市中心的地區進行生產,吸引部分勞動力轉向外圍地區,進一步促進人口的外遷。城市經濟增長區域逐漸分散在郊區,非大都市地區和中心城市周邊地區。而原有的中心城出現重工業增長緩慢,甚至不增長的局面。
二是經濟因素和人口的發展促進逆城市化發展。Champion認為,逆城市化現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某些特殊事件的影響,且受經濟和人口的因素最大。以美國20世紀70年代“逆城市化”現象形成來看,其經濟因素主要包括能源危機和經濟衰退;而人口因素主要是戰后“嬰兒潮”出生的大多數人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大學,而大學大多位于美國的非都市區,這些大學生大多涌入非都市區,從而導致非都市區人口的增加。他認為,這一時期的“逆城市化”現象屬于一種反常現象,當這一時期的經濟和人口因素過去之后,城市發展自然進入正軌[8]。Gkartzios觀察到希臘城市和其他各省在經濟危機方面的差異[20],而該領域的其他研究人員也提出希臘農村可作為一種避難場所[21]。Kyriaki Remoundou等研究結果表明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城市居民更傾向于選擇靠近大城市的農村地區,這樣可以融入國際流動人口,并且認為經濟危機造成了城鄉人口流動,尤其是對于年輕人和失業者而言[22]。
三是農村經濟的發展及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導致人口回流。Ladanyi、Szelenyi指出逆城市化的動因包括農村地區在時間、經濟結構調整和區域政策方案方面導致的人口外流減少[23]。Geyer提出,最初人口流動的主要動機是為了獲得工作和教育,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流動是為了能夠有更舒適的生活環境[24]。Hans、Sten認為斯堪地納維亞半島國家的逆城市化也出現在1970年以后,除類似于德國將工業化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外,地方分權的政治制度還促進了農村地區的繁榮興旺[25]。Milbert提出二戰后的德國在經歷了城市化高峰后,于20世紀60—70年代將工業逐漸從城市轉向農村,伴隨著產業的轉移,農村出現了“非農業鄉村居民點”,美麗鄉村行動計劃吸引更多的人口從城市遷徙至農村定居[26]。Roland、L?ffler、Ernst Steinicke通過分析逆城市化在內華達山脈山區的社會經濟效應影響中得出,旅游業是大都市區人口向高海拔地區擴散的最重要的推動力[27]。Bierens、Kontuly提出關于逆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居民對于鄉村生活的生態經濟因素的影響[28]。Irwin等通過回顧相關的農業經濟文獻得出,美國農村地區的自然資源優勢是吸引城市居民返回農村的主要原因[29]。此外,發達國家農村地區持續上升的收入水平和不斷增加的就業機會也是吸引城市居民逆城市化的重要因素。工業化吸引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形成了城市化,大城市的發展主要是以郊區和非都市地區的移民為代價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開始離開城市,形成了郊區化,然后是逆城市化。這種移民流動是“生產主義者”和“環保主義者”主要動機的結果。然而,來自其他歐洲國家的研究顯示出截然相反的經驗,Gkartzios、Scott和Grimsrud認為逆城市化為農村社區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機會,其中涉及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只是中產階級),且與鄉村田園式的建筑無關[30-31]。
四是其他方面,如新的區位選擇、生活成本、犯罪、自然環境等。城市生活成本偏高導致人口向外流動。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年輕人由于職業選擇、婚姻、育兒和退休等生命周期的變化會選擇新的區域進行新的生活,房地產開發商為滿足這種情況,會在周圍地域開發房地產。從而促使一部分人在城市周圍生活。在英國,長期和持續的逆城市化通常是與農村的殖民統治相聯系的,這一現象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居民在農村生活[32]。另一方面是傳媒時代的發展,文化的傳播等導致中心城外圍的增長和中心城城市化的衰落。Stark、Taylor則認為勞動力回流與城市的吸引力不足有關,城市工作獲取相對艱難、生活成本偏高以及家庭生存風險較大等原因致使農民工家庭作出了回鄉的理性選擇[33]。Ladanyi、Szelenyi認為由于失業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城市人口逐漸向外流動[23]。Joony-Hwan O H研究1980—1990年期間美國大都市區中心城市和郊區人口的動態變化過程,結果表明大城市地區人口的變動受犯罪和就業機會的雙重影響[34]。因居民收入增加、通勤時間和成本降低、種族矛盾及犯罪率增加,居民居住郊區化,此外,城市中心環境污染加劇、交通擁擠導致的產業郊區化成為城市郊區化的主要原因[35]。在中心地區與外圍地區,由于各種生活成本和溝通成本之間的比例發生了變化,許多城市向外圍擴展,出現了郊區化和城市之間人口密度平坦化的現象[36]。
3 逆城市化的研究內容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外對于逆城市化的研究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1980—2002年,萌芽期。在這一階段,以Berry為代表對逆城市化的概念和現象進行分析和探討,并采用人口流動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和檢驗。在此時期內,國外學者對逆城市化文獻研究較少,究其原因是將逆城市化稱為“反城市化”,視作與城市化相對立的一種發展階段,或是一種城市蔓延的方式,一種“壞”的發展方式,很多學者不接受這種城市發展方式。第二階段:2003—2008年,成長期。這一時期以Mitchell為代表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對逆城市化進行界定和分析。研究內容開始涉及城市體系的發展方向,運用地理學方法對人口流動和城市空間布局等進行可視化分析,以此能夠較好地驗證城市的發展階段。第三階段:2009年至今,爆發期。以Feinerman為代表的研究者著手研究逆城市化與鄉村復興、農村發展等多方面,并從人們對農村生活方式、生活偏好,以及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等方面進行研究。
3.1 逆城市化的內容分類
根據研究內容的集中性,可總結為三大類:第一,逆城市化內涵是研究逆城市化問題的基礎;第二,人口組群是逆城市化的具體表現形式;第三,多中心主義是逆城市化的空間布局形式。
第一,逆城市化內涵界定。Berry最早根據Tisdale所提出城市化概念的基礎上推理出逆城市化的概念,并指出逆城市化是人口由集聚狀態轉向分散狀態的過程。此后很多學者也一直沿用這個概念。到20世紀末,Arroyo、Panebianco and Kiehl和Fielding等學者提出,逆城市化是大都市地區人口的重新布局,大量人口由城市向鄉村流動,城市等級層次發生轉變,人口空間布局的重新分配導致中小城鎮發展加速[5-6]。城市經濟增長點不再單單是城市中心,而逐漸向郊區和小城鎮分散。因而,逆城市化是實現鄉村復興的一種方式,不僅提高鄉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可以帶動鄉村經濟的快速發展。
第二,人口重新組群是逆城市化的具體表現形式。在城市化集聚時期,城市吸引力較強,大多數人口不斷向市中心集聚,形成人口向心集聚的現象。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城市病”問題凸顯,如交通堵塞、環境污染、人口擁擠等,人們更意愿向往郊區或是鄉村等環境優美的地方。企業為降低成本也向郊區或農村搬遷,部分勞動力為就業而選擇去郊區上班,在一定程度上疏散了一部分市中心人口。此時,房地產業尋求契機,增加房地產的投資和建設,以較低的價格吸引房客入住,部分人口選擇在郊區居住。這樣,原有人口在市中心集聚轉而向城市外圍的地區集聚,實現人口的重新組群。
第三,多中心性是逆城市化的空間格局形式。城市化的發展正是由于資本、資源和技術對某一地區產生本地化效應,從而使得這一地區成為集聚中心,并且通過道路沿線對周圍腹地產生輻射帶動作用,促使周圍貧窮地區的大量勞動力向中心地區集聚,以此,該中心地區成為主要的創新和增長中心,而周圍地區只為其中心地區提供必要的需求而得以生存。隨著創新的不斷發展,這種中心城市的核心力量已經解體。由于運輸方式和新的交流方式的改善打破了這種模式。經濟增長區域不再是集中于同一個市中心,而是形成在郊區、非大都市地區和中心城市周邊地區等多個地區。城市空間格局由單中心的城市中心逐漸向多中心的城市空間格局轉變。
3.2 逆城市化促進鄉村振興的發展
21世紀初,學者開始意識到逆城市化與鄉村復興有著一種必然的聯系。由于城市地區現有的環境和社會問題,比如污染、犯罪和種族主義等,這種種原因導致了人口逐漸向小型居住點和環境質量更好的農村地區遷移[2-7]。由于技術進步、通信的改善及農村工業化的進程加快等,農村人口增加,為農村的發展帶來生機。這將進一步促使農村地區的進一步發展,從而增加農民收入,增加農村地區的就業機會,提高農村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提高社會公共服務水平,實現城鄉均衡和城鄉一體化發展。Berry、Vining、Kontuly及Fielding指出城市的衰落將標志著大都市區的未來,就像過去城市增長一樣[5-6]。Cloke從農村的角度對逆城市化進行了解釋,他認為逆城市化就是農村復興[37]。Grimes研究了多尼戈爾、利特里姆和斯萊戈等傳統上為農村和落后的西部縣城的非農就業增長情況,發現其出現一個雙重過程,即成年人遷回農村,而青年人遷移出農村[38]。Brady、Gillmor 和Jeffers認為農村復興與逆城市化有關。Brady發現都柏林市中心人口出現下降,人口遷移至郊區及郊區的農村地區[39]。Gillmor、Jeffers研究發現在1961年至1981年期間,由于移民返回,勞斯縣小村莊人口增加及經濟增長[40]。Coward和Cawley通過研究1970年至1986年的人口趨勢,認為在此期間,農村和郊區具有很大增長,而相較于傳統上繁榮的東部地區,西部地區具有一定的相對增長趨勢[41-42]。Champion、Watkins提出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人們逐漸從城市向鄉村遷移,這也是英國城市化進程的最后階段[43]。Hourihan研究表明,愛爾蘭的三個主要城市都柏林、科克和利默里克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人口急劇下降,而遷移出的人口促進了郊區的發展[44]。Phillips將逆城市化研究集中在農村地區,即在人口流動中對于城市居民來說意味著什么,以及他們如何與他們的等級和身份聯系在一起的[45]。Mitchell認為逆城市化模式就是在大城市中克服傳統的工業城市化和集中的模式,并與后工業化的城市發展和農村城市化有關[2]。Feinerman等基于以色列農村的數據發現,逆城市化的結果導致了農村地區人口規模達到最優水平,并且增加了農村居民人均福利水平[3]。一些農村社會學家和地理學家關注逆城市化的經濟解釋。Moseley、Owen和Bosworth認為逆城市化能夠增加農民的收入,增加農村地區的就業機會,并且可以提供重要的地方公共服務[46-47]。
3.3 逆城市化的影響或結果
對于逆城市化問題研究結果多樣化,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逆城市化對于城市發展具有有利影響。逆城市化可以疏解核心區過密的人口,使人口分布趨于合理;同時核心區產業外遷,尤其是污染型工業的外遷等,可降低城市中心區的環境污染,同時騰出的土地可用于綠化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改善居民生活環境,有利于城市生態環境建設。另一方面,逆城市化不利于城市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逆城市化發展導致人口外流,城市市中心人口減少,降低市中心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其次,逆城市化導致城市管理混亂,大量人口戶籍在城市而居住在郊區,存在人戶分離現象,從一定意義上增加了對于人口的管理難度。同時,農村的規劃政策不能及時跟進,導致出現亂開發、亂開采現象,進一步破壞了農村的生態環境。Boyle等主要針對研究逆城市化地理選擇特征,及其與國際上的逆城市化經驗相關的社會空間系統的多樣性問題(包括對多種社會文化建設成果和對農村管理的不同態度)[48]。從對農村居民的角度看,Stockdale指出逆城市化不僅增加了大量的農村人口數量,也通過將城市要素流入農村的方式,如企業在農村辦廠,可以解決農村就業問題,增加就業機會,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49]。Hofmann、Steinicke證實了逆城市化進程正在進行中,不僅導致了橫向發展,而且也導致了縱向的擴建[50]。逆城市化的政策影響被廣泛探討,如規劃和住房政策[51-52]、關于社區權利的關系和農村發展的主要轉變問題等[53]。雖然逆城市化能夠實現經濟發展[54-55],但是其同時也存在著流離失所、社會排斥和住房無法承受的問題[56]。
4 總結與啟示
逆城市化問題已是當今城市的熱點問題,正確認識和理解逆城市化是城市能夠健康發展的必要前提。國外城市發展速度比國內快,其逆城市化發展階段也早于中國。國外學者對于逆城市化問題的研究和理解也較為深刻。通過梳理以上關于逆城市化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逆城市化并不一定會導致城市衰落,而是一種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城市擴張,更是一種城鄉關系的轉變過程,是城鄉一體化的實現方式,是鄉村振興的一種方式方法。當然,各個國家和城市的經濟社會基礎和背景不同,國外文獻可以為中國學者研究逆城市化問題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鑒,而不是一味對于國外相關觀點的認同,也不是認同逆城市化導致的城市衰敗。對于中國而言,國內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對逆城市化進行了研究,包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87—2000年,萌芽期。在這一階段,國內學者首先對國外有關逆城市化問題進行轉述,大多包括對國外文獻的介紹,對于國內大城市地區或是大城市進行逆城市化研究較少,并且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城市發展階段還未進入逆城市化時期。這一時期代表人物主要是張善余、周一星、閆小培等,研究的內容主要以城市化過程、城市化類型以及逆城市化概念探討等為主[57-59]。第二階段:2001—2009年,成長期。在這一時期,國內學者開始著重探討和分析逆城市化現象,并對中國城市是否進入逆城市化階段進行研究。這一時期以王旭、孫群郎、邱國盛、陳伯君為主要代表人物,其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逆城市化的現象、實質以及與郊區化的關系等[60-63]。第三階段:2010年至今,持續增長時期。在這一階段,逆城市化問題逐漸引起國內學者的普遍關注,包括研究區域經濟、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等各方面的專家學者。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致力于將城鎮化與逆城鎮化共同推進城市發展,未來關于逆城鎮化的文獻將會越來越多。在這一階段,文獻數量增長速度很快。在此階段國內學者的研究主題也發生了變化,學者開始關注國內城市發展中的逆城市化問題,尤其是大城市地區,并將其與農村發展、農民工遷移、城鄉關系、城鄉一體化、鄉村振興等相結合。一方面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提出逆城鎮化發展更利于理解現階段的城市發展方向;另一方面與國家戰略政策相吻合,對于促進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時期主要以沈東、張強、李培林、李鐵等為代表,其研究主題包括非轉農、城市空間布局、城鄉一體化、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等[64-67]。
逆城市化問題的研究依然是一個學術挑戰。它影響著農村發展、城市發展乃至區域的協調發展政策,對于未來農村發展規劃具有潛在的關系。然而,國內對于逆城市化的研究理論基礎還很薄弱。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一定的理論基礎背景,且對于逆城市化的內涵界定、概念理解模糊不清。大多數學者只是就逆城市化(逆城鎮化)而研究逆城市化(逆城鎮化),或是單一地運用地理學方法進行案例或經驗式分析。這從根本上無法厘清逆城市化的本質。當然,其中的原因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中國對于城市邊界的劃分、對于大城市地區城市中心、郊區等沒有科學的界定;學者對數據沒有進行詳細劃分,而數據是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68-69]。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學者的研究范圍。本文認為,逆城市化在一定意義上能夠促進鄉村振興,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有效措施。在繼續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應注意中國已經出現的城市擴散現象,因勢利導地發揮逆城市化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