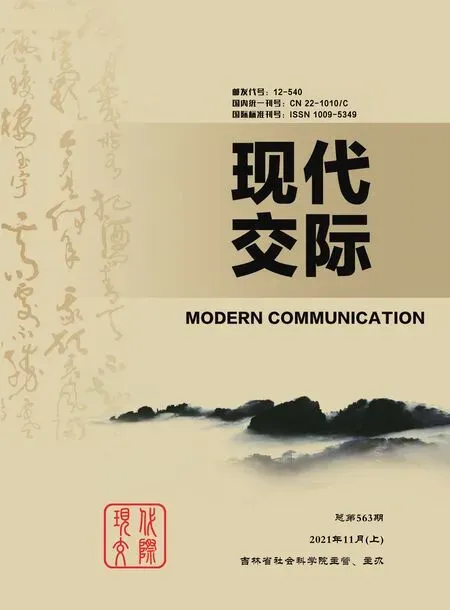網絡語“××腦”限制因素的多維度探討
羅 順
(喀什大學 新疆 喀什 844099)
從漢字字形產生、演變的過程及造詞法的發生、發展角度來看,人的身體部件一直是漢語文化中漢字字形和詞語單雙音節變化中的源部首和源語素。古代漢語常用身體部件詞有“面、口、齒、耳、目、指”六個。“腦”作為身體機能的重要器官,發揮著調控并支配整體生命活動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現代漢語中,隨著認識的深入,我們會發現“腦”作為身體部件的造詞并沒有出現大范圍的增長,而是固定在一定的意義之中,反而是一些隱喻意義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出現這種情況,一是由于過去對“腦”的認知停留在《說文解字》的概念闡釋中,而不是有科學依據的命名;二是由于隱喻作為我們生活的重要認知方式,其多角度的發展豐富、主導了我們的語言生活。因此,本文從隱喻的認知方式著手,探究以人們的認知方式、語言單位生成基礎的“××腦”的限制因素為主要內容,輔以語言的語用因素進行探討,深入地了解以身體部件為基礎的網絡語的發展限制。
一、認知隱喻的因素
認知隱喻作為人類思維的重要手段,在漢語中也很常見,漢語常常將“腦”隱喻為一個容器,即三維空間,可以容納東西,如“腦袋”[1]:
(1)例1:每次都不知道他腦袋里裝了些啥。
(2)例2:到了考試,就會發現腦袋里裝的東西太少了。
萊考夫(1987)發現,在人類認知的意象圖式中,“一個容器圖式,即一個具有界限的圖式,是有‘內’和‘外’之分的”。正因為漢語將“腦”概念化為一個容器,所以有“腦中”“腦子里”的表達,但是由于人們對于腦的發展更多地向容器內的偏向,也因此“腦”的內外差別在容器的空間隱喻中偏向于向容器內的表達。
(3)例3:我們要把知識牢記在腦中。
(4)例4:有些東西是一直存在在我的腦子里的。
也正因為“腦”被隱喻為一個容器,所以有“腦海”“腦容量”等表達,仿佛“腦”內的空間可寬可窄、可虛可實,還可以量化。
(5)例5:腦海里的那些記憶被一次次喚起。
(6)例6:海量的知識需要更多的腦容量。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漢語常常以三維空間為原始域,構建有關“腦”的非空間目標域,將三維空間映射到“腦”上,使“腦”成為某種可以量化、可摸、可視的三維實體。
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對于“腦”的隱喻認知具有一定的封閉性,這種封閉性體現在人們利用“腦”的表達大多存在于三維空間的表達中,且在三維空間中偏向于內向性的表達,缺少二維性空間及一維性空間的表達。這種封閉性使“腦”在理想化認知模型中的結構變為一個較為簡單的整體,構建的心理空間也較為簡單。
以萊考夫對“理想化認知模型”為視角,探討“腦”的空間隱喻結構化,和“腦袋”“腦子里”的表達類似,從隱喻的三維特征出發,“戀愛腦”“事業腦”這種“××腦”的使用,在空間隱喻中可以解釋為:將“腦”視為容納某一事物的容器,這里所容納的就是“戀愛”及“事業”這兩種抽象的事物。也就是說“××腦”的結構整體表達的是一個容器圖式的概念,所構建的心理空間也是容器的心理空間。
這種三維的空間隱喻也可以從方位上來理解,解釋為“腦子里面的東西全是戀愛/事業”,這種方位其實著重突出了其“腦”中心的位置上全是“戀愛/事業”。
二、生成詞庫的因素
隱喻的認知機制造成了不同的語言表達,但語言發展除了使用主體的認知影響之外,還有語言自身的發展規律。語義的生成銜接著結構主義到認知學派的過渡,語義的生成離不開作為語言基本單位的詞語。
在生成詞庫理論中,詞在動態組合的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動態性和彈性,會通過生成機制生成多個具體的意義解釋。這就要求我們在限制詞庫義項的數目時,學會捕捉詞在上下文中潛在的無限意義,在詞匯的表征和語義生成機制中對語義進行選擇。生成詞庫理論的詞匯表征最為復雜的是物性結構,物性結構包括構成角色、形式角色、功用角色及施成角色四個層面。在限制詞庫義項數目的時候,生成詞庫理論提出了語義生成機制,并基于論元的選擇分為類型選擇、類型調節及類型強迫三個組成部分。
物性結構與百科知識有著較為緊密的關系,Pustejovsky(2001)將名詞分為三類:自然類、人造類及合成類。自然類通常是與物性結構中的形式角色和構成角色有關的概念,比如石頭、猴子;人造類通常結合了物性結構中的功用角色或施成角色,如桌子、椅子;合成類名詞或稱“點對象”,由自然類和人造類組成,是一個復合概念。
根據以上解釋,我們不難發現“戀愛腦”“事業腦”在生成詞庫理論中屬于合成類名詞,與物性結構的各個角色有著緊密的關系。
在生成詞庫理論中,我們借用宋作艷(2010)[2]物性結構在認知語言學范疇化中的三種途徑來解釋新造流行詞語的“生成”基礎:
首先,從“戀愛腦”“事業腦”中“腦”這一源語素的單獨成詞的角度來看,在《現代漢語詞典》[3]中主要有以下幾個義項:
1)名詞,動物神經系統的主要部分,位于頭部。人腦管全身知覺、運動和思維、記憶等活動,由大腦、小腦和腦干等部分構成。
2)頭。
3)名詞,腦筋。
4)指從物體中提煉出的精華部分。
5)事物剩下的零碎部分。
從“腦”的義項解釋來看,基本義項“1)”中“動物神經系統的主要部分,位于頭部。人腦管全身知覺、運動和思維、記憶等活動”說明“腦”在身體中的位置及作用,屬于物性結構的功用角色;“大腦、小腦和腦干”說明其組成部分,屬于物性結構中的施成角色、構成角色。粗略地來看,義項“2)”和義項“5)”都是人們在認識上對“腦”的形式體現,屬于物性結構中的形式角色。基本義項“4)”中“從物體中提煉出”的屬于施成角色,而“精華部分”則屬于形式角色。
其次,從其定中復合名詞或短語中的修飾關系來看,新造流行詞語“戀愛腦”“事業腦”及原有詞語“劊子手”“段子手”,修飾成分描述了事物的功用、產生方式、典型特征等,和物性結構的四個層面在一定程度上不謀而合。
最后,從對名詞和名詞性成分進行分類的手段角度,即分類詞角度,不難看出“戀愛腦”“事業腦”是指以一類思維方式在個人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的特質總結,“劊子手”“段子手”是指以一類生存方式為謀生手段的人的特質的總結。
根據以上解釋,如果將“戀愛腦”“事業腦”這類新興流行名詞稱為復合類合成詞,“腦”在構詞上發揮著類后綴的功能。這種類后綴功能的發揮關聯著語義基礎與物性結構中的核心部分,即功用角色。因為人“腦”是“管全身知覺、運動和思維、記憶等活動”的重要調節系統,具有統領的功用,所以“戀愛至上的思維”和“事業至上的思維”才能以此為基礎進行。這里便體現了“××腦”的造詞理據及生成的基礎,由此,我們可以假設以下構詞:
(1)前+職業名詞:學生腦、教師腦、醫生腦、會計腦……
(2)前+動作動詞:學習腦、演奏腦、銷售腦、創作腦、表演腦……
基于前面我們將“××腦”的語義理解為“××思維模式”的情況,就整體性質而言,是名詞性的偏正復合詞。名詞性的偏正復合詞修飾成分有形容詞、動詞、數詞、方位詞等,這里由于數詞方位詞在性質和語義上無法和“腦”產生聯系;因此,我們將社會特征明顯的名詞和主觀意識強的動詞作為思維模式的修飾成分放入“××腦”結構中。可以形成:(1)類社會特征明顯的職業名詞+“腦”的情況,(2)類主觀意識強的動作動詞+“腦”的情況。單純就語言的形式和語義的組合來說,這兩個方面的假設是符合構詞的形式規律和人們的語義認知的。
三、其他語言因素的影響
1.現代漢語基本詞匯的影響
漢語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之一,有著較為完備的造字和用字系統,即便是順應世界發展的詞式書寫或使用,漢語內部的語音、詞匯、語法都具有自己的特點。
基于人的身體構造及對身體構造的最原始的認識,在古代漢語中,最基本的身體部件在《說文解字》中是“總十二屬”,顯然是對于“腦”缺乏足夠的認識。隨著理性認識的深入,腦的思維功能作為詞匯意義的重要部分開始進入復合造詞的行列。如果將在“戀愛腦”和“事業腦”之外的“××腦”構詞作為潛詞,其顯性的因素在現代漢語發展中可能受到社會文化語用和語言內部的自我調節能力的制約。
對于現階段的現代漢語基本的發展來講,數千年的歷史沉淀下來的詞語已然發展得較為完備,過去由于缺乏理性認識,對于“腦”的認識不夠充分,“腦”作為人體思維功能區的重要身體部件沒被發現,其思維功能大多被“心”代替,并以“心”作為基本詞匯沉淀下來。因此,現階段的“腦”只能用基本功能引申出來的“思維模式”意義進行復合構詞,而不是像基本詞匯那樣能夠得到充分的發展。
2.語言使用的現實制約
語言中最不穩固的使用就是詞匯的使用。通常情況下,漢語是在常用詞基礎上對新詞進行再造、以滿足社會發展需要的。語言的使用離不開語言的使用者,除開社會發展的需要,就是人們求新求異心理的需要了。在“腦”本身的使用過程中,“思維模式”的意義并不少見,最基本的就是“頭腦”一詞的使用,這樣的詞語穩定性強,沒有過多附加色彩,最能滿足社會發展的基本需求。
而“戀愛腦”“事業腦”在語言使用中通常具有貶義色彩,且兩個詞語一直活躍于各種偶像劇影評或者宣傳推廣中,其造詞意義的極端化傾向加重了使用過程中貶義色彩的程度。具體的“××腦”使用通常出現在具有諷刺意味的話語中,具有不穩定性,這便使它們的使用頻率受到了限制。同時,“戀愛”和“事業”本身就是現實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兩大話題,其涵蓋面比其下位概念中會用到的詞匯要廣,也因此在需要“思維模式”的言語交際和語言使用中,具有一定的難以替代性和概括性。
另外就是語言使用中可接受度的問題。新詞的產生和使用通常要經過社會交際的接受,可接受程度越高,使用越頻繁,反過來也會促進新詞的發展和使用上的成熟。將“××腦”代入職業名詞和動作動詞后作為類后綴進行類推具有潛詞發展的雛形,但是,如果要進入現實社會的言語交際,在現實發展中沒有出現思維的極端化現象明顯的情況下,前面按照語義生成可以構造出來的詞屬于一種潛詞,潛詞本身不具備較高的可接受度,也因此生成“××腦”的造詞會受到可接受度的現實制約。
還有較為實際的一點就是,從修辭角度來看,這里應該還有轉喻的現象,將這種有明顯貶義色彩的詞語以部分代整體,以人的性質特征代替一整類人。比如,形容一個人“他就是個戀愛腦”,我們可以進行反向思考,這句話中對于“他”的界定,實際上是將“他”歸為“戀愛腦”這一類人中,而“戀愛腦”就自然成為一類人的代名詞了。
總的來說,“戀愛腦”“事業腦”除具有不穩定性,貶義色彩明顯的特點之外,更重要的是具有難以替代性和概括性。同時,同類其他造詞的可接受度低也成為語用的現實制約,修辭手法作為語言藝術化的手段并不是所有交際活動必須使用的,這進一步加深了“××腦”在語用上的限制。
四、結語
根據分析我們發現,從認知的角度看,“××腦”是隱喻思維方式在思維中形成的容器圖式,解釋為“滿腦子都(裝的)是××”“××在腦子里(的中心位置)”;而從生成詞庫的角度看,“××腦”又可以根據功能的不同,析出“××至上的思維”的語義基礎。這就從人們的認知基礎和語言基礎兩個不同方面對“××腦”進行了解釋,但語言的發展離不開特定的規律,也因此有了語用方面的制約。
即使分析了“××腦”的多種限制因素,還是存在可以進一步考察的地方。比如于芳探索了英漢兩種語言中的“腦”的詞群,可以用其理論中的創新隱喻對“××腦”進行不同角度的考察,可以將“戀愛腦”“事業腦”理解為“沉迷于戀愛的思維模式”及“沉迷于事業的思維模式”,這雖然和生成詞庫理論中的語義生成機制所產生的表達較為相似;但這種創新隱喻的表達是在社會經驗中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或者社會行為的解釋,是一種“××腦”構詞前部特征的側重,和生成詞庫中對于“腦”意義的側重有所不同。而漢語對意合的重視,隱喻的認知方式,將社會現象和身體部件類名詞在概念上進行整合,會形成更多類似的表達,這種類似表達在復雜語言現象中該怎么進行解釋是我們需要持續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