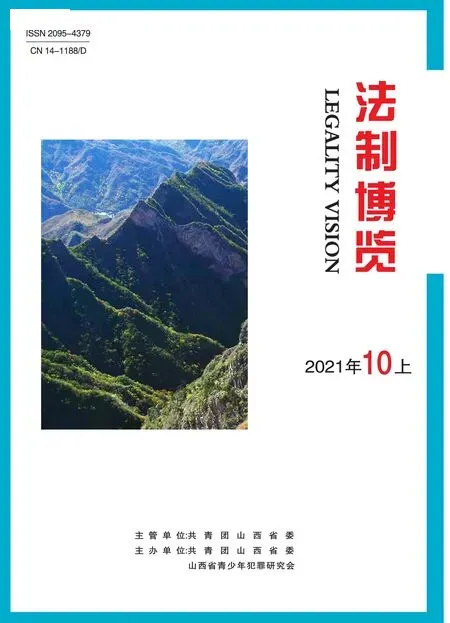著作權視野下視頻截圖的性質認定
曾 文
(四川輕化工大學,四川 宜賓 644005)
隨著攝影設備自動化程度加深,新的版權糾紛也逐漸增多。如利用相機自動拍攝、全息技術等制作的視頻截圖,因具有較高價值,出現被他人商業利用的問題。
一、視頻截圖的特質
視頻截圖是由計算機截取的顯示在屏幕上的可視圖像,來源是一段已完成的錄像制品。在攝影工具的日益智能化下,視頻截圖作品的價值和認定十分必要,不能脫離視頻截圖的特質。
創作空間的有限性。因截圖源于已完成的錄像,留給作者展示個性和智力創作的操作空間本身較小,因而法律應當著眼于如何對較窄創作空間內具備創造性的截圖作品進行保護。按照現有的獨創性標準,僅以技術手段上體現的選擇衡量智力創作,欠缺合理性。
獨立的經濟價值。就侵權訴訟案件看,截圖因具有可觀的商業價值,而侵權頻發。如媒體往往將電視劇截圖單獨宣傳報道,對此,參考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的一則判決,截圖體現出攝錄者對構圖、光線等創作要素的安排,達到獨創性即可。由此,不應基于截圖的產生背景、原始環境等否認其成為攝影作品。
二、視頻截圖作品性質認定的現行標準
攝影自動化下的視頻截圖是否構成攝影作品,大陸法系通常圍繞作品獨創性進行認定。
(一)國內現行認定標準
在截圖作品侵權糾紛中,對于涉案照片的獨創性,法官通常分配舉證責任,由原告對涉案截圖的拍攝過程進行證明,復述創作思考和判斷過程,判斷是否有智力創作介入,圍繞拍攝者對拍攝對象、燈光、布景、角度、器械等技術選擇和后期處理進行獨創性認定。
(二)國外主流認定標準
多數國家都以獨創性作為攝影作品的必備條件,但在側重上有所不同。巴西對作品要求“個人的智慧,想象的努力或藝術的產物”,重點落腳于創造性的努力。但依靠努力堆砌的作品并不一定具有保護的利益,如AlfredEisentaedt抓拍的《勝利之吻》,努力程度雖低,卻評為20世紀攝影作品之首。德國要求作品具有“個性”,即表達的獨特性。如其強調“人人均可為之”的東西不具有個性,正是立足于創作的維度,建立起著作權和鄰接權的二分制度保護[1]。英國法官Hugh Laddie則指出獨創性體現為通過拍攝的角度、光影、濾鏡獲得的以及后期制作的效果,但在實踐中,類案不同判情形也顯示出獨創性適用“短板”。
三、獨創性在視頻截圖作品中的理論之爭和實踐困境
獨創性內涵的不確定,導致在司法操作中極易成為司法人員的一種價值判斷。
(一)理論之爭
理論界雖對獨創性的“獨立創作”和“創造性”兩要素上達成一致,但對“創”的程度產生了分歧。一類主張“一定程度的創造性”,以李明徳為代表的版權體系。該較低標準下進一步細分,有學者強調“最低限度的創造性”[2],只需表述為新或原創;有的主張“稍許的創造性”,即表現作者的個性和情感[3]。筆者認為,任何人為因素投入的視頻截圖都包含創作者的個人色彩和感情,以此標準將視頻截圖都視為攝影作品,過于籠統。
另一類主張拔高獨創性,不贊同尤其是將獨創性較低的截圖認定為攝影作品,認為是向英美法系“額頭流汗”原則的靠攏,與我國著作權秉持的大陸法系傳統不為吻合,梁志文在《攝影作品的獨創性及其版權保護》一文中,就提出法院應當提高獨創性標準,卻忽略了該種理論會造成大多被侵權照片得不到保護的現實后果。
(二)實踐困境
“被動降低”視頻截圖認定標準。訴訟中,法院主要以技術性手段體現的創造性和后期處理作為獨創性標準。即以拍攝器材、角度、設置等技術手段是否體現個人智力判斷,但并未實現著作權保護初衷。而我國又只能將截圖歸入攝影作品,賦予版權保護,因此法院在認定截圖作品時常“降低”獨創性標準[4],少有不被認定為攝影作品的情形,不利于作品流通和公共福利增加。
獨創性標準“天然不足”。第一,以技術性手段具有的創造性作為獨創性是對其內涵的曲解。即便是普通照片,也體現拍攝者在構圖、角度、光線等方面的個性化判斷。同樣,以該標準難以支撐抓拍作品,因為“瞬間性”往往不具有創作意圖和對拍攝要素的選擇。第二,并非所有體現了人為干預的照片都能達到創造性,無異于排除了一部分極具價值的錄像截圖。何況創造性具有極強的主觀性和任意性,對于同一截圖,A法官和B法官看法不一,是當下司法糾紛的一個現狀。在Time Incorporated v.Bernard Geis Associates案件中,拍攝者偶然地拍到肯尼迪遇刺,侵權人截取了視頻進行商業利用,雖然拍攝者只是進行自動拍攝,法官依然肯定截圖的版權性。第三,攝影作品兼具藝術和法律屬性。獨創性之所以難以界定,在于感性的藝術和理性的法律在融合中出現了非自然匹配下的怪象[5]。
四、視頻截圖認定難題的破解
著作權是對作品價值的一種分配機制,目前攝影作品的商業價值與智力投入的不對等也說明了該制度的設計初衷未實現,筆者主張獨創性和唯一性并用。
(一)重構獨創性理論
各國對攝影作品呈現的獨創性表達效果基本達成了共識。以吳漢東為代表的作者權體系認為獨創性應通過作品反映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或是智力創作[6]。結合著作權作品保護的動力——商業價值來看,獨創性包括兩方面:一、獨立構思完成作品;二、表達效果具有創造性。對于視頻截圖,可以通過拍攝技術手法和圖像后期處理實現的表達效果判斷,該表達必須蘊含作者的創意或情感,反映拍攝者的智力投入[7]。在個案中,不僅要考量人為因素的參與,更重要的是作品表達,法官在對截圖進行判斷時,可以根據普通受眾的一般知識和一般能力來判斷作為表達效果判斷的基準線[8],普通受眾的引入既是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也是對公眾審美尊重的表現。
(二)附加唯一性理論
參照英國樞密院案件Interlego V.Tyeo的權威標準:必須足夠使照片作品在整體上具備一定的有形變化或潤色等元素,才能獲得版權保護。Samson Vermont教授進一步提出唯一性理論,指出具備新穎性和不可重復性的攝影作品享有著作權保護[9]。
確定作品唯一性需要衡量兩個變量。變量一:附加元素新穎性。將涉案截圖作品拆解為各元素,在排除已有元素基礎上,審查附加元素是否有明顯的新穎性。若作品表達創造性不明顯時,可將作品主題或創作意圖作為創新因素。該方法與Gideon Parchomovsky和Alex Stein教授提出的“增加價值原則”相似,在《論獨創性》中教授認為侵權作品與原作品比較,若法院認為被告作品在獨創性貢獻上等于或大于原告,則不構成侵權[10]。變量二:可行替代作品數量。即“人人可以為之”的可能性,當他人難以用相同或更高質量完成爭議照片時,替代作品越少,被審查為唯一性的可能性越大。如醫生在手術錄像中截取的臨床應用醫用膜照片等,盡管在創造性上有所欠缺,但因數量上的匱乏而享有極大價值。再如抓拍作品,其可替代作品數為零,具有重大社會價值,當然具備唯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