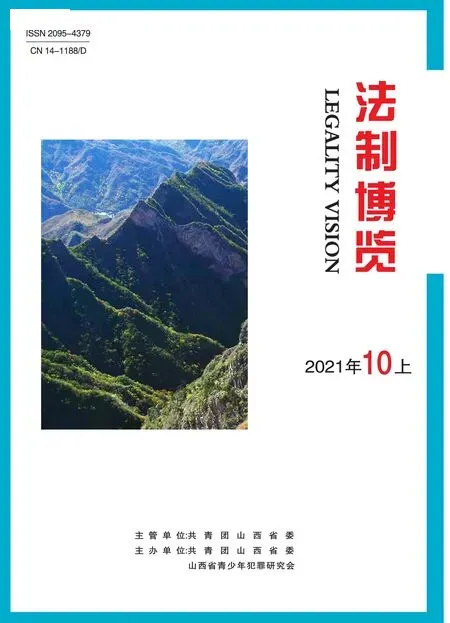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發展與探索
李婷婷
(廣東省深圳市法律援助處,廣東 深圳 518000)
自司法部1994年開展法律援助試點工作,我國的法律援助經歷了27年的發展[1]。期間,從1999年《關于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到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的國務院令《法律援助條例》,雖然有立法與相關制度的支撐,但法律援助的整體發展并不理想。
一、我國法律援助的現狀
(一)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自1994年試點以來一直在進行著自我探索和發展[2]。建立了從部級到省級、地市級、縣區級四級法律援助機構,但存在的問題是結構層次設置不合理,[3]職責分工不明確。1.從橫向看,各省援助機構都是獨立的個體,沒有統一的業務系統,沒有一致的行業標準,人員流動性大,全國法援是一盤散沙。2.從縱向看,整個組織結構依附于司法機關存在,人事和經費管理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四級法律援助機構從上到下只有業務指導關系,各層之間斷層,嚴重阻礙了法律援助事業的獨立與發展。
(二)依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包括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務院《法律援助條例》;各省市制定的條例如《廣東省法律援助條例》《上海市法律援助條例》《浙江省法律援助條例》;市級的如《廣州市法律援助實施辦法》《深圳市法律援助條例》;加上在申訴、刑事案件法律幫助、刑事案件全覆蓋等方面的規范性文件,組成了法律援助法律法規系統。從整體來看,立法的層次較低,且立法的對象與范圍雜亂無章,阻礙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康有序發展。
(三)從經費來看,主要來源都在政府財政,只有不到2%的經費來源于福利彩票、社會及行業捐助。政府經費作為單一來源,經費使用要受到限制,最大的問題就是經費的有限性及使用的機械性。很多地方引入了基金會來對政府經費進行補充和增益,江蘇、浙江、上海就是典型代表。上海的法律援助機構在經費使用上有相對獨立性,可以對個案支付特殊補貼;浙江法律援助基金會,過去5年里對疑難及其他案件的補貼達到了案均5000元,超過正常補貼標準的一倍以上。這些補貼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當地律師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積極性,使法律援助案件的辦理的質量也有了較大的提升。
(四)從標準來看,各地法律援助的地方性差異明顯。三十多個省區市法律援助機構因立法的缺失或實際工作的需要,制定了不同的條例或實施辦法。例如:廣州市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上,對所有的刑事案件免于審查經濟條件,浙江省則認為所有的在押人員都可以認定沒有收入,深圳市對所有沒有辯護律師的被告人指定法律援助律師辯護;在民事援助案件上,各省的標準也各不相同,廣州市以收入低于本市企業職工現行月最低工資標準可以認定經濟困難,上海是以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為標準,深圳是以上一年度職工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衡量標準。但這些條例和實施辦法都沒有超出現有的立法范圍,僅在對象和范圍方面作出了不同的規定,在組織機構、人員編制、經費使用、法律責任等部分并沒有作出實質性、突破性的規定。
二、國外法律援助的借鑒
現代的大多數西方國家認為法律援助是一種政府的財政責任,他們在長期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確立了穩定的經費保障,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機構,規范了法律援助的實施,為貧弱者提供進入司法平等保護的機會。[4]
從英國、美國、荷蘭、芬蘭等國家的法律援助制度中可以看到兩個基本的事實,一是公設律師制度是最有效率的法律援助模式;二是法律援助經費除政府資金外還是要采用費用分擔等制度來保障穩定的經費來源。[5]
三、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嘗試
(一)公設律師制度。這種制度主要參考美國的公設律師制度。在以市場化標準支付律師費用的環境里,公設律師制度以花費少、效率高一騎絕塵,遙遙領先于其他經費使用制度。但在中國,因為機構、人員的性質未定,且法律援助購買服務經費遠低于國外,這項制度的主要優越性并不能體現,但從深圳早期的公設律師項目來看,完成質量比社會律師要高。
(二)輔助性法律援助制度是深圳2008年市級人大立法確立的制度。規定的是對收入高于經濟困難標準低于普遍標準的確有困難群眾的特殊援助計劃。在規定事項范圍內,如果申請人家庭經濟狀況滿足條件,爭議標的高于其3萬元,且申請事項為七種事項之一,就可以繳納600元的受理費用與機構簽訂協議并獲得援助,事后支付機構所得收益的8%。從制度上看,這是一項非常優越的突破,但事實上,從立法至今,受理的輔助性法律援助只有一宗。這與我們的國情、社會誠信制度有相當的關系。當你只需開具經濟困難的一紙證明就可以免除所有費用的時候,又有誰還愿意另行支付其他費用來獲得法律援助呢?而沒有建立一個完善的追繳制度和懲罰機制,申請人就算申請了輔助性法律援助計劃,但不遵守協議支付受益款項也不會得到相應的懲罰,這種情況下輔助性法律援助根本無法繼續進行。
(三)送費評定制度,主要參考我國香港的送費評定制度。我國法律援助機構對所有正常辦結的法律援助案件按統一標準進行結算,這就導致了法律援助案件質量良莠不齊。為解決這個問題,2019年司法部出臺了法律援助案件辦理相關規定,但要從根本上解決案件辦理的質量問題,還是要和經費掛鉤。
我國香港的送費評定是指法律援助指定律師在辦理法律援助案件后將整個案件的辦理工作所產生的流程時間及相關費用的材料提交給我國香港法律援助署進行審核,我國香港法律援助署根據案件辦理的情況綜合評定費用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的優點是可以進行個案評定,對律師的工作能夠有一個全面的評價,但缺點是需要的人力物力較高,不適合案件量較大經費較少的地區。我國目前采用類似制度的是江蘇、浙江等省。從2013年,江蘇、浙江兩省就開始嘗試了類似送費評定的分級補貼制度,由基金會對辦理優秀的案件及重大疑難案件給予資助。
(四)基金會制度。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是全國性公募基金會,根據不同地區和人群的需要,設立了14個專項基金來資助各類法律援助案件。作為對國家財政的補充,全國性的基金組織,主要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統籌安排,例如“1+1”志愿者行動、援藏律師服務團,是將律師資源調整到中西部、藏區貧困縣;還有用在宣傳方面的“高銘暄優秀法律援助案例獎”和專項宣傳基金項目,用于補充財政不足的法律援助宣傳活動。
各地區的基金會援助對象更加日常化,其他各省市的地區法律援助基金會的主要支持對象就是法律援助案件。
從公設律師制度、送費評定制度,到基金會制度、輔助性法律援助制度,我們看到的這些都是在經費上的制度創新與突破,但是在系統和體制上沒有突破;在對象范圍上也沒有創新性的突破。輔助性法律援助制度提出對申請人的申請進行審查,在符合條件的基礎上設置了有勝訴和執行可能的限制性條款,但對于勝訴和可執行案件的認定及因此不予受理的案件申訴等沒有配套規定,因此不具備實際操作性。但這是第一次在國內的援助條例出現的對范圍對象進行的非經濟原因的限定。
從現狀來看,國內法律援助面臨的主要問題一是經費來源單一,沒有可持續性收入來源;二是沒有可供具體執行的立法;三是沒有獨立的機構和獨立的財權;四是對法律援助的對象和范圍沒有進行限制。對于問題一,現在國內進行的基金會制度和其他捐款制度可以作為法律援助經費的補充,但要形成持續穩定的收入來源還是要考慮訴訟費用分擔的機制,由受援人從每個月的可支配收入中按一定比例向機構支付律師費來維持運作。對于問題二,現在進行的《法律援助法》立法能解決一些問題,但關鍵還是要進行制度創新,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來參考國外做法進行調整改革。關于問題三,建立獨立的系統體系要靠實踐來進行探索,但最終要落腳在立法上。問題四,根據國外法律援助機構的做法,對法律援助案件的評估還有一項是否必要性的評估,如果某項事務對于申請人無關緊要,則不會向其提供法律援助。
我國已經進入了法律援助理論探索百花齊放的時代,所有的理論與探索都要靠實踐來檢驗可行性,未來將還有更多的探索能夠指引我國法律援助健康有序地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