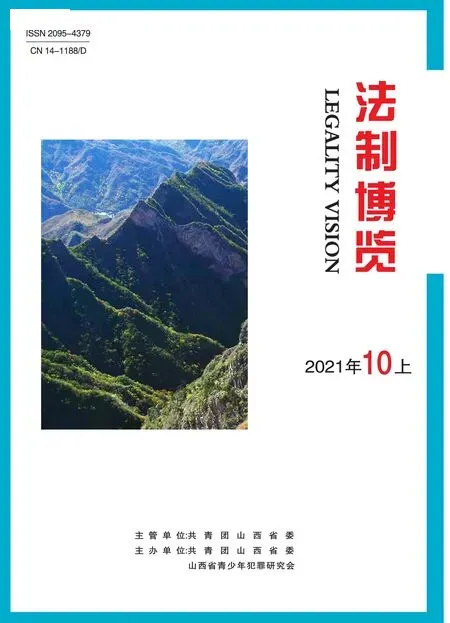心理矯治方法在監管工作中的實際應用性探討
邢 娜 金 榮 徐娜娜 周 瑞
(黑龍江司法警官職業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60)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構建國家安全體系。作為保障社會安全的重要環節,全國司法系統一直在探索著如何能最大程度上完成國家、黨和人民賦予的重任。2018年司法部傅政華部長在全國監獄工作會議上提出,“以政治改造為統領,統籌推進監管改造、教育改造、文化改造、勞動改造”五大改造新格局,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堅守安全底線,完善安全治理體系。從堅持底線安全觀到治本安全觀這一理念的轉變,是堅守監獄工作安全底線,踐行改造宗旨,真正實現“治本”以保障社會安全的科學治理體系形成的標志,同時也是治理能力提升的體現。努力打造監獄改造模式“升級版”,是司法工作對既往工作經驗的總結,同時也驗證了我國司法工作的進步。那么要如何真正實現“五大改造”理念、“治本”理念、“安全觀”理念?
隨著社會的變革,罪犯群體構成、社會環境因素等也都在發生著改變,罪犯的獄內外再犯罪、罪犯的非正常死亡已成為司法領域及社會領域重點關注的焦點。一個人之所以成為罪犯,總是有著原因。從心理學角度去分析,犯罪行為的出現是受犯罪心理支配和控制的。犯罪心理形成以后,不會無緣無故地消失。并且,當罪犯進入監獄服刑以后又會形成“監獄人格”。這雙重區別于常人的心理活動必然會影響到他們的服刑表現,或者說,直接影響到監獄是否能夠真正實現改造他們這一目標[1]。也許,在監獄的強制性管理中,他們的行為是符合要求的,但是他們的犯罪心理真的就實現了良性轉化了嗎?一直以來,“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都是監獄工作的最終目標,但是如何真正地實現這一目標,卻不是單靠理想和工作信念就可以實現的,這其中就要追根溯源去找尋一個人到底是為什么會實施犯罪行為,在什么樣的情境下會實施犯罪行為。心理是行為出現的根源,而某一種心理的形成由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而心理矯治工作正是解決這一“難癥”的最佳治療手段。心理矯治工作機制則是由專業人員用心理科學方法和手段,制造外在的正向環境與干擾因子,通過對罪犯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評估、心理咨詢與治療、心理危機干預等多層次、多角度、多形式的一系列專業性活動,深入改變罪犯原有的消極認知、氣質、性格、情緒、意志等內在心理結構,做到從治標延伸到治本,幫助他們消除犯罪心理及其他心理問題,維護心理健康,重塑健全人格,提高適應社會的能力,實現治本觀與安全觀。
一、對罪犯群體開展針對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加強罪犯心理健康意識,提高罪犯心理健康水平,保障監管安全
(一)以講座的形式進行心理健康教育
講座一般以專題形式進行,進行有針對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比如說什么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的標準是什么、如何進行心理健康的自我評估、人際關系的處理能力對其行為的影響等等。通過這樣的專題講座可以直接讓罪犯了解心理健康與自身的關系,從而引起罪犯對心理健康的興趣與關注度,更重要的是讓罪犯明白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從內心接受心理矯治工作,減少排斥與抗拒,由抗拒到被動接受再轉變為積極主動求助。
(二)全方位開展宣傳活動,以潛移默化的形式影響罪犯對心理健康教育的接受程度
監獄內的宣傳活動大多是以監獄報、墻報、黑板報、廣播、監獄系統內部創辦的雜志開展的,在這些媒介中向罪犯傳播有關心理健康教育的相關內容,對罪犯群體可以說是展開全方位的“包圍”,讓罪犯耳濡目染,在日常改造過程中,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讓罪犯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對心理健康教育有所認知。
(三)組織罪犯進行課堂學習,以生動形象的傳授與講解方式,讓罪犯了解心理健康知識
課堂學習是一種系統化、“半強制化”的教育模式,監獄可以在罪犯的“三課”教育中安排一定的學時,制定符合罪犯接受能力的教學計劃,使用便于罪犯理解的教材,對罪犯進行心理健康教育,并進行考核。這種學習模式可以讓罪犯被動地去了解有關知識,彌補因一些罪犯欠缺主動性學習態度的不足。
(四)組織罪犯之間進行小組學習,并結合自身開展討論
作為同類群體,罪犯之間的學習與探討,會起到與監獄專業從事心理矯治工作的干警或是社會上聘請的專業人員進行由上到下的講解不同的效果。首先,作為同類群體,罪犯在某些問題上會更容易產生共鳴,激發他們對自身問題的反思,也會讓他們在彼此之間提供一個參考;其次,作為同類群體會讓他們減少一種排斥與抗拒感,他們處于同種環境之下,同伴所提出來的看法會讓他們更容易接受,而不是那種“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抵觸感;最后,罪犯們日常改造都是生活在一起,他們彼此之間更加互相了解,可以互相指出對方的日常行為表現有什么不合乎常理的地方,有利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五)為罪犯提供個別心理健康咨詢
由于罪犯的性格和接受能力的原因,這種公開的形式或群體的形式,并不能讓全部罪犯理解或接受心理健康教育,也羞于在其他罪犯面前詢問或討論與自身心理健康狀況相關的問題,考慮到這一點,可以在監獄內為罪犯提供個別咨詢途徑,向前來咨詢的罪犯進行專門的講解和探討,盡量做到心理健康的教育活動能夠深入到每名服刑改造的罪犯。
二、對罪犯進行心理評估,建立罪犯心理檔案,為監管工作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一)對罪犯進行心理評估
對罪犯的心理評估并不是“一刀切”的工作模式,而是根據罪犯在不同的矯治階段的不同監管需要,進行有所側重的評估,比如說,對于初入監的罪犯要進行個性特征、心理健康狀況的評估;在罪犯服刑中期,矯治工作者出于心理咨詢和治療、心理預測、危機干預、監管風險防范的需要進行心理評估;對即將出獄的罪犯,為了檢驗矯治質量和預測未來適應社會狀況、再犯罪而進行心理評估。[2]
對罪犯的心理評估最后以心理評估報告的形式出現。在心理評估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有關罪犯心理問題的產生原因、鑒別診斷、影響罪犯心理健康的主客觀因素、被評估罪犯的不尋常的行為表現、罪犯的危險性傾向性及危險程度等信息,最后心理評估報告中會對所得到的資料進行綜合分析,針對報告中反映出不同心理問題的罪犯從心理科學的角度,結合有關的法律和改造過程中的具體監管措施提出相應的保護和防范建議,供監獄民警在開展監管、教育改造工作時進行參考,從而減少監管教育改造工作中的盲點和漏點。
(二)建立罪犯心理檔案
罪犯心理檔案是監獄通過多種心理評估方法積累起來的有關罪犯基本信息、成長經歷、犯罪經歷、人格特點、心理障礙與疾病、行為習慣等內容的記載,以及針對罪犯心理問題制定的矯治方案及實施矯治效果的記載。[3]一份在罪犯改造過程中不斷被完善充實的動態變化的心理檔案在罪犯監管改造工作中提供的幫助是不容忽略的,它不但可以為監管干警適時提供制定針對性監管策略的參考,也可以為監管改造工作的成效提供比對依據,同時也通過對罪犯危險性的預測可以使監管安全防范工作做到提前性和有的放矢。對罪犯出獄或假釋后的行為方向的預測提供科學依據。監管改造工作是一項治標治本的工作,而心理檔案則正是提供“標”與“本”的治療的記錄,讓“治療方案”的制定更加有針對性,提高監管改造工作的質量和效率。
三、對罪犯進行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解決罪犯的心理問題和治療罪犯心理疾病
(一)對罪犯進行心理咨詢,解決罪犯心理問題,消除影響罪犯改造積極性的不利主觀因素
導致監獄服刑罪犯的心理問題產生的現實刺激事件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來自服刑體驗。比如說對監獄生活不適應,與他犯之間的人際關系、與干警之間監管關系,改造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等。二是來自監獄外因素。比如受到來自家庭關系、婚姻問題、戀愛問題、子女撫養、財產分割與繼承等問題而產生心理問題或情緒障礙。[4]受個人的人格特質所影響,不同的罪犯對同一事件的刺激程度的反應也是不同,因此這些因素會引發罪犯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如抑郁、焦慮等,甚至會導致罪犯實施一些危害監管安全的行為,如自殺、自殘、行兇、脫逃等。監獄中負責心理咨詢的干警通過開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咨詢工作改變罪犯的偏差或錯誤認知,可以有效地幫助罪犯重新評價刺激事件,降低不良情緒影響,改變罪犯應對方式,提高罪犯的適應性。
(二)對罪犯進行心理治療,解決由于心理疾病給罪犯自身和監管改造工作帶來的安全隱患
罪犯心理治療的適用范圍主要是罪犯的適應問題、各種神經癥、人格障礙、性心理障礙、嚴重情緒與行為問題、嚴重心理障礙、各種心身疾病,或康復中心的精神病人等。在長期的監管改造實踐工作中,這幾類的罪犯本身深受自身問題的折磨與困擾,同時也對監管安全造成了極大影響,具體以消極改造、自殘、自殺、傷人、毀物、同性戀等行為方式表現出來。對這些罪犯進行心理治療是保證監管改造工作正常進行的必要手段和途徑。
四、對罪犯進行心理預測與心理危機干預,防患于未然,降低突發事件發生概率
(一)對罪犯進行心理預測,從而實現對罪犯行為傾向性預測,做到防患于未然
對罪犯的心理預測一般針對在監管實踐中容易導致監管安全事故發生的罪犯的自殺傾向、脫逃傾向、暴力危險性和再犯罪可能性幾方面。在監管實踐中,監獄干警根據罪犯入監時的心理測評結果、犯罪事實、基本信息等,對罪犯的人格特質和行為傾向性進行初步評估和預測。在罪犯服刑過程中,監獄干警結合罪犯改造表現和日常行為表現的掌握情況,初步鎖定危險分子,通過運用心理科學方法與手段,可以進一步較為準確的、適時的對罪犯人格特質進行評估,從而預測出罪犯在一定的外界事件刺激下其心理發展變化趨勢,從而確定其實施某種行為的傾向性和可能性,并評估出危險傾向與危險等級,據此采取相應的監管手段,避免危害監管安全行為的發生。
(二)對罪犯進行心理危機干預,降低突發事件發生概率
監獄惡性案件的發生很多是由于罪犯心理危機未能被及時發現和采取預防措施引發的。罪犯在監獄服刑期間,由于受主、客觀多重因素的影響會出現因超過其心理承受能力和調節能力而導致的心理異常或病態表現,并因此可能會實施危害自身或他人的行為,通常表現為自殺、自傷、自殘、精神病、神經癥、人格變態、生理病變、變態攻擊等。這些行為出現的主觀因素主要是罪犯自身的性格極端性、情緒不穩定性、正向意志薄弱、強烈的反社會心理、自我認知水平低、缺乏自我控制和調節能力等。當罪犯心理處于嚴重失衡狀態時所積累的消極情緒和能量達到一個臨界點時,其就成為需要緊急心理救助的對象。通過心理危機干預,讓罪犯內心積累的消極情緒和能量用一種合理、合法的途徑釋放出來,以防止其如“火山”爆發一樣對外界或自身造成嚴重的危害后果,也就是避免突發事件的發生,確保監管安全。
五、運用團體心理輔導,為罪犯提供心理幫助與成長指導的重要作用
通過團體心理輔導,一方面咨詢師可以通過觀察個體在團體內與他人的交互作用,以及個體在團隊內的行為方式對個體的人格特質和行為選擇進行現實性觀察與評估;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針對性的引導促使個體在團體活動中進行觀察和學習、情緒情感體驗、認識與探討自我、接納自我與他人、調整與改善與他人關系、學習新的互動模式與行為模式、感受助人與被助的積極情感體驗,從而幫助罪犯發展出良好團體適應能力,學會如何在團體中自處并體現自我價值。
綜上所述,心理矯治工作的開展首先是可以幫助我們防范罪犯監管風險,實現監獄工作最基本的安全底線觀,然后在這一基礎上通過矯治罪犯心理結構中消極因素,保障罪犯的監管改造工作的順利開展,更好地實現將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的目標,爭取保證罪犯順利回歸社會后,能夠成為有利于社會發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