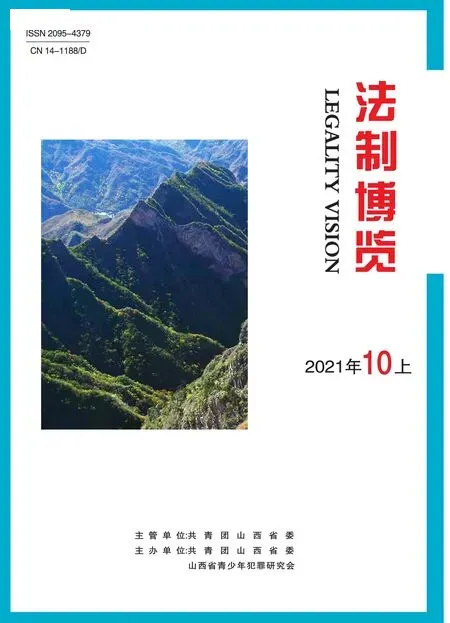深石原則中國化的適用問題研究
范澤坤
(青島科技大學,山東 青島 266000)
一、深石原則的由來
(一)深石原則的由來與內涵
“深石原則”又稱衡平居次原則,是根據控制股東是否有不公平行為,而決定其債權是否應劣于其他債權人或者優先股東受償的原則。其理念來源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泰勒訴標準石油電力公司案(深石案),1978年正式將該原則規定在了《美國破產法》第五百一十條,深石原則從此有法可依。[1]
經過實踐與發展,在適用深石原則時需要注意以下事項。第一,對于適用深石原則的具體情形進行了發展與擴張,不再局限于母子公司的關聯關系。第二,適用深石原則必須發生了更為惡劣的不公平行為,要求行為人有一定的主觀惡性。第三,該原則已發展為一項債權人的救濟原則,因此首要前提是要有損害的發生,否則不能保證衡平居次的實現。
(二)美國法院中深石原則的適用標準
在美國案例中,想要適用深石原則,一般要符合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債權人存在不公平的行為①“不公平的行為”根據美國判例法,表現為欺詐、違反信義義務、違法、資本不足以及濫用控制權,為自身利益將從屬公司作為工具使用。;第二,行為對從屬公司產生了損害;第三,適用深石原則不會與其他法條相抵觸。
二、就我國相關司法案例的評析
(一)沙港公司訴開天公司案的評析
在沙港公司與開天公司的執行異議案中,法院在判決中首次借鑒了深石原則,否定了對于出資不實股東進行同等順位受償的主張。在維護公司外部債權人利益的前提下,又兼顧了公司內部股東的利益。同時本案對于法人格否認制度有一個很好的區分,具有借鑒意義。本案中控股股東開天公司對子公司并沒有財產、業務和組織機構的混同,法人獨立地位并未喪失。在僅存在出資不實的情形下,沒有采取法人格否認制度進行裁判是合理的。但其實根據本文上述分析,在本案中引用衡平居次原則的條件是不充分的,因為衡平居次原則本身要求控股股東實施了更為惡劣的不公平行為。
(二)適用深石原則的合理性
對于沙港案適用衡平居次原則的合理性,一方面體現在既符合我國民商法誠實信用原則及公平公正理念,也是針對控股股東權利濫用的一種救濟手段。另一方面與自動居次②自動居次要求控制股東的債權居次受償。相比,衡平居次理論更符合誠實信用的理念,效果也更理想。當從屬公司進行破產清算時,一概而論地剝奪或居后清償控制公司或控制股東的債權并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而應該根據具體情況來具體分析個案的處理辦法,以達到最好的平衡效果。
三、深石原則中國化的立法困境
本文參考Blumberg教授所總結的四種案件類型:1.資本不足;2.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過度控制;3.濫用法人獨立地位;4.財產混同或不當輸送。
(一)子公司資本不足
與以往資本實繳制不同,目前我國實行的是資本認繳制,沒有最低金額限制,這種做法不可否認地刺激了資本,鼓勵了經濟的發展,但資本不足的隱患也隨之而來。在沒有了最低金額限制之后,發起人就可以以很低的金額注冊公司,之后再以向公司借貸的方式作為對公司的投資,這樣當公司破產后,發起人只需要對一開始注冊資本的金額負責,但是其擁有的公司債權卻能夠與外部債權人同等受償,為心懷不軌之人提供了可乘之機。另一種不合理的債權是發起人在資本注冊時金額過高,在吸引投資者前來投資之后并不如實繳納,資本不足的風險由此產生。在公司運轉中向公司出借資金,就可與第三人的債權同等受償。
這樣一來,股東認繳的資本沒有如實繳納并不能及時得到法律的救濟,資本的空缺就在所難免,但其卻可以與其他債權人同等受償又沒有辦法追究其法律責任,也使債權居次原則的實施缺乏正當性。這也正是沙崗公司訴開天公司案的一大突破,但又有缺乏正當性之處。只有當子公司的破產是由于該股東的繳付義務沒有履行而導致的,從而危及到了債權人的利益時,債權居次才可以獲得正當性,否則將難以適用。[2]
(二)控制公司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操控子公司
我國《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了信義義務,但該義務范圍僅包括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并沒有將股東納入其中。這就不可避免地發生過度控制,尤其在具有關聯關系的企業中,控制公司的股東利用控股權利,操控子公司的經營運轉,以謀求自身利益,也就使得深石原則的移植缺乏法律基礎。
(三)控制公司無視從屬公司的獨立人格
這種類型的案件極易與法人格否認制度的構成要件發生混同。法人格否認制度要求“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而當“控制公司無視子公司的獨立人格而違反法律規定”作為深石原則的適用情形時,[3]這兩種制度都具備公司股東濫用法人獨立地位,極易發生重疊,也就有必要對此兩種制度進行辨析。
(四)財產混同
這種類型的行為和無視法人獨立人格具有相似性,也即極易與法人格否認制度產生混同。只有將法人格否認制度規定得更精確,能夠清晰地區分二者時才能保證深石原則在司法中得到適用。
四、深石原則本土化的建議
通過上述沙港公司訴開天公司案、深石案以及深石原則在美國的適用標準分析,引入深石原則是具有可行性與合理性的。
(一)主體要件
由于深石原則的作用在于通過債權居次來保護外部債權人的利益,因此其權利主體應當是因不公平行為而導致被控制的公司的外部債權人。有學者認為破產公司的其他股東也可以成為該原則的適用主體,但這類主體也持有公司股份,與該原則的出發點并不相同,因此這類股東還是無法得到有效保護。[4]
(二)行為要件
適用該原則的行為要件主要在于界定不公正行為有哪些情形,參考Blumberg教授的觀點,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點:1.從屬公司資本不足。針對這情形,如何在放寬設立公司條件的情形下還能夠保證不會產生出資不實是首要解決的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可以從股東認繳資本后實際支付設定期限方面解決。2.違反誠信義務,濫用股東權利。我國《公司法》未將控股股東納入信義義務的范圍,而股東必將影響董事的選舉。因此如何平衡股東的權利與義務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3.濫用法人獨立地位與財產混同。這兩種情形都要求與法人格否認制度做好區分。當公司法人格被濫用時,要判定這是一種一直持續的狀態還是短暫地出現了這種狀況。如果一直持續則需要運用法人格否認制度來進行判定,如果只是某段時間出現了這種狀況則作為法人格否認制度的補充,通過衡平居次原則來保障外部債權人的利益。
最后由于法系的不同與語言環境等眾多原因的差異,欺詐的含義在不同的語境中也不盡相同。在美國法律中“欺詐”的意思是“具有妨礙、延誤、欺騙其他債權人意圖的設定債權行為或者在特定情況下沒有獲得公平對價的設定債權行為”。而在我國《民法典》中,欺詐是以使人發生錯誤認識為目的的故意行為,不能一概而論。
(三)結果要件
懲罰說與補償說是兩種關于衡平居次原則的不同觀點,本文比較傾向于后一種。一方面從屬集團、關聯公司等存在關聯關系的公司廣泛存在,利益輸送、信息共享已成為常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為了鼓勵經濟發展的多樣化,允許此類經營模式的存在,不能因為個別債權的受損就進行取締。[5]因此,深石原則的存在是為了平衡債權人利益,有效救濟外部債權;另一方面,部分做出不當行為的股東并不能代表全體,若采用懲罰說,對并未作出不公正行為的股東極不公平,有失偏頗。因此,采用補償說比懲罰說更為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