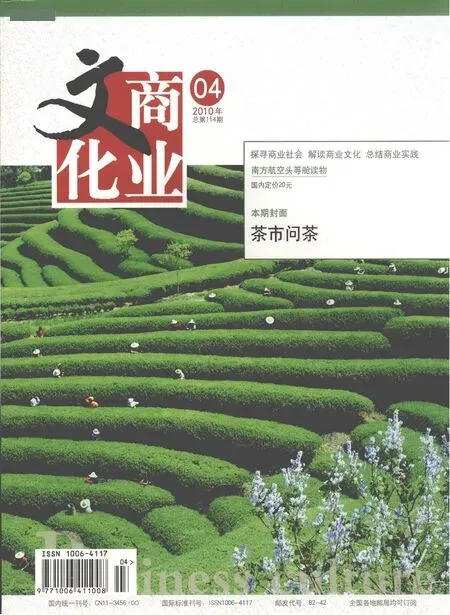如何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
王可鑫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貿易對于每個國家而言都意義重大。我國對外貿易具有一定的優勢,例如商品需求大、貿易市場廣闊、勞動成本低廉以及對外貿易依存度增加等等。為了讓我國對外貿易的優勢穩中有升,需要我們進一步從政府、企業兩個方面尋找可行的處理對策。文章針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以期為對外貿易相關工作的開展提供一些參考。
現如今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越發明顯,同時各國之間不斷開展的國際貿易也讓經濟全球化的水平不斷提高,所以我國也在積極參與到國際貿易競爭當中,為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我國也體現出了特有的對外貿易交流優勢。因而在新的時代,對自身外貿優勢進行分析,并結合我國現有的優勢,探討可行的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對策意義重大,需要予以重視。
我國對外貿易優勢
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我國對外貿易的進出口總額在逐年提高,正確認識我國在對外貿易中存在的優勢,可以充分地調動各種資源,提高我國在對外貿易中的競爭力。
市場廣闊、商品需求旺盛
我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現在人口總數達到14億以上,占世界總人口比例約18%,所以理應在國際貿易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國廣闊的國土保證了廣闊的市場和廣泛的材料供應,同時這樣的人口體量也保證了商品需求總量。一個人的一生都離不開消費,因而我國貿易發展不僅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中之重,更是國際貿易體系的關鍵環節,甚至可以說,如果將我國從國際貿易體系中剝離開來,世界就失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貿易市場,減少了大量消費源。所以很多投資者對我國廣闊的貿易市場持積極看法,和我國建立不同類型、多個層次的貿易聯系。
勞動力資源豐富
我國人口眾多,這也給經濟的建設和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這個優勢也是其他任何國家無法企及的。根據英國波士頓咨詢公司所發布的《把握全球優勢》的分析結果來看,以中國等為代表的高密度人口國家,將會在較長時間內保持低成本,進而在國際貿易中繼續保持優勢。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低成本”指代低勞動力成本,勞動力成本的降低對于壓縮產品價格而言十分有利,進而搶占市場份額。所以不難看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然是我國重要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發揮作用。
外貿依存度較高
外貿依存度是指在國內生產總值當中,外貿創收所占據的比例,這個參數用于體現國家貿易是否開放,也用于衡量國家是否和國際市場形成緊密關聯。隨著我國不斷融入國際貿易當中,同時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我國的外貿依存度也在不斷提高。這說明我國對外貿易開放程度水平較高,同時對外貿易也成為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領域,我國的經濟發展開始和世界經濟發展之間不斷實現融合。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也可以抓住時機,實現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
如何保持優勢實現我國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我國在對外貿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在多個領域存在優勢,但我們不能因此驕傲自滿,而應當保持自己的優勢,進一步讓其為我國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不竭動力。筆者認為,可以從政府方面和企業方面共同制定對策。
政府方面
1.積極給予政策支持
回顧我國最近四十幾年的發展歷程,先后經歷了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改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這樣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發現,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是越來越高的,這也給對外貿易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和廣闊的空間。而在此基礎上,我國對于外貿給予了一定的政策傾斜,例如減少稅費等政策,都在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所以不難發現,包括稅收政策在內的政策支持,對于對外貿易的發展意義重大,需要進一步給予稅收優惠,為刺激貿易市場、提高商品需求創造必要的條件。
2.建立健全法律法規
健全的法律體系是對外貿易健康發展的必要前提,所以需要我們結合國際貿易法和世界貿易的相關規則以及我國客觀實際,進一步對我國現有的對外貿易法律法規體系進行完善,從而讓我國對外貿易法走向成熟,確保我國在各項貿易開展的過程中有法可依。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壟斷是一種非正當的市場競爭形式,其對于貿易的進行、經濟的發展均是弊大于利,對此我國也已經對《反壟斷法》的建設給予重視,于2007年8月頒布《反壟斷法》以來,不斷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和完善,并成立了反壟斷委員會,這表明我國在貿易法律法規的建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可以維護正常對外貿易活動的順利開展,掃清國內市場經濟發展的阻礙,確保中國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企業方面
1.提高勞動者素質
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是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優勢,但實際上存在的客觀情況是我國勞動力綜合水平不高,對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而言較為不利,尤其是難以支撐未來較長時間內復雜的經濟形勢變化下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需求,所以這就需要我們對勞動力綜合素質給予足夠的重視。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不僅需要提高招聘門檻,更需要其積極對員工進行培訓,鼓勵員工個人業務水平和綜合素質的提升,這樣不僅有助于提高員工的勞動生產力,更可以讓企業在未來的發展中搶占先機,在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
2.重視產品質量、實行品牌戰略
產品質量的好壞對于企業的聲譽而言起著決定性作用,同時也是影響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的重要因素。為了保持我國在對外貿易中的優勢地位、實現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提高產品質量、實行品牌戰略就成為了大勢所趨。只有產品質量得到了保證,企業才能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進而提高競爭力。對于企業而言,品牌是“門面”,是外界認識企業的第一道窗口,所以實行品牌戰略、打品牌戰也是企業占據國際市場、搶占市場份額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仍然在不斷提高,所以需要更多企業積極進行品牌建設,在國際塑造良好形象。所以無論是從企業自身發展的需求出發,還是我國對外貿易優勢的保持,還是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實現,質量意識和品牌戰略仍然是我國企業需要堅持的道路。
3.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發展途徑
從長遠來看,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發展途徑是保持對外貿易優勢、促進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關于“引進來”和“走出去”戰略的意義,我國有專家學者進行了探索,認為我國要實現外貿增長,就離不開“引進來”和“走出去”戰略,在對外貿易快速發展的今天,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引進來”是積極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模式,學習既有的成功經驗,從而達到提高產品質量的目的;而“走出去”一方面是指我國企業積極出海,打開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則是指派遣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來到國外先進企業中學習,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并建設溝通協作渠道,實現市場的開拓。所以隨著時代的變化,我們需要對“引進來”和“走出去”重點的變化形成清晰的認識。
結 語
綜上所述,現在我國的對外貿易優勢明顯,主要集中在地域、人口以及經濟體制等多個方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片面地依賴現有優勢,故步自封是無法實現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而是需要政府和企業聯手,各自發揮優勢、互相補充不足,最終才能不斷發揮、擴大我國對外貿易的優勢,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積極開展,為我國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莫斯科國立大學)
參考文獻:
[1]岳壯.我國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研究[J].品牌(下半月),2015(11):92.
[2]孫勝杰.國際貿易形勢和我國對外貿易發展[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上旬刊),2015(05):171-172.
[3]李慧敏,馬月紅,胡成功.保持我國對外貿易優勢 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J].商場現代化,2008(17):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