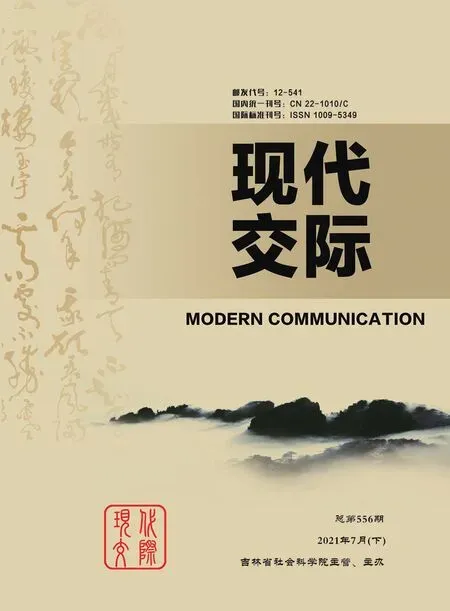馬克思《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概念論析
趙子明
(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山東 日照 276826)
異化是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明確分析了勞動異化的問題。何謂異化,以及關于馬克思異化概念的適用范圍、異化概念在馬克思思想體系中的地位等問題,存在著諸多爭議,對異化概念的使用甚至出現濫用現象。本文通過考察《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思考馬克思對異化的解讀,由此明晰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概念,從而正確使用異化概念,而不是隨意將其濫用。
一、問題的提出
無論是在學術研究,還是在媒體報道中,異化似乎成為一個十分常用的概念。到底應該如何使用異化概念,或者說在哪個意義上使用異化概念?有研究者指出:目前我們對異化概念的使用出現濫用現象,異化概念內涵不清、指稱混亂,往往“把異化簡單地當作某種事物本身的‘異常變化’或‘變質’”[1]。這與馬克思本身的異化概念及其異化思想相去甚遠。異化概念的濫用,不僅不利于我們正確理解馬克思的異化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學術研究的混亂。
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學者嚴厲批評過異化概念濫用現象:“任何錯誤、挫折、事與愿違,都是異化,這是多么廉價而又萬能的科學!”[2]64同時,也有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異化概念應該應用于特定的歷史條件,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況,不應該用其分析社會主義的社會情況:“他們脫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把異化這種反映資本主義特定社會關系的、歷史的、暫時的形式變成了永恒的、可以無所不包的抽象公式。然后,又把它運用于分析社會主義,從而提出社會主義的異化問題。他們就是用這種方法把社會主義社會同資本主義社會混為一談。”[2]57但也有學者認為異化也可以用來分析現在的社會狀況:“其實,我們沒必要把馬克思的概念都當成與己無關的事情,總認為馬克思是批判那個時代的,批判別人的。這樣的話,我們總是過濾了自己,總會讓馬克思與我們生活的時代有一墻之隔。我們完全可以轉用異化的概念,來分析我們的勞動狀況。”[3]而對于何謂異化,也是眾說紛紜:有人認為異化“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有人把異化“等同于對立統一規律”,也有人把異化“看作否定之否定規律”[4]。
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異化是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馬克思思想中最重要、最精華的部分之一,把馬克思的異化思想看作人道主義。他們認為有兩個馬克思,一個是青年馬克思,一個是晚年的馬克思,提出異化的那個“馬克思”,是他們所認可的馬克思,“晚年馬克思”與“青年馬克思”的不同是由于“晚年馬克思”思想的“退化”,他們“把‘異化’視為馬克思的中心概念,把馬克思主義視為人道主義”[5]。
國內學者不同意西方馬克思主義關于“兩個馬克思”的觀點,但也注意到了馬克思異化思想的轉變,如何看待馬克思異化思想及其轉變,國內學者也有不同觀點。有學者認為,異化是馬克思思想的基本概念,是馬克思一生都在使用的概念,而馬克思在研究異化問題時有一個轉變,即從早期的“道德批判優先”轉變到后來的“歷史批判優先”,這也是馬克思早期的異化觀念與晚期不同的原因,而這個轉變正是由于馬克思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在早期,馬克思沒有完全擺脫費爾巴哈、黑格爾等人異化觀念的影響,在考察人的異化時沒有完全考察“現實的人”,在批判資本主義時,青年馬克思主要通過道德進行批判。隨著馬克思思想的成熟,馬克思并沒有放棄異化這個問題,而是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之后,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繼續考察,即成熟時期的馬克思“歷史評價優先”。[6]但也有學者認為,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異化概念,并不屬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而當馬克思的思想成熟以后,馬克思放棄了異化概念。馬克思的異化概念也并不存在所謂的“視角轉換”,異化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中也不具有實質性的、基礎性的地位。[7]還有學者認為,異化、人的本質的異化或人的異化,并不是個嚴謹的科學概念。《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異化的論述并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方式,而更像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采用的一種夸張與形象的描寫方式。嚴格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人的本質并不能用異化描述:“嚴格講,人或人的本質的異化只有兩種情況,一是死亡,一是精神失常,這正是‘異化’一詞的原意,然而今天沒有人如此使用異化概念。”[8]
馬克思明確地提出異化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在他之前,黑格爾與費爾巴哈都曾使用過,馬克思通過異化勞動,分析當時資本主義的社會狀況,批判國民經濟學。此后,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似乎不再正面使用“異化”一詞,但在后來的著作中如《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資本論》中又恢復了使用,“盡管不再如《手稿》中那般密集”[9]。那么,馬克思到底在何種意義上使用異化概念?我們不能不溯本清源,從馬克思的早期文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開始認真解讀。當然我們也應該認真解讀不同時期不同作品中馬克思異化思想的轉變和發展,但限于篇幅和本文寫作目的,本文暫不對馬克思在不同時期對異化的論述進行完整的描述和研究,而將主要目標放在馬克思最初是如何界定異化,以及在哪個層面上使用異化。如此才能正本清源,避免馬克思異化概念的濫用,明晰當時馬克思的異化概念與他思想成熟后的不同,更全面地了解馬克思的異化概念及其異化思想。
二、勞動異化及其規定性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雖然明確提出了異化,但卻沒有直接論證異化概念本身,而是論證了異化勞動及其四個規定性。可以通過馬克思對異化勞動及其規定性的相關論證,解讀馬克思的異化概念。
規定性一:勞動者同勞動產品相異化。
勞動本質上來說是人的外化,勞動所生產的產物不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而存在,成為一個獨立的存在,異己的存在。“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10]47勞動產物應該歸屬于勞動者,應該讓勞動者過上更美好的生活,但在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情況下,勞動產品反而不屬于勞動者,甚至與勞動者對立。而且,隨著勞動者制造更多的產品,創造更多的財富,他反而愈發貧困,“而且越受自己的產品即資本的統治”[10]48。
規定性二:勞動者同勞動本身相異化。
人與勞動的異化,還包括人與勞動過程的異化。“異化不僅表現在結果上,而且表現在生產行為中,表現在生產活動本身中。”[10]50從理論上來說,勞動生產的過程應該讓人感到快樂與幸福,在勞動過程中人應該會得到肯定,人們也應該樂于去勞動。但在資本主義社會情況下,勞動產品與勞動者無關,勞動者被迫勞動,勞動并不是勞動者的自愿。于是“勞動已經不再是一種自我確證和自我滿足,相反,成了人們的負擔,是勞動者‘自身的喪失’”[11]。
規定性三:勞動者同他的類本質相異化。
關于人的類本質,馬克思認為應該是自由的、有意識的:“人把自身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10]51而這也是人與動物之間最大的區別。而人的類本質則在有意識改造客觀自然的實踐中,在將自然“人化”的過程中得以表現:“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10]54但是由于異化勞動,人的勞動不出自人的自由意志,變成一種強迫的負擔:“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10]54,人被貶低為像動物一樣的存在。于是異化勞動導致人自身與人的類本質異化。
規定性四:人同人相異化。
由于勞動產品并不屬于勞動者:“如果工人的活動對他本身來說是一種痛苦,那么這種活動就必然給他人帶來享受和生活樂趣。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為統治人的異己力量。”[10]56而由之前的三個規定性,勞動者也必定與這個占用著應該屬于勞動者產品的人相異化。于是,“通過異化的、外化的勞動,工人生產出一個同勞動疏遠的、站在勞動之外的人對這個勞動的關系。”[10]57
三、異化概念的界定
首先,馬克思所謂的異化是指勞動對象化的產物與主體——人相疏遠,直至與人相對抗,阻礙人的發展。異化是在勞動對象化過程中出現的,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勞動對象化都是異化。馬克思指出:“勞動的產品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的、物化的勞動,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10]54人的勞動是一種能動的、自主自覺活動,通過這樣主體自覺活動,使勞動對象發生變化,也使主體自身的目的和力量等凝結于勞動對象之上,其產物就是勞動產品。人的勞動、人的勞動對象化,體現了人的主體性,不僅在勞動對象和勞動產品上深深地打上人的目的、力量等主體性印記,而且也在勞動工具和其他勞動資料上打上了人的主體性印記。隨著勞動對象化范圍的不斷擴大,自然的世界越來越打上了人類勞動的印記,成為人的世界。勞動的本性,即是勞動對象化,也即人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也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人的勞動對象化的過程,也就是人的目的不斷通過勞動得以實現的過程。但出于某種原因,勞動對象化的產物卻與主體的人產生了分離,直至與人相對抗,阻礙人的發展,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
但是,我們如何確定對象化的產物與主體相對抗呢?這需要一個新的標準。而這一新標準就應該是對象化之后的產物能否重新回歸到主體,為主體服務,促進主體的發展,“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主體能否‘領有(Aneignung)’外在的對象,或者能否實現所謂的‘對象性剝離(Entgegenst ndlichung)’”[12]。也就是說,主體人勞動對象化之后的產物能夠回歸到主體,為主體服務,促進主體的發展,這即是勞動的對象化;反之,對象無法復歸主體,對象與主體分離阻礙主體的發展,即是勞動的異化。
由此,我們至少可以做如下區分:即并不是事物發生了“異常變化”或是“變質”都是異化,也不是人在生產生活中出現的所有錯誤、挫折、事與愿違,都是異化。如不能簡單地將部分大學生奮斗觀存在奮斗態度認知、奮斗目標定位、奮斗價值標準的問題定義為異化傾向;也不能將現代休閑存在的問題,一味都歸為休閑異化,等等。只有人在勞動實踐中的對象化產物,即對象化的客體沒有回歸主體,而是與主體對抗,妨礙主體的發展,才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
人的對象化的活動,亦即人性化于自然的活動,其所創造的產物(如物質器物、社會規范等)能重新回到創造者手中,為人所利用和控制,這就意味著人性的復歸。如果這種對象化活動的創造物從此不復歸于創造者之手,甚至反過來成為控制自己的異己力量,這就是所謂“異化”現象。如宗教崇拜的神圣對象及為規范崇拜行為而形成的宗教制度,即是人性對象化而成的文化創造,但當它們出現在人們的頭腦之中和人類社會之上時,卻總是被抬高成為自然和社會的創造之主,創造神的人反倒成了神創造之物,人異化為神的身上的人性則被認為是支配人和自然的神性,再也不能復歸于人的自身,這就是宗教與人性的異化。一旦人把異化于神的人性奪回來,使之復歸于人的自身,人就會成為自身命運的主人,宗教與神便不復存在了,也就取消了宗教與人性的異化。
其次,按照對象化產物回歸主體的不同境況或路徑,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屬于狹義的異化。按照黑格爾對異化的分析,存在著兩種異化:一是狹義上的異化,是指對象化脫離主體之后,沒有回歸,并且與主體相對抗;二是廣義上的異化,是指經歷了對象化之后,又經歷了對異化的揚棄,對象化的客體再次回到了主體。“‘狹義的異化’……只能停留在否定階段。對主體而言,這種異化無異于沒有回報的自我犧牲,因此可稱作‘惡’的異化。而‘廣義的異化’則不同,它包括了對‘狹義的異化’的揚棄過程,從而使主體的犧牲得到了補償,因此可稱作‘好’的異化。”[13]馬克思基本沿用了黑格爾的說法,但卻與黑格爾的異化觀點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因為在黑格爾的異化觀點中,異化最終會向著回歸主體的“好”的異化發展,“按照黑格爾辯證法的本性,所謂異化只能是向主體回歸的‘好’的異化,即‘異化辯證法’”。而這顯然不符合馬克思所處時代的社會現實,黑格爾的異化觀點無法解釋勞動者的異化勞動,因為在異化勞動之中,對象化的產物不可能再回歸主體也就是勞動者了。于是,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論證異化勞動時,是在否定意義上使用異化概念,也就是“狹義的異化”,用其來批判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狀況。
由此可見馬克思關于異化的概念是:主體創造了一個對象化的客體,客體脫離了主體而獨立存在,之后對象化的客體沒有回歸主體,而是與主體對抗,妨礙主體的發展。馬克思否定并批評這樣的異化,認為其阻礙了人的發展。
最后,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如果異化現象出現后,當對象化的客體離開主體并無法返回,而且與主體相對抗,那么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而這就要引出馬克思的重要思想——歷史唯物主義了。
通過異化勞動的規定性,我們已經得知,當馬克思在研究異化問題時,研究的是勞動者的異化狀況,是現實的人的異化狀況,而不是抽象的人。我們認為,這已經具有一定的歷史唯物主義特點了,但此時馬克思的思想體系還沒有成熟,于是他借用了之前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人使用過的“異化”這個概念,作為他的思想武器,去分析、批判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狀況。而當馬克思的思想成熟之后,他超越了異化思想:“他不再用異化理論說明歷史,而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說明歷史;他也不再用異化理論說明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而是用剩余價值學說來科學地說明它們。”[2]54因此,認為異化是馬克思的中心思想的觀點是不正確的,馬克思的中心思想或思想核心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當然,異化問題應該也是馬克思一直關注的問題,只不過后來他不再用異化來描述和分析問題了,而是轉而使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進行分析。或許他不再使用異化,也有可能是因為之前有大量的哲學家用過這個詞,馬克思想與他們區分。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在異化“其上加了引號,加重了這一概念中客觀性、科學性的意涵,以區別于他所批判的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9]28。
今天,馬克思所批判的異化現象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依然存在。而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其根本制度與社會現實與資本主義社會狀況有本質不同,異化現象即使還存在,也絕不是作為一個社會的主要現象存在。因此,如果將異化作為一個普遍現象來分析社會主義社會,顯然是不準確的,也是一種濫用。而且,既然馬克思在思想成熟之后是在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下來考察異化問題,我們是否也應該更多地使用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社會狀況,而不是簡單地通過異化來一概而論。
四、結語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論證異化勞動時,是在否定意義上使用異化概念,也就是“狹義的異化”,是指勞動對象化的產物脫離主體之后,沒有回歸,直至與人相對抗,阻礙人的發展。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之前,馬克思用異化來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問題。而當馬克思的思想成熟之后,他超越了異化思想,利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分析問題。
今天,許多研究者用異化分析社會現象,但使用時往往不夠準確,甚至不在馬克思的本意上使用異化概念,而是隨意將自己“創造”的異化概念貼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標簽,顯然是不正確的,是一種濫用。另外,也不宜將異化作為一種普遍現象,來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因為馬克思在思想成熟之后,是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考察異化問題的,我們也應該更多地使用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社會狀況,而不是簡單地使用異化來一概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