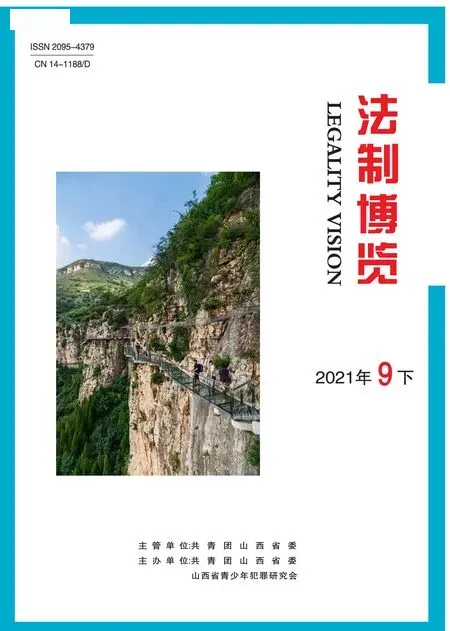基于公司治理視閾下股權代持的法律規制
邵 群
(吉林財經大學,吉林 長春 130117)
隨著現階段我國社會的進步發展,出現了新型的企業融資方式——股權代持。在公司實踐運行發展中,由于相關的具體規定不夠明確、存在一些潛在的法律風險以及對方利益主體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等,影響了公司的長效運行發展。在公司治理視角下,應完善股權代持的相關法律規章,以望能夠促使股權制度有所增益。
一、公司治理視角下股權代持存在的問題
(一)無法有效保障多方主體的權益
在關于股權代持有關案件處理過程中,所牽涉的利益主體較多,其中就包括了名義股東、實際出資人以及公司等等。在公司進行經營的實際過程中,名義股東有著較大的股東權利,且行使權利并不受實際出資人的約束,因而極易可能會發生名義股東無視和實際出資人之間的協議約定,做出轉讓股權或者不利實際出資人的一些行為,進而導致實際出資人后期無法成為股東或者直接失去股東權益。
(二)存在潛在法律風險
由于股權代持的相關法律關系相對較為錯綜且復雜,因而這就會導致多方主體權益承擔一定的潛在法律風險。一是名義股東潛在的法律風險,其具體表現為若是實際出資人出現虛假出資或者沒有按照相關的協議約定進行出資,且直接對公司的運營發展產生影響,那么這個時候名義股東就需要承擔有關的法律責任,像是限制名義股東離境、補繳出資差額以及在網絡平臺中登記不良信息等等。二是實際出資人的潛在法律風險,在關于其確認股權或者股東資格方面,相關法院部門一般情況下會根據工商登記、股東名冊以及股東表決記錄等等來確認公司的股權以及股東資格認定,據我國《公司法》相關規定表明,股權代持合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法被法院有效認定的,那么此時將無法保障實際出資人的歸屬股權投資申請權益。三是股份持有公司潛在的法律風險,若發生名義股東無法完成隱名股東的缺失資金或者私自轉讓股權時,再加上股權協議被法院部門認定無效后,那么這個時候公司將會出現注冊資金缺少的風險。
(三)無效認定后缺少相關的規定標準
現階段我國的《公司法解釋(三)》中有關于認定股權代持權利的相關法律法規,但其中并沒有明確規定效力認定是否能夠以其他部門規章以及更加詳細的內容為參考依據。比如像是在公司與公司之間發生糾紛案件中,一審法院部門以最終審判結果是雙方公司均違反《股權管理辦法》相關規章制度為準,來判定股權代持合同無效。二審法院部門則根據原《合同法解釋(一)》否認了《股權管理辦法》的無效股權協議認定,并明確提出不以行政規章以及地方法規來作為合同認定無效的相關依據,并根據《民法典》合同法編中相關規定維持了一審判決結果。基于以上現象可以分析得出,在關于股權合同認定方面,相關的法律法規還存留著一些問題,這就要求及時補充和完善管理方面的規定以及法律條文上的效力規定。另外,還需深入分析和研究當股權代持被認定為無效之后,這樣的處理結果是否符合《民法典》合同法編有關制度中的無效規定,股權有著自身的特殊性質,并不能通過折價賠償或者返還的方式來進行處理,還需制定相關的具體規定來符合股權代持的特殊性質[1]。
二、公司治理視角下完善股權代持法律規制的相關建議和措施
(一)平衡維護多方主體的相關權益
由于在股權代持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像權利人無視協定規定而濫用權利的此類現象,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多方利益主體的經濟權利,這就要求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定相應的制度來有效平衡多方的主體利益。在制定平衡法律規定制度方面,應該適當賦予債權人一定的求償權利,若是出現名義股東不顧協議約定濫用股東權利直接侵犯到債權人時,此時債權人可以要求名義股東或者股權公司承擔相應的責任,公司有直接的證據證明和名義股東沒有直接的關聯的話,可以免除公司的承擔責任,直接申請名義股東進行賠償。另外,還可以借鑒西方先進國家股東代持的優秀經驗,像是美國名義股東和隱名股東雙方互相監督的方式,可以建議賦予實際出資人相應的監督權利[2]。一般情況下,實際出資人是很難知曉名義股東行使的權利是否侵害到自身的權利,若實際出資人可以行使監督權利的話,就能夠具體了解到名義股東的權利行使情況,并做好及時制止防范。同時還建議賦予股權公司向實際出資人主張求償申請權,以此來保障公司的切身權益不受侵害。通過具體說明實際出資人和名義股東分別股權代持的關系,促使實際出資人能夠全面履行公司的實際出資義務,從而確保公司資本能夠正常有序運行[3]。
(二)完善風險防范行為
在股權代持中相關的主體權益存在著多方面的法律風險,因而構建相關的風險防范機制對于其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需要將相關的股權代持行為進行細化區分以及完善,規定側重點,像是股權協議中的違約承擔就需要重點闡述,促使實際出資人以及名義股東能夠清楚明確自身的代持股權的違約責任以及相關規范,采用增加利益主體違約成本的方式來保障避免存留潛在風險行為,促使其能夠履行合同約定行為。其次,還需明確規定名義股東行使股東權利的具體程序方式,避免出現股權代持產生的法律風險,并以此來保障實際出資人能夠準確掌握自身投資股權的運行情況。再次,還需要注重避免出現非法股權代持行為,在公司的實際經營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諸如此類的非法股權代持行為,像是在2015年某公司就出現了這一現象,這種行為不僅僅和社會的公共秩序準則相悖,還嚴重違反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并直接損害公司相關的利益主體,對于市場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作用[3]。針對于此,我國的相關司法以及公司法相關解釋可以適當采取列舉的方式,將非法股權代持行為的基本特征以及構成元素闡述出來,明確禁止出現此類現象,同時加大懲處力度,制定具體的懲處措施來進行嚴格規定。最后,還需要明確規定關于隱名股東的股權資格認定標準和要求,在認定方面,可以考慮使用形式原則以及實質相結合的認定理念,在相關的司法規定中就提出了關于隱名股東顯名以及資格認定的標準條件,并將股權代持的主體法律以及內外部結構有機結合起來,并使實際出資人在對待投資股權方面能夠采取理性的態度,從而更好地解決股權代持股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認定難點以及法律糾紛[4]。
(三)加強認定無效后的具體規制
在關于股權代持資格被認定無效方面,《公司法》相關的規定對其進行了詳細說明,但并沒有明確規定具體哪種情形下認定無效,并在司法和立法規定中將股權代持協議歸屬于民事合同范疇內,但由于股權代持合同自身的特殊性,因而又不能將其按照《民法典》合同法編的相關規定來進行認定。那么當股權代持合同被認定為無效之后,需要相關的立法機構以及司法部門綜合考慮實際出資人、名義股東以及其他利益主體股權的后續解決問題。若是將《民法典》合同法編應用在其中之后,就會要求歸還隱名股東之前的出資股份,名義股東此時就需要出資相應的份額來獲取股份,那么當名義股權缺少足夠的財產的話就會影響到公司的經營發展。針對以上現象,這就要求了堅持民主自愿的基本準則,通過轉讓第三方認購股權或者認購原出資比例的方式,又或者是退還股款公司減資的方式,提存股權收益,以此來促使在股權代持認定無效后股權份額能夠進行有效提存,從而促使公司的運行發展得到有效保障。
綜上所述,在建設現代化公司治理的發展形勢下,應不斷完善和優化股權代持的法律法規來規制公司運行發展中所涉及的法律關系,從而保障公司制度能夠符合社會發展需求。在股權代持方面,通過有效防范潛在的法律風險、加強認定無效后的具體規制方式,來規范股權代持的法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