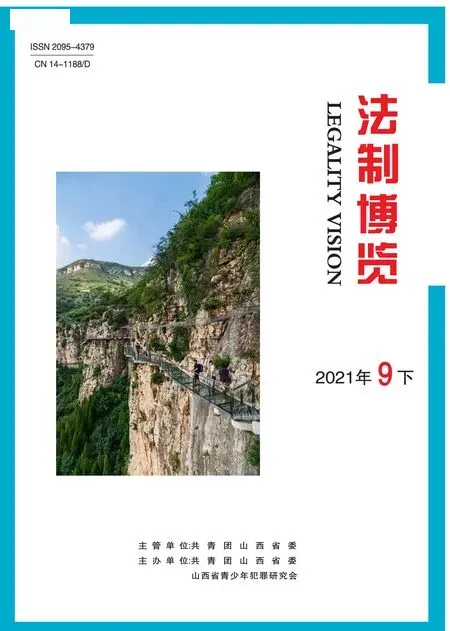自媒體背景下網絡謠言的《刑法》治理研究
成瑤笙
(吉林財經大學法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自媒體是一種為個體提供信息生產、積累、共享、傳播內容兼具私密性和公開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隨著互聯網信息通信技術的進步與更新,微博、微信、短視頻平臺等自媒體平臺得到了蓬勃發展。在自媒體時代信息呈現爆炸式的增長,同時也為網絡謠言的滋生提供了穩定的信息流通條件。自媒體時代網絡謠言四起,嚴重污染了自媒體環境,影響自媒體平臺的健康發展。不法之人鉆法律空子,惡意散布網絡謠言,必須要予以《刑法》規制,阻止網絡謠言危及社會秩序,營造積極和諧的社會環境。隨著網絡謠言愈演愈烈,甚至嚴重污染網絡環境,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國家也接連出臺相關法律,治理網絡謠言泛濫的問題。為了進一步減少網絡謠言現象,降低網絡謠言引發的風險,我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中,提出將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納入《刑法》規制范圍,要憑借《刑法》的力量遏制網絡謠言犯罪行為。即使我國在網絡謠言《刑法》規制方面出臺了相關的法律法規,但仍有需要完善之處。
一、自媒體時代網絡謠言的危害
謠言作為一種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言論,在傳播的過程中被人利用,便可能會引發負面的網絡傳播效應,且真正具有危害力的謠言是具有攻擊性的,容易產生消極的社會影響。[1]網絡謠言在學界雖沒有統一的觀點,但網絡謠言通常被認為是憑借網絡平臺傳播的不實的無中生有的信息,這個信息可以是虛假的,也可能是未經證實的信息。但在刑法學領域而言,《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規定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即“編造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依據此法律規定可以理解為,《刑法》層面上的網絡謠言指的是明知虛假信息卻進行網絡散布并形成了惡劣影響的信息。自媒體時代網絡傳播迅速高效,網絡謠言傳播所產生的危害也是不可忽視的。
第一,從個體角度而言,自媒體時代網絡謠言嚴重損害個體利益。因為惡意傳播網絡謠言,隨意捏造虛假信息,對他人進行無端的揣測、謾罵甚至是暴露個人隱私等,對個體造成了心理和生理上的傷害。第二,從社會角度而言,網絡謠言若形成一定規模,可能會煽動圍觀網民的情緒,更有甚者可能會影響現實社會的秩序,危及社會公共安全。第三,從國家角度而言,網絡謠言通過自媒體平臺傳播到世界各地,不實和極端的網絡言論,也可能給國家的形象抹黑,在國際上形成惡劣影響。自媒體時代網絡謠言必須要進行嚴格規制,杜絕網絡謠言的傳播,嚴格打擊不法之人傳播不實言論。《刑法》作為規制網絡謠言的一大手段,必須要貫徹到底,嚴懲造謠之徒。
二、自媒體時代網絡謠言《刑法》規制現狀
(一)網絡謠言犯罪主體的范圍較窄
我國規制言論犯罪的主體通常限于自然人,但在自媒體時代,獨立的個人或是某一單位組織也可能成為犯罪的主體,網絡謠言的爆發,可能是一個組織的共同編造和傳播的結果,這就說明了我國《刑法》在網絡謠言犯罪主體規制方面的漏洞。自媒體時代,具有規模化和組織化的單位,通過輸出信息獲取流量和利益,在傳播謠言方面具有系統的產業鏈,這也加大了網絡謠言傳播的范圍,擴大了網絡謠言的影響,所造成的傷害也是巨大的。但是,我國目前通常按照非法經營罪對單位實施的網絡謠言犯罪進行規定,即使是在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這種專門針對網絡虛假信息的罪名中都沒有將單位納入犯罪主體的范圍。[2]因此,可以看到我國《刑法》在網絡謠言犯罪主體界定方面范圍較為狹窄,這也影響對網絡謠言犯罪的《刑法》規制力度。
(二)網絡謠言犯罪的界定標準模糊
我國《刑法》有關網絡謠言犯罪的界定,一般采取“新瓶裝舊酒”立法模式,認為網絡犯罪與傳統犯罪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并無特殊之處,兩者只是犯罪手段和途徑有所差異,因此,治理網絡犯罪甚至不需要專門的立法,換言之,現有的法律沒有專門針對網絡犯罪制定的法律,而網絡犯罪可以遵循《刑法》規定進行具體處理。[3]但是我國《刑法》并沒有對網絡犯罪進行特殊的說明和規定,也缺少網絡謠言犯罪方面的細則,沒有明確的網絡謠言犯罪的界定標準,且在審理網絡謠言犯罪的過程中,也缺少專門的法律規定,而主要通過對傳統罪名進行擴大解釋以此來規制網絡謠言犯罪。然而在自媒體時代,網絡信息傳播涉及眾多,影響也較為廣泛,隨著網絡謠言犯罪的增多,并且網絡謠言犯罪所引起的社會危害和個人危害也嚴重影響了社會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對社會治理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然而《刑法》卻無法精準地解決網絡謠言犯罪問題,這就導致法律懲罰與犯罪之間的不協調和不匹配。
(三)網絡謠言犯罪的懲罰力度不足
網絡謠言犯罪的懲罰力度不足,對不法之人沒有起到震懾作用。我國《刑法》所規定的懲罰力度偏低。以誹謗罪來說,誹謗罪法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且有期徒刑中只有一個層次的幅度刑。行為人即使造成受害人及其近親屬自殺或者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國家利益等危害結果,最高也只能受到三年有期徒刑的懲罰。[4]違法犯罪成本與獲益相比,網絡謠言犯罪成本低也給不法之人以身犯險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三、自媒體時代網絡謠言《刑法》規制的完善措施
(一)適當增加部分網絡謠言犯罪主體
根據網絡謠言治理現狀可以知曉,適當增加部分網絡謠言犯罪主體,擴大網絡謠言犯罪主體范圍,是網絡謠言《刑法》規制完善的必經之路。一方面,自媒體時代,個體信息傳播雖起到助推的作用,但個體的力量遠不如訓練有素的網絡謠言生產與傳播的單位,依托網絡平臺而生的“單位”憑借多元的傳播渠道和大量的粉絲團體,能夠在短時間內將網絡謠言傳播到各個平臺,從而引起大量網民的跟風與轉發,造成惡劣的影響。因此,我國《刑法》網絡謠言犯罪規制也需要將“單位”納入網絡謠言犯罪主體部分。另一方面,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和誹謗罪作為網絡虛假信息犯罪的兩種主要形式,其中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罪擾亂社會秩序,誹謗罪侵犯個人合法權益,以單位為主體的網絡謠言犯罪行為同樣對社會和個人造成危害,因此,可以適當增加網絡謠言犯罪主體。
(二)推動落實網絡謠言犯罪界定標準
網絡謠言犯罪界定標準清晰,也能夠提高網絡謠言犯罪《刑法》規制的效率和力度。以網絡謠言誹謗罪為例,我國《刑法》規定,誹謗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轉發五百次”的主體也算作為一般主體。在網絡誹謗案件審理過程中,行為主體主要為信息的發布者和轉發者,發布者是網絡謠言第一發布人,其網絡誹謗的主體地位是確定的,但轉發者是否能夠成為誹謗的主體仍舊存在較大的爭議。發布者的誹謗主體地位是沒有任何異議的,出發點是故意為之的,但是跟隨的轉發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轉發造成惡劣影響的也應受到相應的懲處,若是轉發者本身了解信息是為他人偽造的,而仍舊選擇轉發該信息導致謠言影響范圍隨之擴大,那么可以認定該轉發人存在主動誹謗他人的責任。在網絡謠言犯罪界定的過程中,還需要根據現實情況進行分析,但界定網絡謠言犯罪標準是《刑法》規制需要持續關注的問題。
(三)加大網絡謠言犯罪《刑法》懲治力度
第一,提高網絡謠言犯罪的法定刑。有關誹謗罪的刑罰較輕,而誹謗所造成的受害人的傷害程度較深,罪與罰之間沒有得到平衡,因此,需要適當提高誹謗罪的刑罰力度,對造成嚴重后果的網絡謠言犯罪必須要予以嚴懲。第二,增加網絡謠言犯罪的罰金刑。自媒體時代,信息與流量可以變現,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許多不法分子鋌而走險,選擇以散布網絡謠言的方式謀取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刑法》應該適當增加犯罪罰金,根據網絡謠言所造成后果的嚴重程度設立不同等級的罰款。尤其是對犯誹謗罪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的主體普遍增加罰金。第三,增加剝奪網絡謠言犯罪者終身權利的刑罰。對傳播不實言論影響社會秩序的犯罪主體,予以剝奪終身權利的刑罰,維護和諧的社會秩序。
四、結語
自媒體時代,虛擬的信息傳播環境為不法之人傳播網絡謠言提供可乘之機,網民可以隨意在網絡上發布言論,甚至利用不實信息煽動情緒,污染網絡信息環境,破壞社會正常秩序。我國《刑法》關于網絡謠言犯罪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也取得了實質性的治理效果,但并沒有完善的網絡謠言犯罪的《刑法》規制措施。因此,在未來治理網絡謠言犯罪案件時,還需要根據現有的《刑法》規定,并結合現實的案件情況,合理規制網絡謠言犯罪行為,維護個人利益和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