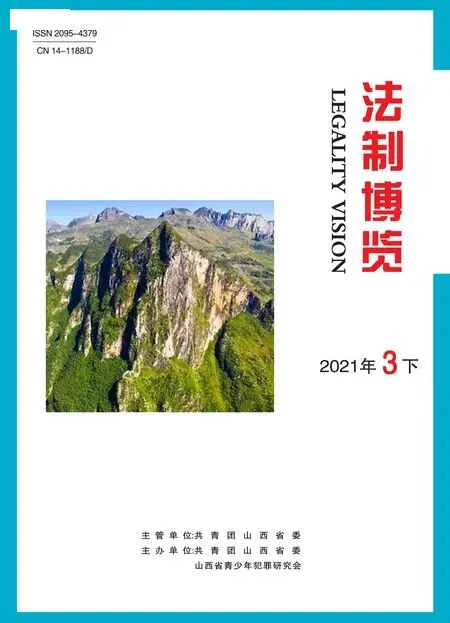家庭暴力人身安全保護令落實問題研究
納曉菁
(寧夏職業技術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
一、引言
近二十年前,一部名為《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的電視劇,第一次把全中國觀眾的視線聚焦到家庭暴力現象上來。劇中的人物設定、場景鋪排、劇情發展,生動地展現了高知人群家庭暴力案件的社會縮影。
時至今日,家庭暴力案件并沒有隨著社會不斷發展進步而消失,反而演變出更多類型、更多特點。中國家庭暴力發生率為29.7%-35.7%,受害者多半為婦女,而老人、兒童和男性的比例也有所上升。鑒于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在千呼萬喚中正式出臺。這是一部反對暴力、保護弱勢、維護和諧的良法,尤其是其中確定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更是對相關法律空白的補充和對婚姻家庭立法的一次創新。
二、地區家庭暴力案件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落實情況
(一)地區家庭暴力案件概況
早在2008年,寧夏籍作者李丹丹、安琳、高燕秋三人,就發表了題為《寧夏農村地區家庭暴力發生情況研究》的論文,對我區農村家庭暴力發生情況進行了研究探討。他們抽取的2000余名受訪者均為15-64周歲的女性,且僅在2007-2008一年時間內,受訪群體家庭暴力總發生率就高達30.1%[1]。時間到了2018年7月,《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實施已兩年有余。但自治區各級公安機關仍然接待處理警情7000多起,發出家庭暴力告誡書500余份;各級婦聯也接到反映家庭暴力現象的信訪投訴 1000多件[2]。
由此可見,寧夏地區家庭暴力現象較為常見。據寧夏縣級以上婦聯統計,我區家庭暴力問題大多分布在已婚人群中,且婚齡多集中在6年至20年期間,群體以農民、個體經營戶和普通家庭婦女為主,更加令人擔憂的是家庭暴力案件致傷比例竟然高達70%。家庭暴力事件發生的原因,大多包括夫妻性格感情不和、一般家庭事務糾紛或第三者介入等因素。家庭作為決定著社會和諧、國家安定的重要構成要素,存在著如此巨大、復雜的隱患,確需公權力適時、適度地介入。
(二)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地區適用情況
2016年至2019年期間,銀川市共有5家基層人民法院先后發出49份人身安全保護令,值得一提的是其中2份是發給遭遇家庭暴力的男性受害者的[3]。在銀川市范圍內,某區人民法院在2016年3月就簽發了第一份人身保護令[4]。此后,近一年時間里,銀川市三區內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受害者僅有7人。據相關工作人員回顧,《反家庭暴力法》頒布之初,隨著新聞報道的不斷宣傳,關于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執行等情況的咨詢人數相對比較集中,但僅在數月后,遭遇家庭暴力的群體對相關法律法規和整個制度設計的關注度就迅速下降了。同時,上述7件家庭暴力案件在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后,均未進入保護令的強制執行階段。對于作出裁定的法院而言,人身安全保護令無疑發揮了正面作用,至少杜絕了受害者再次遭遇施暴的境遇。2020年10月,寧夏高級人民法院與自治區公安廳、民政廳、婦聯聯合制定印發了《關于推進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的實施辦法》[5],進一步明確了人身安全保護令的保護范圍、申請流程、具體效力等實質性問題,使得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落實落細成為可能。
盡管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在我區的落實標準、步驟已足夠細化,但是申請了人身安全保護令卻并未進入強制執行階段的家暴案件,其背后的原因更加令人擔憂。根據現行《婚姻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法定情形中就包含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內容。雖然遭遇家庭暴力最終并不一定都會選擇離婚,但是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者中只有極少數人選擇離婚,難免讓我們對人身安全保護令發揮的真正作用表示憂慮。究竟是人身安全保護令的震懾力得到了認可,還是家庭暴力現象的隱蔽性、復雜性對受害者產生了心理影響,我們不得而知。
三、落實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關于家庭暴力范疇的界定問題
根據《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條規定,家庭暴力主要還是針對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侵害行為。盡管精神侵害也在該條中予以體現,但是法律條文并未通過列舉、解釋、說明等形式對精神層面的侵害行為加以界定。這就導致隨著社會不斷發展,家庭暴力案件類型不斷呈現新趨勢和新變化,但法律規制范圍明顯過于狹小,并不能很好地服務于保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同時,由于家庭暴力范疇界定存在一定不足,在發生冷暴力、精神虐待、性暴力案件時,是否能夠參照執行《反家庭暴力法》中的相關規定,也將成為未知之數。
(二)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程序不夠嚴謹
我國《反家庭暴力法》和寧夏出臺的《關于推進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的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中,都明確規定了人民法院受理人身安全保護令后的所需條件和申請程序。特別是寧夏的《實施辦法》中規定:“人民法院受理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后,應當在72小時內作出人身安全保護令或者駁回申請;情況緊急的,應當在24小時內作出。”然而無論是在上位法中,還是在該實施辦法中,都沒有詳細列舉或規定“緊急情況”的具體標準。這一缺失,勢必會導致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難以對“情況緊急”作出認定。具體實踐中,相關部門為了規范執行上述規定,而統一按照72小時的時間節點對家暴案件進行受理,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受害人權益卻因具體規定的不完備得不到及時充分的保護。
(三)人身安全保護令效力發揮尚顯不足
“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的正式落地,為我國反對家庭暴力、保護受害者合法權益提供了新方法、開辟了新路徑。特別是對防止家庭暴力案件再次發生,起到了顯著的震懾和警示作用。就立法意圖而言,“人身安全保護令”實質上是一種防止家庭暴力案件發生的事前預防措施。
我區《實施辦法》中明確講到,家暴案件受害者在面臨現實危險,暫時不能或不宜回家時,可向公安機關、民政部門、婦聯組織等申請庇護,并由上述單位、組織在收到人民法院送達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后,協助人民法院執行。被申請人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尚不構成犯罪的,人民法院應當給予訓誡,處以罰款、拘留。被申請人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情節嚴重的,人民法院可以將其列入失信聯合懲戒對象名單。這其中存在兩個明顯問題:一是受害者面臨現實危險,但尚未收到法院頒布的人身保護令時,將始終處于危險之中;二是被申請人違反人身保護令但不構成犯罪時,僅需要承擔訓誡、罰款、拘留或被列入失信聯合懲戒名單的后果。這就意味著,施暴者違法成本太低,而受害者的生命健康、人身安全、人格尊嚴等一系列重要權益,都可能在人身安全保護令尚未送達之前被再次侵害。由此可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事前預防效果較差。
四、完善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落實的對策建議
(一)進一步明確家庭暴力的具體范疇
在現有相關法律規定基礎上,立法機關應進一步補充完善法律條文中關于家庭暴力的具體范疇。特別是對精神侵害行為的界定,應通過列舉方式、解釋說明方式或描述性等方式予以明確。盡管冷暴力、精神虐待、性暴力案件在現實生活中多數比較隱蔽、復雜,但是這類行為對受害者精神層面的傷害折磨并不比軀體暴力帶來的傷痛程度輕,有時身體受傷可能已經痊愈,但精神損害卻會給受害者帶來無窮無盡的心理創傷。因此,適當擴大相關法律規制的具體范圍,能夠增強司法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從源頭上對家庭暴力案件受害者進行更為全面的保護。
(二)優化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的程序性規定
一是簡化流程,確保高效。結合《反家庭暴力法》和寧夏《實施辦法》中的程序性規定,在合理范圍內適當縮短人民法院受理時間,簡化申請人提供證明材料的內容,爭取從制度設計上確保人民法院在較短時間內以更加高效、更加便捷的方式迅速反應,切實從細節上對申請人合法權益予以保護。二是“情況緊急”,有據可循。下一步,相關部門應更加細化人民法院在24小時內作出回應的所謂“情況緊急”的具體標準。如,結合具體工作實踐中出現過的緊急情況,對《實施辦法》中“情況緊急”進行定量或定性;或者也可結合以往家庭暴力案件的具體情形,進行窮盡的情況列舉。有了這樣的具體標準,一方面可以確保人民法院快速高效頒布、送達人身安全保護令,另一方面,也從時間上、程序上對申請人合法權益進行了充分有效保護。
(三)確保人身安全保護令事前預防效力充分發揮
很多人把“人身安全保護令”稱為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護身符”,而事前預防、事前保護就是“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的核心要義。“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人,常常是已經被家暴行為造成身體和心靈雙重創傷的家暴案件受害者。因此,充分發揮“護身符”的事前預防作用,是杜絕家庭暴力行為對申請人造成“二次傷害”的有效措施。第一,脫離危險是首要條件。在優化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程序性規定的基礎上,對正面臨或正處于現實危險的家暴案件受害者,應以暫時脫離現實危險為目的,立即交由公安機關、民政部門和婦聯等組織進行保護。待脫離危險后,再由上述單位據實要求人民法院頒布、送達人身安全保護令,且在保護令執行過程中應由上述部門與人民法院和受害人所在社區通力合作,從預防、保護的角度確保“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執行力。第二,充分發揮震懾作用。當被申請人不構成犯罪時,人民法院、協同部門和相關社區應上下聯動,充分了解被申請人的工作、生活實際,從其身邊的人、事、環境入手,逐步增強執行監管力度,增加被申請人的違法成本,令其不敢違反、不能違反、不想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從源頭上對受害人進行全方位、全過程保護。
五、結語
家庭暴力始終依附于家庭或夫妻的特殊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卻常常發生在最親密的家庭成員之間。我們要主動預防和避免家庭暴力事件的發生,還家庭、還社會一方凈土。因此,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就成了有效預防和及時制止家庭暴力,維護社會和諧、家庭穩定的一劑良方。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源頭治理”,同樣適用于家庭暴力案件的全面遏制。隨著“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在生活實踐、社會實踐、司法實踐過程中的不斷完善,這一制度必將對家庭暴力案件的源頭預防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將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