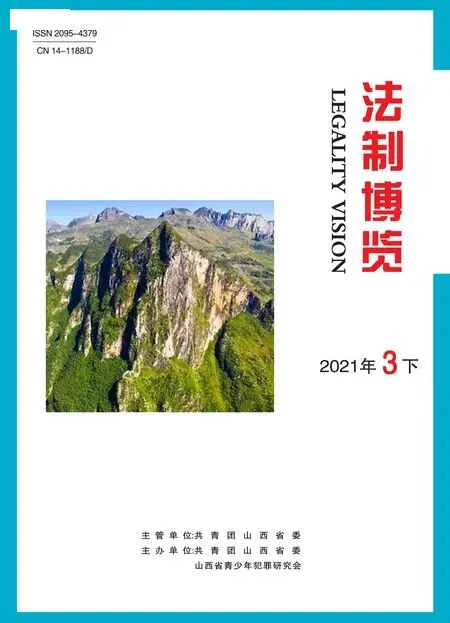網絡眾籌下剩余善款處置問題
王姝涵
(沈陽師范大學,遼寧 沈陽 110034)
近年來,眾籌概念逐漸進入到公眾的視野,我國眾籌市場也迅速從商業領域轉入公益領域。
網絡眾籌作為一種新興的公益融資模式,以“互聯網+金融+公益”為媒介,打破了傳統的公益籌款的方式,實現了“隨手做公益”的行為模式,正是由于它是互聯網迅速發展的產物,這一新興模式缺乏具體的法律制度進行規制,由此產生的剩余善款安置問題也尚待解決。因此,如何規范對互聯網眾籌的監管,由慈善法來規制網絡眾籌行為是當務之急。
一、網絡眾籌法律性質與合法性分析
(一)網絡眾籌的法律性質
慈善是捐贈人與受贈人之間的一種贈與法律關系。根據合同法的相關規定,捐贈人的贈與款是用于特定用途的,贈與款的管理人必須將贈與款用于特定用途,不能擅自改變用途,也不允許將捐贈款挪作個人消費。網絡募捐平臺不是慈善組織,不具備公開募捐資格,他們涉嫌越權發起眾籌項目,雖然目前鼓勵互聯網公司參與慈善行業,但互聯網公司只能以正規慈善組織的名義提供技術和平臺進行募捐,而不能以自己的名義進行募捐。而且,在慈善過程中,應該邀請第三方對資金的運作情況進行監督。個人的募捐活動只能由有資質的慈善組織發起和監督。但“輕松籌”等網絡平臺沒有相關的監管部門對捐款的使用進行監督,所以不具備募捐資格。通過“輕松籌”募集的資金在平臺收取一定比例的費用后直接匯入受助人的個人賬戶,而不是通過監管部門和慈善機構募集,完全是一種個人行為,而缺少監管的募集資金則是非法行為。
網絡公益眾籌活動涉及網絡眾籌平臺、活動項目的發起人、捐贈人、受益人和第三方資金托管平臺這五個權利義務主體。網絡公益眾籌平臺起到的是橋梁的作用,但我國法律對該平臺缺乏明確的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關于居間合同的規定,居間合同是居間人向委托人報告訂立合同的機會或者為訂立合同提供中介服務,委托人支付報酬的合同。規則上可以對公益與募捐的法律關系進行適配,網絡公益的募捐平臺類推于居間人的定位,而項目發起人承擔的就是委托人的角色,而居間合同當中涉及的第三方就是受益人或者捐贈人的地位。網絡公益眾籌平臺作為中介,在中介人的聯系下,項目的發起人與捐贈人簽署贈與合同,平臺從中抽取一定比例的籌集資金作為委托人的報酬,抽取的比例一般為最終所籌集資金總額的2%[1]。眾籌平臺與第三方資金托管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可以視為委托關系。第三方資金托管平臺負責收取委托人發起項目內所籌集的資金。
(二)網絡眾籌平臺合法性分析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鄭功成認為,如果是個人為了私人利益而求助,不會違法,因為法無禁止即可為,公眾在接收到這樣的求助信息后需要自己理性判斷并作出行動。但如果求助是假的,肯定要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等法律法規來進行處罰,有關人員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個人通過網絡平臺進行募捐行為的合法性問題一直是存在爭議并廣受關注。自2015年10月底《慈善法》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開始,一些人大代表就提議賦予個人公開展開募捐的權利,對此,有代表對此持相反意見,認為慈善法本身就沒有關于個人可以發起募捐的規定,這是由于立法目的本就不想規制個人的募捐行為,個人的行為從根本上說就不是慈善行為,因此不屬于慈善法的調整范圍,那么除了法律明文規定的慈善組織,其他組織和個人不應當享有公開募捐的權利。在這個問題上,十二屆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特別指出,個人向社會救助是其本身的權利,但是這并不是慈善活動或公益活動,不應當納入慈善法的調整范圍。
公開募捐行為之所以要受到慈善法的規制是因為慈善組織是在用募捐到的公眾的資金進行慈善活動,簡單來說是在用他人的錢在做善事,如果不加以規范監督的話,有違慈善活動的本意,所以在正式提交的草案中才給予慈善組織進行公開募捐的資質。那么對于個人或其他不具有募捐資質的慈善組織來說如果想要進行公開募捐的話只能通過與有相關資質的慈善組織進行合作,以具備資質的慈善組織的名義進行募捐,所募捐到的財物也應當由該慈善組織一并進行管理監督。以合作的方式間接賦予個人或其他組織募捐的權利,一方面能夠鼓勵社會公眾投身于公益事業;另一方面又能規范公開募捐行為,防止出現內部貪腐、資金使用灰色地帶的發生。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表示,個人為自身利益求助并不是違法行為,因為法律并不禁止,對于社會公眾而言,需要有理性判斷的能力,對于求助信息需要學會區分是非真假。個人的求助信息若為虛假信息,自然是要受到法律的懲罰,具體而言包括治安管理處罰法,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還要受到刑罰的處罰,承擔相應的責任。
二、網絡眾籌剩余款項安置問題面臨的困境
(一)網絡眾籌平臺求助缺乏定性
根據法律規定籌款主體應該是具有公募資質的公益組織,而其他組織和個人自然不具有募捐資格。因此,借助互聯網平套眾籌本質上當屬為個人求助行為。個人的求助行為目前只能由合同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進行規制,缺乏專門的立法。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針對某一領域缺乏專項立法并不意味一定要出臺該領域的法律,動輒立法的行為代價不只是我們在進行倡議時想得那么簡單,只有當該法律問題具有立法價值時才能啟動立法程序,如果能在其他的法律中對個人求助行為進行定性時,則不必進行專項立法。
(二)缺少對籌集款項監管規則
目前,頻頻發生在求救人因無法救助死亡時籌集人利用剩余的籌集款項從事其他活動,例如,用剩余款項為死者辦“法事”,更有甚者疑似用剩余善款搞旅游。對于股權類和綜合類的眾籌平臺可以由《私募股權眾籌融資管理辦法》和《私募股權眾籌管理辦法》進行約束,但是由于網絡平臺眾籌仍然屬于灰色地帶,因此對于剩余善款的安置問題自然也得不到相應的約束。
三、相關措施
(一)預留款項返還制度
當救助行為已經成功結束后,或發生其他特殊原因致使中斷籌集善款,又或者未達到籌集目標而失敗時,對于所籌集到的款項及剩余款項如何安置就成了問題[2]。筆者建議建立預留款項返還制度,在捐款匯入到求救人的銀行賬戶前,捐款人仍然擁有對該筆資金的所有權。平臺不能僅僅承擔中介的角色,還要對款項進行分類審核,最終由捐贈人來決定如何處置善款。若捐贈人愿意將款項用于其他同類項目,則善款由平臺來進行操作匯入其他同類項目,若捐贈人不同意那么也應當全部返還給所有權人。
(二)眾籌平臺應當公開所籌善款使用情況
具體而言網絡眾籌平臺應當加強對善款余額流向的監督,就治療進度公開披露,披露的信息應當及時有效,保障捐贈者的知情權。比如在信息公開期間治療費用發生減少,網絡平臺應當及時與院方核實醫療費用使用情況,核實后主動在平臺進行公示。此外網絡眾籌平臺還應當對籌集人的真實情況與身份進行詳細的審查,在確有向社會公共籌集的必要時才同意利用互聯網資源,從源頭上控制將籌集資金另作他用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