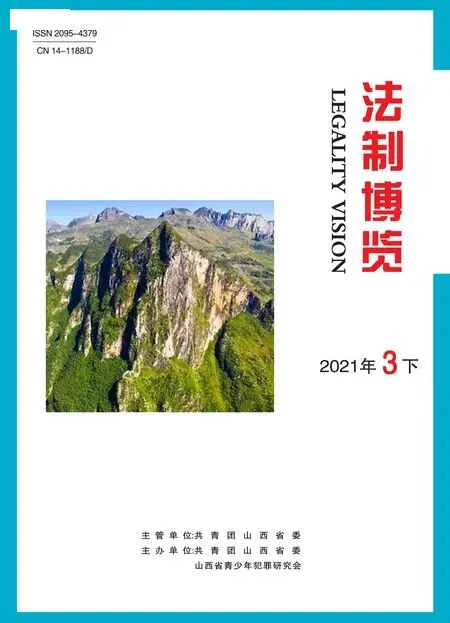將即時回憶工具應用于目擊者記憶探討
劉芷蕓
(1.中國政法大學,北京 100088;2.悉尼大學)
事實上,由于目擊者的記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暗示性,由于人的記憶不像錄像機,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靠,即時回憶在實際應用中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正如Huff,Rattner和Sagarin(1996)聲稱,不準確或虛假的目擊證詞可能是無罪嫌疑人定罪的主要原因,并解釋了從目擊證人獲得的證詞在許多法醫調查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Gabbert,Hope,& Fisher,2009)。具體來說,一方面,目擊者對事件的記憶可能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性別、年齡、訓練、教育水平或心理健康。
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目擊者對事件后信息的記憶首先容易迅速衰減,然后趨于平穩(Ebbinghaus,1885)[1],因此,犯罪發生后目擊者的證詞應盡快記錄。
目前,為了獲得更可靠的目擊證人陳述,在經過大量的實證檢驗后,常用的方法是認知訪談法。該技術是一種基于記憶檢索、一般認知、社會動力學和交流等各種原則的采訪協議(Fisher &Geiselman,1992)。實際上,根據羅納德、麗貝卡和雷(2011),在常規警察采訪中,大多數警察缺乏訓練尤其是采訪,采訪依靠他們的直覺和經驗,這可能會導致一些問題,包括:(a)和證人未能建立融洽的關系;(b)令人不安的目擊者的敘述;(c)問太多的帶有暗示性的問題。例如,“剛才發生了什么?”“那個行兇者是不是又高又壯?”或者“他穿的是黑外套嗎?”與之相比,CI由開放性和非誘導性問題組成,能夠引出更多信息而不降低準確性(Fisher,Geiselman,& Amador,1989;Fisher,Geiselman,Raymond,Jurkevich,& Warhaftig,1987;Mello & Fisher出版社,1996年;Wright &Holliday,2007年;關于CI文獻的評論,請參閱Bekerian和 Dennett,1993年;Fisher & McCauley出 版 社,1995年;Fisher & Schreiber,2007;Geiselman & Fisher,1997;Ko hnken,Milne,Memon,& Bull,1999;梅蒙 & 布爾,1991)。
然而,無論是傳統的警察面談還是CI,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警察資源有限的制約,導致在事件發生后的短時間內對每一個相關證人的面談機會都受到限制。換句話說,在調查的關鍵初期階段,由于可能會有多個證人在場,所以對警務人員來說,優先分配資源是一項挑戰。此外,由于證人、警察和每個案件的情況都不一樣,所以CI不能像機器人一樣,用同樣的方式采訪所有的證人。此外,當警察在應對犯罪事件,特別是一些暴力或恐怖主義犯罪時,最初他們承擔著比采訪證人更重要和緊迫的責任(例如,保護生命和財產,保護犯罪現場等)。
因此,在現實中,盡快約見證人的理想目標似乎是不現實的。在此基礎上,一些更復雜的即時回憶工具被創造出來,以滿足當前刑事司法的需要,例如,自我管理面談(Self-Administered Interview)和 iwitnessed。
一、即時回收工具的開發——SAI
SAI由 Gabbert、Hope 和 Fisher(2009)[2]開發,是CI的一種自我管理形式。換句話說,這個工具的目的是讓目擊者自己記錄下自己對事件的記憶。有關細節,證人提供一本由專業人士或心理學家科學設計的問題和說明小冊子,以方便證人立即檢索他們的記憶和描述事件細節。
為了測試SAI是否能更準確地回憶起目擊者的記憶,科學家們進行了一些實驗。更具體地說,在第1個實驗中,55名參與者(33名男性,22名女性,年齡在18到40歲之間)被隨機分配到三種情況中的一種,然后要求他們在觀看了一段犯罪錄像后敘述自己的記憶:(a)SAI條件(以小冊子的形式,包括五個部分);(b)自由回憶條件(鼓勵證人盡可能陳述和寫下他們所看到的情況);(c)CI條件(采訪者在技術上受過良好訓練)。結論從這項研究中,參與者確實產生了信息與質量明顯高于自由回憶(FR)條件,然而,SAI好像并沒有任何明顯的優勢(Fisher,et al,1987)。
實驗2的主要目的是考察SAI回憶工具在有延遲回憶的情況下,是否有能力在較長時間內保存和維持目擊者的記憶。這個實驗是非常有用和實用的,是由Fisher等人(1987)進行的。因為在真實的場景中,重述犯罪和報道細節之間的延遲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研究方法與實驗一有部分相似。42名參與者(10名男性,32名女性,年齡在30歲到60歲之間)被隨機分成兩組:SAI組和對照組。在觀看了一個模擬的犯罪事件后,前一組的參與者被要求在沒有任何時間限制的情況下完成一個SAI表格,然后在一周后做出安排,重述他們從之前觀看的犯罪事件中獲得的信息。對于后一組參與者,只要求他們在一周的間隔內自由地描述兩次犯罪事件的內容。最后,這個測試演示了與實驗1相同的推論。
上述兩個實驗都有其合理性。首先,參與者的年齡是不同的,有男性也有女性,這保證了實驗結果的代表性。隨后又設置了FR、CI、Control等條件,與SAI條件形成鮮明對比,得出更有說服力的結論。除此之外,所有的參與者都是單獨或以小組的形式參與實驗,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每個參與者的獨立性,而不讓他們的記憶或陳述受到他人的影響和干擾。
必須承認,實驗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例如,這兩個實驗都只做了一次。因此,實驗的結果可能會因為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例如,參與者的精神狀態,他們的壓力水平,或他們在間隔周的個人經歷等)而產生偶然性。此外,還可以嘗試擴大即時記憶回憶與第二次記憶回憶之間的間隔時間,或在相關的長時間內增加記憶回憶的次數。但總的來說,這兩個實驗的結果是科學的、可靠的。
一方面,毫無疑問,除了SAI能夠以最小的延遲從大量的目擊者那里獲得更高質量的證據外,它在其他方面也有優勢。首先,它解決了警方在調查證人時對警力資源的巨大需求的長期障礙。其次,SAI的提問和指示得到了規范,極大地避免了不良的面試做法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如不合理地使用引導問題或封閉性問題,以及對證人施加過多的壓力。最后,不僅要強調主要證人的證詞,而且要有機會搜集一些邊緣證人的證詞。畢竟那些邊緣目擊者可能掌握著關鍵的線索,所以他們不能被忽視。
另一方面,必須承認SAI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SAI表格要求手工填寫,因此,如果證人讀寫能力較低或不會說英語,該工具無法適應這類證人的需要。語言多樣性的難度似乎可以減輕通過面試的問題翻譯成不同語言的分類,盡管McPhee,帕特森和坎普(2014)聲稱,證人特別是一些不識字的喜歡給口語反映,而不是書面使用立即召回式的工具。SAI的另一個缺點是紙張格式不靈活,不能適應所有的犯罪。它更適用于一次性事件,而不適用于重復或正在發生的事件,尤其是欺凌、家庭暴力和性犯罪的受害者。
綜上所述,在現階段,CI還不能完全被SAI所取代。比較可取的方法是這兩種方法的結合。
二、一個更先進和新穎的即時召回工具——iwitnessed
鑒于CI或SAI的缺陷,一個新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序——“iwitnessed”面世。
首先,iWitness被設計用來搜集和保存目擊者的證據,使用引導回憶程序(例如,發生了什么;它發生在何時何地;在場的;;涉及車輛;是否武器,及任何被偷或損壞的物品)幫助目擊者或受害者記住事件的細節。同時,它可以用于任何類型的事件,從交通事故到恐怖主義,一次性或重復發生的事件,這彌補了SAI的劣勢。其次,用戶可以通過文字或圖像記錄他們的即興記憶和陳述。即使某人有書寫或打字障礙,他們仍然可以選擇音頻記錄盡可能詳細地描述事件從頭到尾的順序。之后,這些口頭證詞會自動轉化為文本。這個功能也非常有用和方便,因為每個證人都用自己的母語記錄證詞,提高了證詞的準確性和完整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每一頁都有一張清晰的地圖,可以在每一份報告上蓋上日期、時間和GPS位置的“章”。更重要的是,在安全性方面,iwitness是在其他即時召回工具之前推出的,它通過PIN得到了很好的保護。每次用戶重新輸入時,他們以前的客觀記錄都會被更新并私下存儲在電話中,并以PDF格式通過電子郵件發送,以確保證詞的機密性。我看到的最后一點是,手機已經成為最普遍的工具之一,以澳大利亞為例,絕大多數(84%)的國內公民擁有智能手機(德勤,2016)。同時,iwitness可以免費下載,從而使這個即時召回工具能夠向公眾普及。
當然,iwitness在某些方面還有待發展。目前,該應用程序僅提供英文版本,因此預計將提供多語言版本。另外兩項改進是根據法律使用這些證據,以及提供更多的心理幫助以降低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風險。
無論如何,我們所見證的可能是電子即時召回工具領域的游戲規則改變者,其優點大于缺點,其目前的不足也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被推廣。因此,應提倡廣泛應用。
三、結論
可以看出,從詞到言再到iwitness,這些即時回憶工具反映了目擊者記憶檢索的不斷進步和努力。CI是第一次嘗試通過啟發性的提問引導目擊者回憶更精確的記憶,但囿于警力資源和時間的限制;SAI是獨立犯罪采訪的第一個突破,但不能應用于所有類型的犯罪事件;iwitness是第一個成功探索電子即時回憶工具和鎖定目擊證人證詞,通過PIN在私人智能手機進行,但它還沒有實現進一步的目標,通過不同的語言下載,在目前階段。因此,考慮到我們上面討論的這些即時召回工具各自的優點和缺點,它們應該聯合使用。應該表揚的是,在每一項技術投入使用之前,人們更加重視大量的測試或實驗。總的來說,人們應該對新的科技持積極和接納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