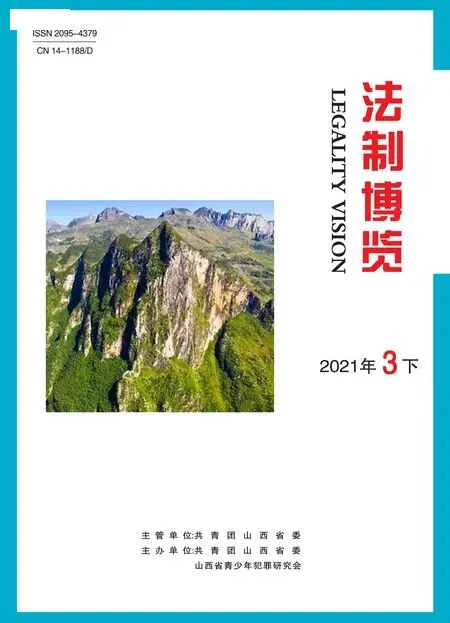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法律性質探析
魏良冠
(中共鄆城縣委黨校,山東 菏澤 274700)
一、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概述
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規定于《民法典》第七百二十六條、《城鎮房屋租賃合同解釋》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所謂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是指,當出租人(房屋所有人)出賣(或者拍賣、將房屋抵押、抵押權人實現抵押權)房屋時,該房屋的承租人享有的在同等條件下優先于第三人購買該房屋的權利。在一般情形下,房屋承租人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出租人相對處于優勢地位,為了促進物盡其用,同時體現保護社會弱勢群體的立法理念,法律以立法的形式設置了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制度。該優先購買權的行使必須同時符合以下條件:第一,僅限于房屋租賃合同,易言之,其他動產租賃合同中,承租人并不享有優先購買權;第二,僅限于出租人于租賃期限內出賣(或者拍賣、將房屋抵押、抵押權人實現抵押權)房屋的情形下,才符合優先購買權的行使條件;第三,承租人須以同等條件購買,所謂同等條件不僅包括價款,還包括付款期限、付款方式等;第四,受除斥期間限制,即承租人必須于除斥期間內行使該優先購買權,否則該權利即歸于消滅[2]。另外,《民法典》第七百二十六條第二款還規定了排除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兩種情形。
二、形成權說或附條件形成權說
長久以來,對于該權利的性質到底是屬于形成權還是請求權的爭論一直未停息過,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從總體而言,我國學者更多地傾向于將形成權的性質界定為形成權或附條件的形成權。依據形成權之特征,在具備法律規定的條件時,承租人僅僅依自己的意思表示,就可形成與房屋所有權人的買賣關系,而無須其同意[3]。例如,王利明教授認為:形成權說認為,在具備了法律規定的條件情況下,優先購買權人只憑自己的單方意思表示,而不問出賣人是否同意,即可與義務人之間形成買賣關系。另外,還有一種觀點,即附條件的形成權說,王澤鑒先生為其有力支持者,王澤鑒先生認為:優先購買權人得依一方之意思,形成以義務人出賣與第三人同等條為內容之契約,無須義務人之承諾,惟此項形成權附有停止條件,只有在義務人出賣標的物時,始得行使。筆者以為,雖然當我們對該權利的性質予以界定時,不能撇開當初設立這一制度時的立法初衷與美好愿景,因為,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制度恰恰是為了保障作為處于當今社會相對弱勢地位的承租人居住的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從而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由此,只有形成權說更符合立法初衷同時也更有利于該權利功能的最大限度發揮,但是,這一認定卻無疑有違背民事法律上的意思自治原則,況且,即使賦予承租人以形成權也未必能夠使承租人的權益得到更完善的保護。
三、債權說
債權作為一種最為典型的請求權,是指請求特定主體為特定行為(作為或不作為)的權利[4]。與形成權形成鮮明對比,債權說最大特點是具有明顯的相對性,只能是通過相對人的協助行為即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予以實現。因此,依照債權說之觀點,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行使僅僅能夠產生債權上的效力,無論如何不會涉及“第三人”,僅僅是及于房屋出賣人而已,當其優先購買權受到侵害時,也只能享有請求出租人賠償的請求權。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實質上屬于一種要約,若要取得房屋的最終所有權尚需要出賣人的承諾方可。所以,該權利完全符合債權的基本特征。在我國當前的學術理論界,對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問題最大的爭議之一無疑就是“債權說”,有部分學者主要是我國臺灣地區的學者認為,如果依照債權說之觀點,當房屋出租人出賣房屋時,承租人作為優先購買權權利人的主體僅僅具有請求與出賣人(出租人)優先訂立合同的權利,但是在長久以來的法律實踐案例當中不難發現,如果出賣人不同意出賣給承租人,即不作出承諾的話,那么權利人的優先購買權就不可能得到實現,這明顯不符合立法者的立法意圖,違背法律初衷。但是,筆者認為在與房屋買賣合同的并存關系當中,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只是一種法律明確規定的從權利,是從屬于房屋買賣合同關系的,不能因此就改變該優先購買權的債權之法律性質。
四、物權說
上文對于形成權說與請求權說的簡要辨析僅僅是揭示了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一層面紗,若要更加全面細致地對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做進一步的了解,尚需要對該權利展開進一步的研究與分析。在法律實務領域,對于該權利究竟是屬于物權還是債權的爭論,在近幾年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究其原因,一方面無非是因為伴隨著中國房屋租賃的驟熱與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件的激增,自然而然的將該問題推向了風口浪尖。另一方面,是因為對該權利性質的界定還直接關系到第三人的利害關系。筆者通過悉心查閱一系列相關問題資料知悉,在理論界,大凡支持物權說觀點的學者的理由不外乎有以下幾項:首先,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是法定權利,該權利的法定性與物權法所規定的物權法定原則是完全吻合的;其次,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優先性也表現為可以直接支配房屋,亦符合物權的根本屬性;最后,為了保障承租人權利的最終實現,完全有必要賦予該權利以對抗第三人之效力,而倘若將該權利的性質界定為物權的話,恰恰具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但是筆者以為將該權利界定為具有物權效力的權利尚值得商榷,下面,筆者做出自己的分析與判斷。首先,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法定性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物權的法定性,物權法定僅僅是指種類法定、內容法定、類型法定以及公示方法的法定性,因此,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雖然具有法定性,但不能僅憑此就認定該權利具有物權效力。其次,承租人對房屋的直接支配是基于其與出租人之間的租賃合同關系或共有關系或共同居住關系,而非該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本身,據此,不能認定其符合物權的直接支配性特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根據,依據2009年《城鎮房屋租賃合同解釋》第二十一條的規定,筆者以為,若將該權利的性質界定為具有物權效力的優先購買權頗有不妥之處。
五、混合效力說
除了上文對于該問題的相關論點以外,在學理界尚有一種觀點即混合效力說。比如,王利明教授認為: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一方面具有債權的效力,這一點無可置疑,另一方面也同時具有物權效力。只有賦予其一定的物權上的對抗效力,才能更有利于對承租人權利的保護。
六、筆者觀點
針對以上各家觀點,究其本質來說都有其合理之處,無非是各種觀點的側重點與著眼點不盡相同而已。例如,形成權說側重于保護房屋承租人的利益,同時注重保護關注該權利的最終實現,不過往往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房屋出租人選擇賣家的自主性。
筆者更傾向于債權說,理由在于,首先,眾所周知,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行使對象是房屋的出賣人,其行使效果在于使出賣人在出賣房屋時優先于第三人與承租人訂立房屋買賣合同,而絕非對其他任意與其無涉的第三人產生任何效力。其次,承租人雖然表面上表現為對房屋的占有、使用等,但不難理解也毫無疑問的是,這種占有使用等完全是基于房屋租賃關系而存在的應有之義,完全不同于物權中所表現出來的對物權客體的直接占有與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