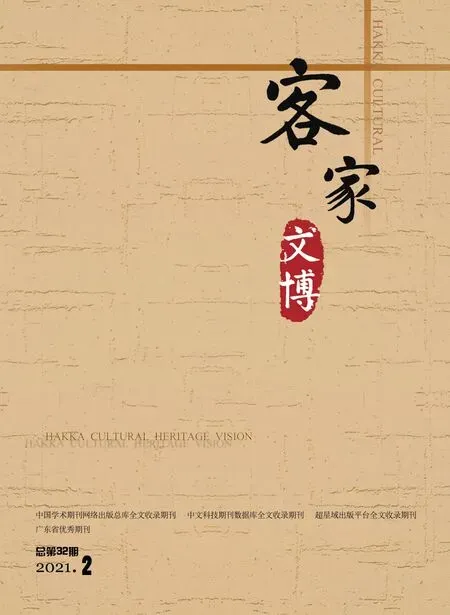縣區級文物建筑保護工作的幾點思考
祝 筍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文物保護工作的逐步重視,各地區也積極主動作為,結合當地實際情況,不斷創新文物工作思路和方法,文物保護和利用工作如火如荼地開展。這是文物保護工作進入新時期呈現出的新發展趨勢,即由靜態保護轉向動態活化,在利用中更好地進行保護。然而,新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必然面臨新問題。本文擬結合深圳市龍崗區不可移動文物保護與利用工作的實際情況,就一些具體問題闡述自己的看法,目的是引起學界對該類問題的關注,進而引發共同思考并努力尋求破解之道,最終實現更好地保護我國優秀文化遺產的奮斗目標。
一、討論范圍的界定
按照文物保護法的規定,不可移動文物是指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畫、近代現代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筑等。根據龍崗區文物實際情況,不可移動文物按類型可分為墓葬、遺址、建筑。本文的論述對象為不可移動文物中的古建筑類型。為便于行文,以下均稱為文物建筑。
二、文物建筑修繕問題
(一)“原材料”修繕原則的把握尺度
對于從事文物保護工作的人來說,文物修繕工作是再普通不過的一件事情。而要充分保留文物修繕后的歷史風貌及文物價值,按照一定的修繕原則進行施工顯得尤為必要。《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2015年修訂》中提出的保護原則有不改變原狀、真實性、完整性、最低限度干預、保護文化傳統、使用恰當的保護技術、防災減災[1]。《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2017年修正本)》第二十一條規定,“對不可移動文物進行修繕、保養、遷移,必須遵守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2]。有學者將“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簡要歸納為“四原”即原型制、原材料、原工藝、原做法[3]。在實際工作中,原型制、原工藝、原做法基本在現有體制和條件下可以實現,而且也有利于將一些傳統修繕工藝持久地傳承下去。但是針對原材料這一原則,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現實條件的制約,在實際操作層面還有可待商榷之處。
以龍崗區一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修繕為例予以闡釋。在整體修繕工程結束開展竣工驗收時,專家提出一個問題即在某些修繕部位沒有使用土坯磚,需要整改。按照該省保單位建造時使用的原材料要求,其土坯磚是用三合土制作而成,成分分別是純凈黃土、石灰、無鹽沙,有些為了增加磚的粘合度,會增加糯米汁和紅糖汁[4]。但現實情況是深圳在改革開放后迅速發展,基本農田用地幾乎都被用作城市建設,如果再使用純凈黃土作為修繕的原材料之一,恐怕會事與愿違。據向有關專業人士咨詢,該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整改工程共約需20000塊土坯磚,磚的規格是40厘米×22厘米×12厘米,如此計算累計約需200多立方的土方量。如果真的按照原材料這一原則開展修繕工作,不僅與深圳寸土寸金的現實情形不符,也與時下提倡綠色節約發展理念相背離。據悉土坯磚的制作,最后是在省外的一處農田里,按照一定配比,經過無數次實驗最終完成。
目前龍崗區共有182處文物建筑,其中面積在2000平以上的有70余座。按照每處文物修繕時約需10000塊土坯磚計算,累計需要700000塊,按前文所述測算,共計約需要7500多立方的土方量。如果都要從省外“進口”,不僅運輸成本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對于其他地區的生態環境也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壞。
由于原材料的修繕原則在實際操作層面存在困難,在修繕過程中還造成另一個問題,即施工單位為應付工程驗收,僅在墻體表面使用三合土,再往里面使用的就是普通的混凝土,往往還沒過一個雨季,墻體已經出現“剝離”的情況,這不僅產生一定的安全隱患,還會帶來后續不必要的工程整改麻煩,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重復投資。
基于上述情況,對于類似龍崗區這類處于城市快速發展階段的縣區級城市,在文物修繕工程中,對于某些原材料可否采取一些其他環保材料予以替代。這既是對現實的一種尊重,也是新技術融入文物修繕工作的必然發展趨勢。
(二)私有產權文物的修繕
1.擅自修繕
在內地絕大多數地區,文物建筑的產權多為公有,與之不同的是,龍崗區文物建筑幾乎全部為私有產權。很多文物是村民的祠堂,用于供奉祖先的牌位,村里很多重要的活動類似婚喪嫁娶等也在祠堂舉行。后代人生活富足后,出于對祖宗的尊敬與緬懷,大家通常會共同集資對祠堂進行修繕。在實際工作中,經常會遇到村民私自修繕祠堂的情況。文物部門一般會耐心跟村民進行溝通,讓他們按照文物保護法要求,把修繕方案報送審批,并嚴格按照審批的設計方案進行施工,但仍然存在村民不能理解的情況。這個祠堂是我們集體的,我們自己修自己的祠堂憑什么要向文物部門報批,為什么一定要按照政府部門批準的方案施工。當文物保護工作與公民物權相遇,公權益與私權益碰撞時,類似擅自修繕文物的問題就顯得尤為棘手。
2.私權益的補償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2017年修正本)》第二十一條規定,“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由所有人負責修繕、保養。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有損毀危險,所有人不具備修繕能力的,當地人民政府應當給予幫助”。私有產權文物的修繕義務由其所有人承擔,這固然與各地有限的財政資金和文物基數大的現狀分不開,但確實存在公民讓渡私權益卻沒有在法律層面得到適當補償的情況。文物保護是一項持久的工作,不可能指望產權所有人憑借一腔熱血持續對古建筑投資維修。另一方面產權人不具備修繕能力的,當地政府可以介入,這在現實中又會遇到兩個不同的問題。第一是產權人認為一旦由政府介入進行修繕,產權會發生變化,自己將逐漸失去主導權,因此對于政府出資修繕持抵觸情緒;第二是政府修繕后,為了確保政府財政資金使用的公益性,一般會要求古建筑適當對外開放,但產權人出于維護產權和自身私密的考量拒不向公眾開放。
三、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問題
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發表講話,習總書記指出,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如今,文物不僅活起來了,更火起來了。各地依托當地的文物資源,不斷創新工作理念,讓文物利用工作更好地服務一方經濟社會發展。但在看到工作成效的同時,很多共性問題也隨之出現,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利用方式有待進一步拓寬
2014年國家文物局印發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集中成片傳統村落鄉土建筑保護利用導則(試行)》,里面就鄉土建筑的利用方向進行了政策引導,“可用于村委會、村史館、圖書館、衛生所、老人活動中心、非遺展示中心等村莊公共服務設施”[5]。2017年11月,國家文物局印發《文物建筑開放導則(試行)》,其中第十二條對于活化利用方向進一步拓寬,按照使用功能劃分出五種類型:社區服務、文化展示、參觀游覽、經營服務、公益辦公[6]。但就目前全國文物建筑的活化利用案例,表現出來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利用方式略顯單一,多數用作博物館、展覽館等展覽展示場所,未來可以結合片區規劃嘗試更多利用方式。
(二)消防驗收問題
結合龍崗區文物保護利用工作和國家現行的政策法規,筆者發現,無論對文物建筑開展何種方式的利用,有一個問題總是無法回避,那就是消防審批。以利用文物建筑設立博物館為例,2014年7月31日,國家文物局印發《關于民辦博物館設立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設立民辦博物館需要提交“公安、消防部門出具的辦館場所安全驗收合格證明或消防備案受理憑證等文件”[7],省級文物部門制定的《廣東省博物館設立備案服務指南》中也明確要提供“消防部門出具的辦館場所的消防合格意見書”。目前這一行政審批事項“建設工程消防驗收”的審批權在住建部門。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2019年4月23日修正)第十三條規定[8],住建部門只負責現代建筑的消防驗收,文物建筑不在其審批事項范圍內。另一方面,文物部門也不具備消防驗收的審批權限,這就導致利用文物建筑設立博物館面臨一個無法破解的難題。由此推之,利用文物建筑開展任何對外開放的場所,都要先解決消防驗收這一問題。
四、文物建筑保護對策的思考
(一)健全文物保護工作的相關法律或制度
首先,針對修繕工作的原材料問題,究其原因是我國缺少文物修繕原則的更為細致的指導意見。目前業界修繕遵循的指引有文物保護法、《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2015年修訂》,同時參照國際上的適用準則,如《威尼斯憲章》、《保護世界文物和自然遺產公約》[9]等。上述制度性文件針對文物修繕的原則都較為宏觀,對于我國各地文物修繕中遇到的很多具體問題不具有實際指導性。為此,下一步國家層面應該盡快組織文物建筑修繕方面的專家和高級技師,針對我國目前文物修繕的實際情況,再進一步細化相關工作標準,各地區再參照制定符合本區域內的文物修繕指導意見。
其次,健全文物產權人私權益讓渡的補償機制。
這一問題,早有學者已經關注到。洪善倫在《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保護中的物權問題》[10]一文中,就從法律的專業視角提出對于文物建筑“私有公物”的情況應當建立一種補償機制。安國瑞在《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與利用須破解利益矛盾》中進一步指出,可嘗試的補償措施有政策優惠,榮譽獎勵,經營與稅收減免,遺產稅減免等。在一些農村地區,還出現了宅基地置換方式化解矛盾[11]。目前深圳市已出臺相關政策對非國有文物保護單位每年給予一定經濟補償,龍崗區也摸索出一條城市更新中文物保護的補償途徑,即采取容積率獎勵的方式來平衡文物產權人、城市更新主體和文物保護三方的利益。隨著文物活化利用工作的持續推進,今后可以在法律層面探索出更多有益、合理的補償方式。
再次,文物建筑活化利用中面臨的消防驗收問題
文物建筑消防問題學界探討的比較多,但多從消防安全的角度討論文物建筑如何配備相應消防設施,如何使用防火器材、如何提高產權人或使用人消防安全意識,目前尚未有學者從文物建筑活化利用方面,探討如何解決消防驗收行政審批的問題。文物活化利用工作是我國文物保護工作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面臨的一個新課題,在開展該項工作中遇到的消防驗收這一問題,也是我們遇到的一個新情況。文物建筑消防驗收目前是政策的一大空白,其間也有很多工作亟待解決,如文物建筑消防標準的制定、消防驗收行政審批事項歸口管理部門的確定,以及在文物建筑消防標準制定的過程中,是否要同步對文物修繕工程的相關管理規定進行調整,這些都需要多部門共同研究。
按照“管行業必須管安全”的工作原則,為了妥善做好文物建筑活化利用和文物建筑安全工作,國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在這一問題上主動與相關部門進行溝通,盡快出臺對應政策或指導意見,以實現合理利用和安全利用的雙贏目標。
(二)地方政府要提高文物活化利用工作的整體觀、全局觀
艾楠在《老建筑的保護與活化利用思考》中提出,要“樹立整體保護的理念”。除了保護文物建筑本體及其所依附的社會、自然環境外[12],還應盡可能將活化利用視野范圍進一步拓寬,甚至可以結合城市發展規劃來布局謀劃相關工作。因為文物工作不是孤立的,應該被列入地區發展一盤棋中統籌考慮。龍崗區于2017年開始啟動全區文物管控指引規劃研究,今年又結合各街道文物分布情況謀劃編制片區文物保護與利用規劃,這是經過多年文物工作實際情況摸索出的新的工作思路,只有這樣才能更好落實國家關于保護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指示精神,也只有這樣才能在城市發展中盡可能多地為后代保留一些印記,讓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們既能享受到現代設施的便利,也能看得見歷史,記得住鄉愁。
(三)加大文物保護工作的宣傳力度
如前文所提到的擅自修繕問題、產權人不同意由政府出資修繕的情況,與文物保護工作宣傳不到位是有很大關系的。要做好新時代的文物保護宣傳工作,就要有新時代的宣傳思維。第一,及早轉變工作思路,不斷創新宣傳方式。傳統的印制宣傳手冊要與線上宣傳有機結合,線上線下同步發力。還可以將文物保護工作與文藝創作、旅游工作融合發展,探索更多有效宣傳途徑。第二,廣泛發動宣傳力量,讓與基層群眾接觸較多的文化志愿者、社區工作人員等加入到宣傳隊伍,把國家最新政策、保護文物的歷史意義講給產權人聽。第三,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及時向公眾宣傳文物惠及群眾的實事,讓人們真正意識到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從而形成全員保護文物、支持文物活化利用的良好社會氛圍。
五、結語
我國文物建筑的活化利用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各區縣級也在工作中不斷摸索符合本地區實際情況的活化利用實施路徑。雖然面臨的問題各不相同,但隨著文物建筑活化利用工作經驗的不斷積累,總有一些共性問題亟需解決。作為基層文物工作者,我們要做的就是將一方的工作情況和相關思考及時與業界人士進行分享交流,共同尋求解決良方,從而更好地保護和傳承我國優秀物質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