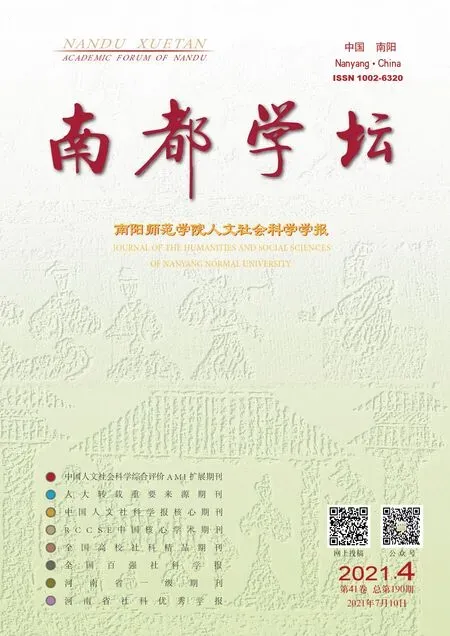非遺影像史記錄的轉型與實踐研究
劉 東 亮
(國家圖書館 社會教育部,北京 100081)
在現代性的語境下,目前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一般簡稱非遺,特定語境下不簡稱)影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闡釋其文化功能和社會意義。影像媒介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讓非遺最大化地實現了學術“本真性”的要求。1994年12月在日本通過的《奈良文件》肯定了本真性的意義所在,稱本真性是“定義、評估、保護和監控文化遺產的一項基本原則”[1]。不同于一般的影視創作,非遺影像記錄兼有學術倫理的價值導向和人文關懷的社會功能。影像技術手段的不斷提高,可以使非遺的“本體”更加直觀地展現出來,同時又能涵蓋物質媒介、文化空間、社會歷史環境等關聯內容。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非遺影像的記錄內容及方式進行研究。
一、非遺記錄方式的轉型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正式確定了“非遺”的概念與內涵,其中規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2]。
(一)口頭傳統的演述
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記錄,最初是口頭文本的講述,這是傳統社會存儲和建構人類文化與記憶的基本方式。對于沒有文字的族群來說,文化的傳承更多的是靠非物質的形態延續下來的。尤其對于一些人口較少的民族而言,口頭傳承就視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是由于民族文化的傳承大多是以口頭相傳的方式來記錄和保存。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它以人傳人、代傳代的媒介模式,將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人生禮儀、器樂、服飾等各種文化事項的記憶保存下來,并以“記憶內容—語言—形式邏輯”的方式完成自我價值的重新定位。
口頭傳承是“非遺”的一個重要載體和表現形式,口頭知識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有特定演述形式和傳統技藝實踐環境的知識,比如在民間文學中講一個故事,表演藝術中演唱一首民間歌曲等,這種講、唱都是一種在特定文化空間中的藝術表達形式,具有比較強的“規范性”。另外,編漁網、建房子、織繡、鑄造等技藝,是在具體勞作過程中傳下來的,屬于文化實踐中有關生存技能的知識。第二類是既有特定的演述形式,又有特定應用場合的知識。比如人生的重要儀式中,出生禮、成人禮、婚禮這些生命過渡儀式,都需要特定場合才能講述。其他比如少數民族有很多的禁忌和避諱,例如普米族巫師為病人舉行的“送替身”“退口舌”等儀式,必須在某一個特定的民俗文化事項里才能夠應用。第三類是一般性的知識,在人與人的交談、聊天等各種場合中講述的,不需要有明確的時間、場合、形式上的規定,因此具有普遍的適用性。
(二)影像書寫——新媒介的產生
在傳統的社會中,圖畫和圖形是一種有效的輔助性手段,可以彌補口頭傳播中因記憶和理解力而出現差異的缺陷。現代化技術的應用,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非遺的記錄方式。隨著攝影技術的興起,對于包括口頭傳承在內的非遺來說,其記錄手段無疑更加豐富了。影像記錄可以滿足非遺動態性保護的需求,“數字化音視頻設備能夠實現高保真、高清錄音與攝像,加之多機位拍攝技術、多媒體呈現技術等,非遺的動態性在數字資源中的實現程度越來越高”[3]。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拍攝的《佤族》《涼山彝族》《額爾古納河畔的鄂溫克人》等十幾部民族志影片,用鏡頭記錄了大量的少數民族生產生活場景、風俗習慣、節日儀式、宗教信仰等內容。依靠影像化的手段,可以真實地記錄下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把語言與文字無法完全展現的言外之意,如人的姿勢、神態、動作等記錄下來,使傳統非遺文化真正成為立體性的活態文獻。
二、非遺影像中的集體記憶和個體自覺
面對這些活態的文化藝術形式,需要進一步思考如何合理地利用視覺化的方式完整地展現出項目的核心價值,發揮影像傳媒的中介作用,拓寬非遺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從而以創新發展的方式賦予非遺更強的生命力。“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于影視媒介,則是可供開發的原材料、新的藝術創造的源泉,更不失為傳播傳統文化、張揚本土色彩、堅守‘文化版圖’的有效策略。”[4]在這一情況下,非遺的影視書寫有了雙向的發展策略。
(一)集體記憶:文化的標志物
1925年,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分析了人類的社會交往行為的基礎上,提出了“集體記憶”的概念。德國文化學者揚·阿斯曼和阿萊達·阿斯曼在記憶理論的研究中,進一步闡釋了交往記憶和文化記憶的命題。他們把“日常的集體記憶形式稱為交往記憶。它的最大特征是時間的有限性”[5]。實際上,這種交往記憶的典型例子就是非遺的代際傳承。集體的知識在歷史的演進中產生,但是它會隨著文化傳承者的消失而與現代社會產生某種斷裂,從而衍生出一種新的記憶。這也是我們強調非遺的影視記錄重視傳承人的原因,“人亡藝絕”現象的出現正是代際記憶機制發揮作用的重要表征之一。文化記憶正是在日常交往轉換為文化傳承的過程中實現的。它需要有固定的時空節點,通過一定的文化形式得以存在,并且還保留于節日、儀式、故事、歌曲、文化遺跡等各種載體之中。這些“記憶的形象”,通過系統化的集體實踐與互動得以延續和傳承。
傳說是最早的口頭敘事文學之一,如北京的永定河傳說是典型的地名傳說類型。這就牽涉到集體的場所記憶了。挪威建筑理論家諾伯格·舒爾茨建立了“建筑現象學”的理論,提出了“場所”的概念。在舒爾茨看來,場所是“人們通過與建筑環境的反復作用和復雜聯系之后,在記憶和情感中所形成的概念——特定的地點、特定的建筑與特定的人群相互積極作用并以有意義的方式聯系在一起的整體”[6]。現今關于永定河的傳說有30多個,其中大多與日常生活習慣有關。比如永定河邊栽楊柳樹的由來、如何治理永定河等,都是當地人以一種程式化的方式記憶歷史,在不斷講述傳說的過程中,附會上某一個權威人物或有意義的事跡,來闡釋傳說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并進一步強化這種集體性的認同。
(二)個體意識與文化自覺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質是“人”的知識和技能,它的核心是以人為主,所以,社會真正需要關注的是非遺所蘊含的人文精神與文化價值,充分喚醒非遺傳承人群體的文化自覺,形成大眾對于非遺保護重要性的共識。對于非遺的保護來說,在倡導傳承人“文化自覺”理念的基礎上,要充分保障傳承人的“文化權利”。具體來說,文化權利“需要考慮個人和群體所共同擁有的文化價值觀,這些個人和群體非常珍視它,而它又決定了他們的集體特征”[7]。在 2005年10月歐洲理事會通過的《法羅公約——文化遺產社會價值框架公約》中首次提出了“文化遺產權”的概念,其主要規定有“人人都有單獨或者集體享有享受文化遺產的權利以及為豐富文化遺產作出貢獻的權利;人人都有單獨或者集體承擔如同自身遺產一樣尊重其他文化遺產的義務”[8]。簡而言之,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保障傳承人自由開展文化活動,使其文化利益更好地得以滿足,同時在延續傳統的基礎上,實現文化的發展及個體的社會價值和意義。
但是面對快速發展的城市化建設,傳統文化的傳承面臨著巨大的困境,都市文化流失現象嚴重,逐漸呈空心化的趨勢。近年來,由于網絡和數字技術的普及,大眾媒介娛樂化的傾向也日益顯著。在這一過程中,激化了傳統與現代這兩者之間的文化沖突,加劇了都市文化的變異現象。由此使人們形成一種刻板的印象,認為非遺是一種“不合潮流”和“落后”的文化現象,這種心理暗示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非遺傳承人的文化焦慮感。
三、影像記錄非遺的工作方法
(一)對民間文學、表演藝術和傳統技藝實踐的記錄
口頭作品典藏。對民間文學與表演藝術影像記錄最主要的方式是錄制其代表性的作品。通俗來說,就是在傳統的表演場合里,以其應有的表演形式,對其代表作品進行記錄,重點是要體現出傳承人的語言特色、表演技巧、即興能力、互動能力,記錄與作品相關的信仰與禁忌等。對于傳統音樂的記錄,應選取傳統性、代表性的作品錄制,側重于他們的演唱、演奏技巧,所記錄的音樂作品保留了其傳統的表演環境和表演方式,并且要詳細記錄與音樂相關的儀式。對于傳統技藝實踐的記錄,具體的工作方法是全程記錄傳統技藝流程、制作步驟和方法。其中注意不要遺漏原材料及其加工方式、特殊工具的制作等內容,并且還可以記錄與之相關的口頭知識、傳統行規、師訓、行話等。
(二)對民俗活動的記錄
對于民俗活動進行影視學的記錄。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中完整記錄民俗活動從籌備、活動準備、活動呈現、活動結束及循環規則等的全過程。比如對于傳統年節及大型祭典等習俗,要記錄年節及祭典活動的全過程,重點記錄其中的核心儀式和藝術表達,如敬天、祭祖,這些都是嚴肅的精神活動,在儀式中的集體歌唱、舞蹈帶有娛樂表演的性質。對于民間信仰習俗,要完整記錄整個儀式的過程,如迎春、神誕、禳災、還愿等,以及傳承人對相關信仰儀式的解釋說明,并且還要著重記錄和民間信仰有關的口頭表述,如各類說辭、經文等內容。
對于生產生活習俗,則要完整記錄該項習俗的全部環節。記錄依托在生產生活習俗上的各種藝術形式,如窗上的剪紙,宴席上的祝詞、歌曲,勞作時的民歌、號子等。這種生產生活習俗是民族傳統觀念的外化,不僅強化了彼此之間的身份認同,而且規范了族群的道德倫理觀念,增強了民族的凝聚力。因此,對于民俗活動的記錄應該在當地的日常環境中進行。
(三)口述史訪問
口述史的工作方法被越來越多的學科所接納。因此口述史訪談工作基于相關的資料和信息的收集展開。對于文化事項的持有者和非遺傳承人的訪問,可以依據四級非遺傳承人名錄,以此為參考,確定訪談對象。因為大量的口頭傳統內容是分布在非遺十個大類里面,蘊含著民眾的生活傳統和經驗,具有非常豐富的文化內涵。因此,采訪者要熟悉傳承人所屬項目的歷史源流、發展變遷及傳承情況,初步編寫傳承人年表、傳承譜系表及訪談提綱。訪談結束以后需要將口述史訪談的內容轉錄、校對、編輯,做成口述文字稿。口述文字稿完成以后,請受訪人審稿并在紙質文本上簽字確認;如果有不予公開或暫時不予公布的部分,則在紙質文本上標記。
除此之外,還可以進行相關傳統村落的專題口述史訪問。口述史的方式可以有效彌補有些村落文字書寫的不足,將傳統的口頭遺產如農耕知識、祭祀儀式、節日廟會、婚喪習俗等內容由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社群和民族群眾講述或表演出來。
(四)已有文獻的收集
從圖書館的本位工作出發,對相關的社會組織、科研機構、新聞媒體和傳承人個人記錄的非遺影像資料進行收集,可以通過接受捐贈、購買、交換、復制、數字化、網絡下載等方式獲得相關的文獻。對于已獲取的各種類型的文獻資料,均應通過簽署《文獻收集與使用授權書》等方式明確使用權限,避免可能引起的法律糾紛。
四、結語
在當下的時代,我們對于非遺的影像記錄不能僅僅停留在項目這個單一主體上,而是應該回到其所處的文化環境之中,將視角轉向傳承人的動態實踐活動,以及與文化傳承者的集體互動等方面,在此基礎上將非遺的核心內容用影像記錄下來,從而形成對非遺的立體性保護。
非遺從來不是一種靜態的文化事項,它的發展和傳承與特定的文化環境緊密相關,所以在文化空間和社會互動中理解非遺就顯得尤為重要。非遺影像對于傳承人和項目的記錄,不是讓其作為“標本”保存,而是在動態的項目實踐和傳承教學中保持其發展的活力,同時了解這個項目的歷史文化、社會關系、未來前景等方面的內容,在此基礎上對非遺影像進行整體性的詮釋和理解。另外,非遺影像還應該堅持對人的描寫。傳承人所掌握的知識技能、表演藝術、節慶活動與人生儀禮,這些是非遺項目的核心所在,可以說人的實踐活動是非遺價值的集中體現。如何將傳承人頭腦中的知識與技藝外化出來,才是影像記錄的難題所在。
影像在對非遺項目和傳承人進行記錄之時,也應對人所處的現實生活環境以及項目背后的歷史文化進行深度闡釋。因為淺層次的文化記錄容易走向追求新鮮感、時效性與娛樂化的誤區。當我們把傳承人與一系列的文化事項聯系在一起時,就形成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文化研究文本。我們通過影像的方式對非遺進行分析和描寫的時候,就更容易闡釋其中的文化蘊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