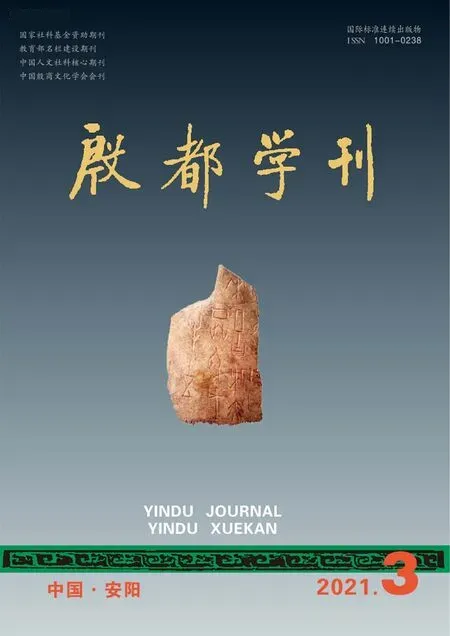甲骨學的發展與胡厚宣的巨大貢獻
王宇信
(中國社會科學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自1899年甲骨文發現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以甲骨文為代表的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因而“甲骨文研究取得顯著成就”。幾代學人的一批標志性成果,推動了120多年的甲骨學研究,經歷了發展道路上的“形成時期”(1899年-1928年),“發展時期”(1928年-1949年)和新中國成立后的“深入發展時期”(1949年-1978年)“全面深入發展時期”(1978年-1999年)。在甲骨百年輝煌中,進入新世紀“全面深入發展與弘揚時期”(2000年至今)再創輝煌的新階段。
享譽世界的甲骨學大師胡厚宣(1911年-1995年),85年的漫漫人生路上,有60多年與甲骨文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的“金字塔式”論文集《甲骨學商史論叢》(初、二、三集,以下簡稱“《論叢》”),把“形成時期”的甲骨學商史研究推向了“發展時期”的高峰。1949年以后,胡厚宣總編的《甲骨文合集》(13分冊,以下簡稱“《合集》”),為80多年來甲骨文發現和研究作了總結,是甲骨文“深入發展時期”古籍整理的最大成就,并為其后甲骨文“研究全面深入發展時期”奠定了堅實基礎。而胡厚宣主編的《甲骨文合集釋文》(以下簡稱“《合釋文》”),是從《合集》出發,展現了“全面深入發展時期”甲骨文字研究的最新水平,不僅為100年來的甲骨學研究增光添彩,而且為新世紀的再輝煌開了個好局。
一、一聲裂帛驚天下
胡厚宣在研究工作中,堅持“期能綜合歸納,分析疏通”全部甲骨文材料,因而他的170多種論著屢創新說,震聾發聵,在海內外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史學大師顧頡剛高度贊譽其深遠影響是“一聲裂帛驚天下”。
還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讀書時,胡厚宣就以《楚民族源于東方考》展露才華。1934年北大畢業后,就被傅斯年所長聘入史語所,旋即被派往安陽,投入了殷墟第十、第十一次的發掘工作,著名的牛鼎、鹿鼎和36捆銅矛,就出自他主持發掘的1004號大墓內。第十一次發掘以后,胡厚宣離開了考古工作,專與董作賓一起編《甲骨年表》,并投入第一至九次發掘所得6517版有字甲骨整理和《甲編》釋文的撰寫工作等。1936年7月,胡厚宣又參與了殷墟YH127甲骨窖藏坑17000多片的南京“室內發掘”工作。如此等等,這就使胡厚宣掌握了殷墟發掘最新信息和考古出土甲骨的全面材料。特別是“玩之尤為熟悉”的考古“所得大版,碎片近三萬”的最新甲骨材料(《論叢》初集序)。
在殷墟發掘工作的實踐中,使胡厚宣深刻認識到“研治古史,必當始自殷商,而甲骨文實為其最基本之材料”(1)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自序,齊魯大學國家研究所,1994年。。胡厚宣的甲骨學商史研究,“為避免斷章取義,穿鑿附會之嫌,則所見材料必多”。胡厚宣立志撰寫出與眾不同的《甲骨文字學》《古史新證》專著,大力搜集甲骨文等資料。“凡已出版之書,必設法購置;其未出版之材料,知其下落者,必輾轉設法,借拓鉤摹。國內國外公私所藏,雖一片不遺,雖千金莫惜。”(2)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自序。如此等等,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就是在史語所發掘所得甲骨文最新科學資料和廣泛搜集當時所能見到非科學發掘所得傳世甲骨文著錄43種和尚待刊布的99種拓本材料的基礎上,“對甲骨文字作一通盤總括之整理”完成的。
胡厚宣宏偉的甲骨學商史研究計劃,其“軔始”之作《論叢》(初、二、三集),是在抗日戰爭1937年7月全面爆發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的特殊時期完成的。期間,胡厚宣隨史語所“西遷”殷墟甲骨和文物,有在南京、長沙、昆明、宜賓李莊(胡厚宣去了成都)的長途跋涉、居無定所的流離之苦,也有日機轟炸掃射的不時竄擾和激流險灘、崇山峻嶺的險惡地形,但胡厚宣與同仁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充滿艱難和危險的征途上,堅持保護、研究國家文物,還見縫插針,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進行自己的研究。胡厚宣“居昆明三年,所成論文逾百萬字”,是在他“室家窘窒,衣食艱屯”的極端艱苦的生活條件下完成的。與此同時,胡厚宣參與整理殷墟發掘所得《甲編》《乙編》的工作也基本告竣,于是他應時在成都的齊魯大學顧頡剛之邀,去追求明義士藏置于齊魯大學的一批從未面世的甲骨去了。胡厚宣“在授課之余,方期以最大努力,在最短期內”,對掌握的大批甲骨材料再“發掘”整理研究。1942年夏季以后,經增訂修改,“乃略據舊作,每成新編”,就基本上完成了《論叢》初集和二集、三集的集稿工作,并由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1944年出版了初集,1945年出版了二集、三集。
《論叢》不僅運用甲骨學商史材料齊備,而且還引用了不少為當時研究者極為罕見的殷墟科學發掘所得甲骨文新資料。因而可以說,《論叢》(初、二、三集)也是一部集當時甲骨文之大成的巨著。正是在如此齊備研究材料的基礎上,《論叢》一書拓寬了甲骨學商史的研究范圍,不僅論及了商代的農業生產,還探索了商代上層建筑,諸如土建制度、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天神崇拜等方面。不僅如此,還對商代的文化和天文歷法、氣象和醫學等方面也作了深入研究、考辨。書中不少發前之所未發的真知灼見和糾謬主新的發明,亦是從大量甲骨文材料的分析、梳理中得出的。因而《論叢》不少篇章立論精當,歷時常新,直到今天仍有重要參考價值。《論叢》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學者推崇此書“不是通史,但幾乎包含了殷代史的主要方向,確可稱為殷代研究的最高峰”,把“發掘時期”的甲骨學商史研究推向最高峰。這部“斯學空前的金字塔式論文集”(3)白川靜:《胡厚宣氏的商史研究》下篇,《立命館文學》第103號,1953年。,獲教育部“著作發明二等獎”(獎金為8000大洋),為抗日戰爭期間的甲骨學商史研究贏得了榮譽。
二、集大成著錄《甲骨文合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胡厚宣在歡呼“舊的時代死去了”的同時,下決心“站在新的立場,用新的觀點方法,對甲骨文進行一番新的研究”(4)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序,中華書局,1952年。。他努力學習和自覺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并認真地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指導自己的甲骨文研究,寫出了《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人祭》(上、下)等知名論作,從而把《論叢》的研究水平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
早年為追求甲骨文而來殷墟,并與殷墟發掘同仁共歷保護甲骨文等“國寶西遷”路上,艱辛的胡厚宣,為追求從未見過的一批甲骨文的蹤跡,又離別朝夕與共的殷墟考古“兄弟”,另辟新途而去。胡厚宣為寫好《論叢》,千方百計搜集摹記甲骨文材料熱度不減,這就使他坐擁書城,并掌握了分藏海內外傳世甲骨文的全面訊息,也為他1956年承擔大型甲骨文資料匯編《甲骨文合集》總編輯重任打下了基礎。
1956年,《甲骨文合集》列入國家科學發展規劃。1959年,編纂工作正式啟動。郭沫若任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協助郭沫若處理日常編纂工作及相關具體事務。編纂工作時停時輟,直至1937年到編輯成員從河南息縣“五·七”干校畢業回京后,《合集》編輯工作才再次啟動。在胡厚宣總編輯的帶領下,編輯組成員齊心協力,努力奪回已失去的十年大好時光。1978年底,《合集》的全書圖版稿基本完成,并開始了13分冊的陸續印制工作。從1978年至1982年,全書共13分冊,收入甲骨41956版,至此《合集》正式出齊。
《甲骨文合集》從1959年啟動,到1982年全書出版完成,經歷了20多個春秋。工作中有艱苦尋覓的磨難,也有如歌歲月的豐收。《合集》是集八十多年來甲骨文研究之大成的著錄,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學者們大規模集中、整理和利用甲骨文材料取得的豐碩成果,今天也成為甲骨學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繼往開來,為甲骨學“深入發展時期”做了總結,并為已經開始的“全面深入發展時期”的研究和新世紀甲骨學研究的再輝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合集》總編輯胡厚宣,為空前規模的甲骨文資料收集工作,奉獻了全部心力、智慧和經驗,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他早在《論叢》的撰著過程中,繼其后在1945年抗戰勝利后兩次南北之行中,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幾次假期各地尋訪中,收得不少甲骨文資料,同時也積累了許多搜集甲骨的經驗及掌握了收藏信息、藏家人脈。這就使胡厚宣在為編纂《合集》搜集甲骨文材料時,可以輕車熟路、老馬識途地帶領(或指派)編輯組成員上路,在1959-1960年、1962年、1965年、1973年和1974年前后幾次,分若干批,南征北戰,奔走于大河上下,赴全國各地尋訪、收集、照拓甲骨文,終于成功地完成了史無前例的甲骨文資料大規模集中整理的工作,為《合集》的編纂奠定了基礎。而胡厚宣長期在實踐中積累的收藏經驗和掌握的藏品信息及人脈,為甲骨文材料的集中做出了方向性的保障和持續性貢獻。故我們把胡厚宣《合集》1959年大規模搜集資料前的幾個階段與《合集》編纂聯系起來,稱1928年至1940年撰著《論叢》搜集資料時期為《合集》大規模搜集甲骨文材料的“前景”;而1945年以后撰著“戰后四書”搜集材料時期為胡厚宣《合集》搜集材料的“序幕”;而1949年后出版《甲骨續存》搜集材料時期,是胡厚宣總編輯《合集》這部大型甲骨文資料著錄的“預演”。因此1959年《合集》編纂工作啟動后,經驗豐富的總編輯胡厚宣順藤摸瓜,出色地完成郭沫若交給他“一定盡可能把材料搜集齊全”的任務。
在帶領編輯組進行大規模的科學整理甲骨文材料時,胡厚宣首先把當時已出版的海內外180多種著錄書收齊,再廣泛調查收集分藏各地的甲骨實物和拓片(或照相)。同時,盡力搜集流散海外的甲骨、拓片或照片。在編輯成書時,盡可能采用原骨的新拓本,并把一骨的正反集中,還進行了大規模的校重、辨偽、綴合、選片、集中同文和對甲骨片進行分期分類等一系列煩瑣而細致的整理研究工作。僅就著錄書統計,共校出重片6千多片,重片次達1.4萬之多。可以說,這是80多年來空前規模的“對舊著錄進行了一次清查”。此外,《合集》編輯還非常注意對所搜集材料的斷片綴合,共收入綴合版2千多,其成果超過了前人,從而“使不少看來并無太大意義的殘碎甲骨,在復原后產生了使人意想不到的學術價值”。
如此等等,胡厚宣為了編纂《合集》,或事必躬親,率先垂范,或事無巨細,規劃指點,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智慧。《合集》1982年出齊以后,付出了大量心血的智慧。《合集》1982年出齊以后,使研究資料匱乏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觀,從而使更多有志于弘揚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學人,向絕學、冷門學科甲骨文研究提出了挑戰。集大成式《合集》,為甲骨文“深入發展時期”的研究作了總結,并繼往開來,為“全面深入發展時期”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部里程碑式的《合集》,以它在甲骨學發展史上愈益凸顯的重量地位和重大影響,得到黨和國家的多次表彰,并獲得了吳玉章獎、古籍整理獎、中國社科院獎和政府出版等國家部委級多個獎項。
三、《合集釋文》是新百年再輝煌的開局巨獻
在1978年《合集》編輯工作基本結稿以后,年逾古稀的胡厚宣壯心不已,表示“一定要抓緊時間,完成郭老讓我具體負責主持編纂的《甲骨文合集》及釋文等尚未完成的工作”。未雨綢繆,在《合集》第一批第2、3、4、5、6、7分冊已于1980年前陸續出版面市,而第二批第1、8、9、10、11、12、13分冊至1982年也全部陸續出齊的過程中,胡厚宣主編的《甲骨文合集釋文》的撰著就陸續啟動了。
郭沫若主編的《合集》,為研究者提供了80年出土甲骨文的最完備資料。而研究者利用時,再配以更準確釋文與原版互相發明并相得益彰,將更增強材料不可置疑的可信性。不僅如此,《合集》原片對甲骨學家們來說,是十分必要的一手材料,但對多學科學者來說,因不懂甲骨文,從《合集》中發掘甲骨文傳承的優秀傳統文化基調,就是十分困難的事。因此,出版一部適應多學科者需要的《合集釋文》,也是甲骨文的精華得以實現創造性轉化,助力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發展的需要。
為《合集》41956版甲骨一一作出準確的釋文,是非常艱巨而浩大的世紀工程,主編胡厚宣知難而上,他胸有成竹,有步驟、有計劃地把《釋文》研究工作推向前進。
首先,是需要解決《釋文》各分冊的撰稿者問題。胡厚宣相信群眾,相信《合集》編纂的完成,會使一批青年人也成長起來。因此胡厚宣把印制完成的和還在印制中的《合集》各分冊,先后交給有關學者負責釋文的撰著,并要求他們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并吸收近年最新成就。
其次,經多人之手并在較長時間完成的規劃較大的《合集》釋文,遇到了最大、最復雜,也是最困難的問題,即如何達到全書(十三冊)文字和體例的統一。主編胡厚宣指揮若定,有條不紊地安排下述幾個步驟,就使全書在文字和體例方面實現了“大一統”。
一、初稿的撰著。集思廣益并分工負責,由學者各負其責,完成承擔的《合集》分冊釋文任務。1980年8月5日,胡厚宣召開全體參編人員會議,對已印出或印制中的各分冊作了分工,并對每冊“初稿”完成后,學者的“初稿”交換校對,即“互校”也作出了安排。會上,胡厚宣介紹推薦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并反復強調:全書釋文的體例和文字的隸定,要盡量保持全書的一致性。在充分討論和研究的基礎上,王宇信受胡厚宣之托,起草了“《合集釋文》體例(暫行)”,從而使“釋文”的撰著者,明確自己在《釋文》初稿的寫作上,應該遵循的原則;由于《合集》各冊殘片很多,且大小不一,因而在撰著《釋文》初稿時,經常出現很多預想不到的問題或困難。因此,胡厚宣在此基礎上,又于1981年10月委托齊文心擬定了“《釋文》之補充體制”,主要就全書的釋文標點、殘文處理等具體操作方面,對前“《合集釋文》體例(暫行)”作了進一步補充,此外,對“文字的隸定”也作出更具體的規定。對辭條中常遇到的“貞人”名,作有“貞人隸定表”(58人),供統一全書貞人名號之用。1982年8月,《合集》第二批分冊也印制出齊,胡厚宣馬不停蹄,在隨后的8月28日召開全體會議,檢查了各冊釋文的進度并作出其他事項決定。根據會議討論和作出的一些決定,王宇信受命起草了“《釋文》計劃(草案)”,要求各冊“釋文”初稿務于1983年年底交稿。其后,胡厚宣在1983年2月的全體人員例會上,再次檢查了釋文的進度,并對原來的一些規定做了補充修訂。王宇信執筆的“釋文組83年2月1日工作例會紀要”,上報歷史所并分發與會者,“供工作參考”,以保障“在釋文工作中,繼續貫徹保證質量的原則”。
二、互校。就是二位學者互相校對所做的“初稿”。互校完后,有爭議處經商定,兩人并達成共識,再改訂后,保持全稿齊、清,即為“初定稿”。1983年3月底,部分學者完成了第一批印出的《合集》釋文初稿(1984年底,第二批印制出版的各分冊《釋文》初稿也基本完成)。胡厚宣就不失時機地在1983年4月召開全體人員例會,“就下一階段釋文初稿‘互校’及時間安排進行了討論”,并對“釋文行文格式”重申并補充七條規定。要求在下一階段的研究工作中,必須認真閱讀并熟悉“有關各次會議所定條例(或紀要)”“在整理稿子時,嚴格實踐之”。胡厚宣還安排了下一階段“自行校對、統一格式、互校、初定稿、整理”等工作,要求“互校”工作在5月底完成。所謂“整理”,即“互校”后,初稿修改后的散亂不清處,要自行謄清重抄,以保持卷面清楚。胡厚宣要求7月交出經“互校”的釋文“初定稿”,以便全書“初定稿”的總審校工作啟動。就在這次會議上,決定了“在一般情況下,稿子處理各項規定不再變動,以保持連續性、統一性”。盡管如此,在各冊釋文的撰著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問題,還是一些常用字的統一問題。王宇信又據學者的意見,草擬了一份“常用字(136個)隸定表”,在1984年5月9日胡厚宣出席的例會上,進行充分討論、研究、確定。胡厚宣責成王宇信再擬“常用字隸定及總審校格式參考(初定稿)”,供學者進一步校定各冊“初定稿”及總審校“初定稿”之用。經胡厚宣的周密安排,《合集釋文》初定稿大規模精益求精的研究工作終于在1984年底基本結束。
三、初定稿的總審校。1985年,《釋文》主編胡厚宣把總審校《合集釋文》初定稿的任務,交“釋文組”組長王宇信、楊升南。雖然胡厚宣召開的多次決策性會議上,對《釋文》全書的用字、格式,甚至標點等等,都作有明確的規定。并形成多份“紀要”和“體例”等,用于《合集釋文》初稿和初定稿撰著和審定的整個過程中。但不同人作的釋文初稿,還是“百花齊放”,對辭條的理解總是因人而異,而行文用字也總是各不相同。雖然初稿經過“互校”,但初定稿只是把雙方的初稿,作了表面浮光掠影的修正,而全部13冊定稿仍然缺乏一以貫之的文字修定和體例的貫通,因而與“互校”前的初稿面貌,還是大體相同。因此,對初定稿進行一次總審校,即以壯士斷腕的氣魄,把初定稿中不符合歷次會議精神和紀要、條例規定之處一一刪削、改定、調整、補充,從而完成全書釋文初定稿的通稿任務就十分必要。
由于胡厚宣年事已高(年逾80歲),再不能像指導撰著《合集釋文》初稿和互校后初定稿時那樣事必躬親,一頁頁地審校初定稿了。王宇信、楊升南毅然承擔了總審校釋文初定稿的任務。二人依據歷次會議決議和會后整理發放的“紀要”“參考”“暫行辦法”等,從文字到體例等必須貫徹體現在《合集釋文》初定稿的總審校中。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則電話請教胡厚宣,或他來所時當面確定。對確定的常見字、疑難字等和特殊情況的處理,隨時記錄在案,供其后總審校參考,以保障全書文字和再出現此類現象的統一。王宇信、楊升南二位學者,將釋文“初定稿”上的每一條釋文及每一條上的每一字與《合集》上的對應辭條一一互校。互相勘校后,確定初定稿上的文字,再精心推敲、確定其標點符號,甚至動用《合集》珍貴的原稿與初定稿的文字筆劃勘校確定。如此等等,雖然總審校的工作煩瑣,但我們都耐心細致。雖然平淡枯燥,但也為總審校初定稿的速度加快而高興,也為從《合集》與初定稿互校的字里行間有新發現和新想法而拍手稱快。就是這樣,從1985年5月6日起至1987年10月21日,《合集釋文》初定稿的總審校終于完成!在這二年零八個月的總審校《合集釋文》初定稿的過程中,我們認真貫徹、執行了胡厚宣為保障《合集釋文》文稿的質量,在大會上提出的一系列原則和方向,及會議形成的一系列“簡報”等文件,是我們在總審校過程中不時遵循的方向。特別是胡厚宣在《釋文》總審校過程中,反復要求我們要反映當代研究的最新成果等,這就使總審校后的定稿,站在“全面深入發展時期”古文字研究的最前沿。
為使《合集釋文》經過總審校后的定稿早日出版,胡厚宣又解決了出版機構和出版資助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決定影印出版《合集釋文》。發稿排版,即相當于書法家韓樹績繕寫《合集釋文》全書的影印稿過程。自1992年10月28日1994年11月25日,全書繕寫影印稿2059頁全部完成,王宇信、楊升南又把影印稿再總審校一遍,這相當于排版印書的三校后“合紅”,就只待下廠成書了。胡厚宣為《合集釋文》出版諸事宜,又做出了新的貢獻。在付印之前,他還在關心著《合集釋文》的質量,1994年春去臺灣訪問前夕,還叮囑王宇信“待從臺灣回來,我看一遍彩印稿后再付印!”但從臺灣回來后,疾勞成疾,再也沒提要看影印稿之事,因病在1994年秋住進了醫院。在病情稍好時,就急著要回家工作,他還有《合集釋文》要出版……1995年4月14日,胡厚宣出院回家,精神很好,信心十足地對看望他的學生們說:“終于回家了,我還有好多事要做呢……”。天有不測風云,1995年5月16日,這位一直念念不忘工作,不忘甲骨的殷商史甲骨學大師,突然發病,駕鶴西歸,永遠離開了我們……
胡厚宣在世時,總審校后的《合集釋文》稿,已經繕寫成“影印稿”,相當于排版印刷書籍的三校,只待機器開動,就可見到印出的《合集釋文》面世,雖然胡厚宣生前沒有見到傾注了他大量心力的《合集釋文》出版,但《合集釋文》工作的每一步推進,都離不開胡厚宣策劃、指揮、安排、運作和推動。
胡厚宣主編的《合集釋文》,是郭沫若主編《合集》的繼續,為海內外學者深入研究甲骨文所蘊含的歷史思想和文化價值作出了新的貢獻。此書在1999年紀念甲骨文發現100周年大會上隆重推出,堪為甲骨文“全面深入發展時期”的總結,也是胡厚宣獻給新世紀甲骨學研究再輝煌的開局巨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