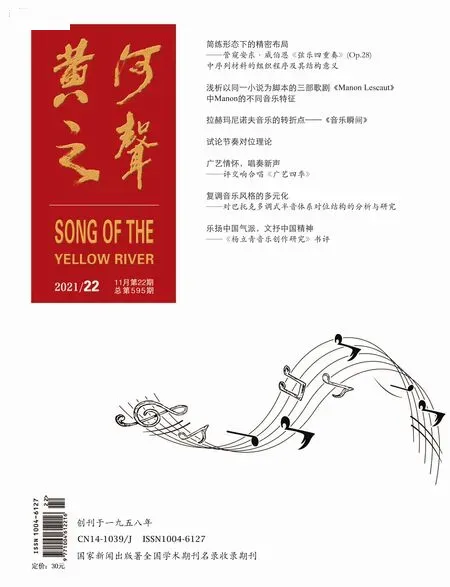中國鋼琴音樂作品的民族化特征研究
胡 敏
自十九世紀末鋼琴音樂在中國大地上廣泛傳播開來不久,它就與中國民族音樂結下了不解的藝術情緣。在融會中西音樂藝術思維和創作技法的基礎上,一代代中國作曲家奮發砥礪,創作出一系列鋼琴音樂經典名作,逐步構建起了中國風格鋼琴音樂作品體系。而在下文中,就將開宗明義闡釋中國風格鋼琴作品“中西合璧”的內涵與創作特征,并援引當代中國風格鋼琴名家經典名作為例,來有力地論證這一觀點。
一、中國鋼琴作品民族化的內涵
1840年之后,隨著清王朝閉關鎖國的大門被英法等國的堅船利炮轟開以及大量租界的建立,西洋鋼琴音樂也在中華大地上廣泛傳播開來,并受到中國社會上流階層與文化人士的熱愛。至一戰前后,像趙元任、蕭友梅等音樂藝術先驅已開始引入民族傳統曲目或旋律嘗試創作具有中國藝術血統的鋼琴作品。而1934年正就讀于上海國立音專的賀綠汀憑借一首《牧童短笛》摘得俄籍鋼琴家齊爾品“征求中國風味鋼琴作品”比賽桂冠之后,典型意義上的中國風格鋼琴曲創作就正式拉開了帷幕。經過近90年的藝壇耕耘,中國作曲家推出了諸如《花鼓》《夕陽簫鼓》《百鳥朝鳳》《梅花三弄》《瀏陽河》等經典名作,在用鋼琴這件“舶來”樂器傳達中國民族音樂情韻美感的同時,也憑借獨特的風格在世界樂壇上為中國鋼琴音樂爭得了應有的一席之地。
提到近現代中國鋼琴作品,人們的耳畔往往會回響起諸如《黃河鋼琴協奏曲》《夕陽簫鼓》《百鳥朝鳳》《瀏陽河》等一系列經典名作那耳熟能詳的樂音。這些作品不僅耳熟能詳,而且親切可感,令一代代聽眾喜聞樂見,余音難忘。這也很容易造就一種觀念,即:近現代中國鋼琴作品所表現出來的風格,是一種民族化的風格。中國風格鋼琴音樂所呈現出的獨特美感,是一種民族音樂的情韻之美。
這樣的論斷,雖然看上去貌似沒有問題,但卻容易令人產生以偏概全的誤解。誠然,近90年來中國鋼琴音樂的創作歷程,是一段不懈融合民族音樂元素、藝術思維和寫作手法的創新、變革、發展歷程。然而我們也應注意到,這里所提到的“融合”,是民族音樂元素、民族音樂藝術思維和寫作手法對于西洋音樂創作技法體系的融合。如果脫離了自傳入中國之際就已“與生俱來”的西洋鋼琴音樂創作思維和技法體系,那么中國風格鋼琴音樂的創作同樣難免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有鑒于此,本文認為,中國風格鋼琴作品所表現出的民族化特征,從本質上來說可以歸結為中國民族音樂藝術思維、寫作手法、音樂元素同西洋鋼琴音樂創作思維和技法體系之間的對接與融合。在這個基礎上推陳出新,創作出了具有“中西合璧”特點的鋼琴音樂作品,才足以標志著中國風格鋼琴音樂逐步走向成熟。所以,藝術思維與寫作技法這兩個層面的“中西合璧”,既足以全面概括中國風格鋼琴作品民族化、本土化的內在涵義,也足以準確地描述其外在表現特征。下面,本文就以儲望華、王建中、但昭義這三位中國鋼琴作曲名家的經典作品為例,來論證中國風格鋼琴作品“中西合璧”的內涵與民族化創新特征。
二、中國鋼琴作品中民族化技法的不同呈現形式
(一)儲望華鋼琴作品民族化創作技法
儲望華是一位多產的作曲家,其代表作《黃河鋼琴協奏曲》在我國當代音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在鋼琴獨奏作品方面,憑借改編曲《二泉映月》《翻身的日子》等著名作品,儲望華也足以引起鋼琴習練者的高度重視。朱工一教授曾將儲望華鋼琴音樂創作風格評價為“喜歡用裝飾音,模仿民間音樂的韻味”。這也為我們探究儲望華鋼琴作品中民族化技法的呈現方式指明了方向。
的確,儲望華的鋼琴作品善于運用各種寫作手法來模擬多種民族樂器的演奏技法和音響效果。比如,在鋼琴改編曲《翻身的日子》第1到11小節之間,左手部分作者安排了一系列空五度和弦八度形式的平行進行,借以模仿民族打擊樂——鼓聲的音響效果。而在該曲第16到20小節之間,鋼琴右手部分又表現為一系列由升B和升C音構成的小二度和聲音程平行進行。這兩個變音與民族樂器板胡的音高相似,它們組成小二度和聲音程所帶來的不協和音響效果恰到好處地模擬了板胡下滑音的音色特征。之后,在《翻身的日子》第84至88小節之間的左手部分,作曲家設置了三個前倚音。它們與主音之間或是小二度,或是大二度,或是小三度,這就在表現民族樂器管子(篳篥)低沉音色的同時模擬了其富有諧趣的滑音奏法效果,為樂曲的音樂織體平添了幾份詼諧的情感氛圍。
在儲望華的另一首成名作鋼琴改編曲《二泉映月》中,模仿民族樂器二胡演奏方法和音色特征的鋼琴音樂寫作手法也表現得較為突出。比如該曲第4小節右手部分首拍,作曲家在升B音前設置了一個較其低五度的前倚音G。這就比較形象地模擬了民族樂器二胡上滑音技法的音響效果,給聽眾帶來了親切之感。同樣是這一小節第三拍處以三十二分音符節奏型展開的七連音,則又模仿了二胡顫弓技法的音響效果。然而,同是對于二胡顫弓技法,作曲家在《二泉映月》中卻又并非單純以同一種寫作手法來表現。比如該曲第33小節右手部分,對于第三拍的八分音符C音,則是采用了波音的技法來表現二胡的顫弓音效,同樣收獲了別開生面的表現效果。
所以,綜合上文的論述來看,作曲家儲望華在創作中國風格鋼琴作品時,其最為突出的特點是采用多種鋼琴音樂寫作手法來模擬各種民族樂器的演奏技法和音響效果。然而,通過分析上文列舉的多個案例,也不難歸納出儲望華用來模擬各種民族樂器音響效果的兩種基本藝術思維方式:其一是通過對西洋音樂和弦構成進行民族化的變通處理來模仿民族樂器的特定音響效果。比如前述《翻身的日子》中所出現的空五度和弦八度形式就是對西洋音樂中三度疊置和弦的變通處理;其二是運用西洋音樂成熟的寫作技法來巧妙模擬民族樂器演奏技法及其音響效果。但無論是哪種情況,都體現了民族化音樂思維與西洋音樂寫作技法的對接與融合。而這,正是足以體現中國鋼琴作品民族化創作特征之處。
(二)王建中鋼琴作品民族化創作技法
在我國當代鋼琴創作發展歷程中,王建中是一位不容忽視的作曲大家。憑借《百鳥朝鳳》《梅花三弄》《瀏陽河》《云南民歌五首》等民族器樂或民歌鋼琴改編曲,王建中在我國當代鋼琴樂壇上書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上述這些鋼琴曲目,也成為了近幾十年來盛演不衰的“常青藤”式作品。
若從民族化藝術思維和技法運用的角度去考察則會發現,王建中鋼琴作品在五聲縱合性和弦運用、民族調式布局和轉換、借鑒民族化旋律發展方法等諸多領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藝術成就。然而受限于本部分的篇幅,我們僅從五聲縱合性和弦運用這一角度入手,對王建中鋼琴音樂創作中的民族化藝術思維和手法進行解析。
在這里所提及的五聲縱合性和弦,是指把民族五聲調式旋律中的各音階縱向結合到柱式和弦當中而構成的民族化和弦形態。因其將原本橫向散布于五聲調式旋律中的各音,轉變為在西洋音樂典型的疊置柱式和弦當中的縱向結合,故稱為五聲縱合性和弦。從這個定義來看,五聲縱合性和弦體現了中國傳統音樂藝術思維對西方和聲技法的融合與變通,其本身就足以體現中國鋼琴作品“中西合璧”的民族化創作特征。
在鋼琴改編曲《梅花三弄》當中,王建中就運用了多樣化的五聲縱合性和弦來表現特定的音樂情韻和意境。比如在該曲的第49小節處,作曲家分別在右手部分和左手部分安排了一個建立在F宮上的“宮——商——角”和弦轉位形式“商——角——宮”。這無疑是將五聲調式旋律中的宮、商、角三音縱合于一個疊置柱式和弦當中,因此屬于五聲縱合性和弦。而上述這兩個“商——角——宮”和弦又分別同空五度和弦“宮——徵”構成了復合結構和弦。“宮——徵”實際上是大三和弦“do—mi—sol”去掉三音的形式,屬于民族五聲性和弦當中的“省略音和弦”。這樣,省略三音之后所得的“宮——徵”和聲音程為純五度,其和聲效果已大大弱化而使其音效變得有些空洞,容易表現幽遠的情調氛圍,因而稱為空五度和弦。而在這里,兩個空五度和弦與“商——角——宮”構成復合結構和弦,其所包含的純五度、大二度、小七度、小六度等極協和音程、不協和音程與不完全協和音程相互交織,營造了既有些尖銳又不乏幽深之感的音響效果。這就非常形象地刻畫了寒梅所處冬夜既嚴酷凜冽又蕭疏曠遠的環境特征,也對本樂段所模擬的《梅花三弄》原笛曲“二弄穿云、聲入云中”的主題構成了生動的呼應。
從上面這個案例不難看出,五聲縱合性和弦本就是中西音樂思維和寫作技法交融“合璧”的產物。若能在鋼琴樂曲中得到恰當的運用,就容易轉化成具有“點睛”作用的神來之筆,幫助樂曲營造出理想的氛圍和意境,從而傳達出典型的東方音樂意境之美感。
(三)但昭義鋼琴作品民族化創作技法
與前述的儲望華、王建中兩位作曲家不同,但昭義首先是以鋼琴教育導師的身份而聞名于世的。在絳帳傳薪之余,但昭義也以較高的熱情投入到了中國風格鋼琴音樂的創作領域。幾十年來相繼推出《思戀》《箏印象》《蜀宮夜宴》《苗家新歌》《放牛娃兒盼紅軍》等一批民族風格鋼琴曲目,受到了音樂學界和鋼琴學習者的高度重視。
由于長期從事鋼琴教學工作,但昭義更注重采取一些適于展示技巧性的特殊技法來表現民族化的音樂思維。比如在鋼琴改編曲《思戀》第23至25小節之間,作曲家采用了“三對四”“二對三”“五對四”等復雜的復節奏形式,客觀上要求通過在時間上交錯演奏不同節奏型來表達濃烈、飽滿、激越的情緒。從譜面上來看,規模龐大而又復雜交錯的復節奏形式乍一看去仿佛是高難度的節奏型練習曲,似乎從中看不出來一點兒民族音樂技法的痕跡。然而,如果上升到音樂思維層面就會發現,作曲家采用一系列規模龐大交錯的復節奏,實則暗合于類似我國傳統戲曲中“散板”板式的自由式節奏思維,實現了“有法”和“無法”的統一。從這個意義上說,作曲家實際上是以我國傳統的散板板式所表現的藝術精神為指導,采取了西洋音樂的復節奏技法來創作《思戀》第23至25小節之間的織體片段的。這就體現了西洋音樂創作技法與民族音樂藝術思維之間的有機融合,堪稱為民族風格鋼琴曲創作領域實現“中體西用”的典型案例。
當然,除了上述這種民族音樂思維與西洋音樂技法融為一體的案例之外,但昭義鋼琴作品中也不乏民族音樂創作手法與西洋音樂技法相交融的其它案例。比如他創作的兒童鋼琴曲《放牛娃兒盼紅軍》在曲式結構和調性布局方面就表現出了創作技法中西合璧的特點。《放牛娃兒盼紅軍》采用了西洋鋼琴曲常見的變奏曲式結構全篇。在樂曲開始處呈現主題之后,接下來作者相繼展開了七段對于樂曲主題的變奏段落,最后終結于一個包含十四小節的尾聲樂段上。然而,在上述的變奏曲式結構當中,作曲家又隨著樂曲變奏的展開過程而不斷推動民族調式的轉換。具體來說,樂曲主題和變奏一、二采用C宮的A羽調式;變奏三轉換為降E宮的C羽調式;變奏四進一步變為降E宮的G角調式;變奏五轉換為B宮的G角調式;變奏六又變為F宮的D羽調式;最后,變奏七和尾聲又回復為C宮的A羽調式,與主題和變奏一、二形成了首尾呼應。從中可見,在《放牛娃兒盼紅軍》中,作曲家將西洋音樂變奏曲式與民族調式轉換有機結合融為一體,從而有效強化了這首作品的民族音樂情韻特征。
通過上文對但昭義中國風格鋼琴曲目中兩個創作案例的解析不難看出,采取中國傳統音樂思維來指導西洋音樂寫作手法的運用,最終促成中西音樂創作思維和具體技法的水乳交融,正是對中國風格鋼琴作品“中西合璧”創作特征的生動詮釋。
結 語
綜上所述可見,中國風格鋼琴作品之所以能夠表現出鮮明、濃郁的“中國風格”,從本質上來說還在于它們實現了中國傳統民族音樂的藝術思維、寫作手法、音樂元素與西洋鋼琴音樂創作思維和技法體系的有機對接與水乳交融,從而營造出了既植根于西洋音樂技法體系、又洋溢出鮮明的中國民族音樂情韻美感的鋼琴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西合璧”不僅足以全面概括中國風格鋼琴作品民族化的內涵與審美表現特征,而且也從“取精用弘”的角度為當代中國鋼琴音樂的進一步創新發展指出了正確的范式和道路。因此,進一步明確中國鋼琴作品“中西合璧”的內涵與民族化特征,對于今天中國鋼琴作品的進一步深入創新發展也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