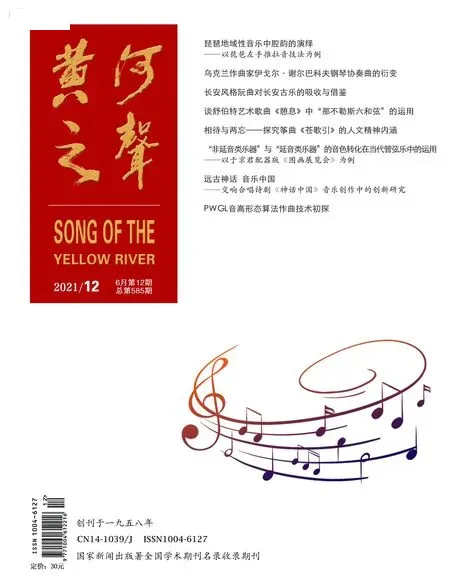淺析瞿曇寺“花兒”語言特點
李 彤
引 言
瞿曇寺花兒會是青海省花兒會中影響較大的一出場所,演唱的花兒以河湟花兒為主。瞿曇寺所在的樂都區作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文化背景。瞿曇寺花兒會正是在這種多元文化的影響之下產生并不斷發展的。
一、瞿曇寺“花兒”的生成語境
(一)自然環境
瞿曇寺所在的樂都區地處于青海省的東北部地區東與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毗連,西與海東市平安區相鄰,向南以化隆縣以青沙山為界,北面與互助縣隔河相望。全區總面積為3.5平方公里,人口約為36萬,共有東鄉、藏、土、漢、回等15個民族。
獨特的地理環境孕育了不同的人文環境,瞿曇寺花兒在此基礎上又不斷地吸收著當地各種獨特的民俗文化,最終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可以說,地域文化是促進瞿曇寺花兒扎根、發展的內在動力。
瞿曇寺寺廟地處環境十分優越,背靠著羅漢山,左邊是廟頂子山,右邊為臥虎山、與鳳凰山則隔河相望,可謂稱得上是一處環境雄渾而有清幽的風水形勝之地。
人類的生活依附于大自然,不同的地勢地貌、氣候變換對于人類的文明產生來說都是有著重要影響的,反之,它也必然會體現在人類的文化作品之中。“花兒”作為表達人們思想、情感的民歌,它的產生與發展與這些外在因素是密不可分的,而這些外在因素又不斷地波及人類內心的情感情緒,這也使得這三者之間的關系變得密不可分。
(二)文化語境
1、多民族文化格局
漢代以來,不少民族不斷地遷入樂都,隨著越來越多的民族的遷入,樂都成為了一個多民族聚居區,它的存在不但促進了各民族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的交融,更是形成了以漢族文化為主,其他民族文化為輔的河湟多元文化,花兒會也便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的,它成為了連接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認同的橋梁和紐帶。
樂都區作為一個典型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宗教信仰、語言、風俗等各種差異是花兒曲令風格形成的根本原因。根據樂都區的民族分布來看,花兒則是在漢、藏兩大民族文化體系下夾生出來的文化。
各民族創作本民族花兒時不光會借鑒其他民族的文化特點,也會融入自己的民族音樂文化特色在花兒歌曲中,在其展示的時候也會加入當地的民俗活動等有趣的內容。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如今各民族共享的花兒文化,而各族群對文化的相互借鑒也使得花兒能夠扎根民間,源遠流長。
2、瞿曇寺簡介
瞿曇寺,藏語稱之為“卓倉多杰羌”,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是明朝建立的規模最大的皇家寺院。瞿曇寺的建筑形式主要以漢式為主,但內部陳設、供奉確是藏式。瞿曇寺的建設因與北京故宮相似所以也被稱當地人之為“小故宮”。
起初,明朝建立瞿曇寺是想要通過這一宗教活動中心,籠絡地方的宗教領袖,從而強化對河湟流域一帶的進一步統治,從而樹立天朝的權力地位與威嚴,但是隨著時間流逝,朝代更迭,清代之后瞿曇寺的地位日漸沒落。但是這并沒有影響當地人民前去祈福、朝拜,直到如今依然可以經常看到當地民眾去寺廟還愿、膜拜。瞿曇寺花兒之所以有很大的知名度,與瞿曇寺的悠久歷史和當地民眾對藏傳佛教的膜拜是分不開的。
3、瞿曇寺的民俗文化
樂都區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當地的生產環境也還以半牧半農為主,這就造成當地的經濟發展較為的緩慢,但是也帶來一個好處,那就是使得當地的一些民俗傳統文化得以保留與傳承。例如至今當地仍然保留著誕生禮、婚禮、葬禮等一些節日上的規矩習俗。因為樂都區所容納的民族較多,所以各民族之間通婚的較為常見,它們在保留了本民族習俗的基礎上又兼容其他民族的習俗,求同存異、特色鮮明。在信仰方面各民族之間也秉承著兼容并蓄的理念。在如此背景下產生的瞿曇寺花兒就不僅僅是抒發人們內心情感的民間文化,它更像是各民族人們友好相處的紐帶、橋梁。它潛移默化地促進著當地人民之間的感情,極大的創造、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不斷地發揮著民間傳統文化的實用功能。
二、瞿曇寺“花兒”的唱詞分類
“花兒”多數表達的是男女愛情,是回、漢、撒拉、土族等多民族表達情愛的獨特方式。它以自己的獨特的韻味描繪出土生土長的西北人的生活風俗,記錄著養育當地人民的黃土高原,表達著西北人民豪邁灑脫的豁達情感,因此也就形成了它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唱詞。
(一)情歌
在眾多的花兒歌曲中,描寫愛情主題的“花兒”依舊是主線,是最吸引人、最打動人、也是最容易引起共鳴的一個題材。描寫愛情的花兒曲目有很多,描寫了兩個人從相識、相知、再到相愛、婚戀的全過程,深受人們的喜愛。
阿哥是天上的白龍馬,脫韁著下凡來了;
尕妹是騎手著愛駿馬,因此上我愛上你了。
(二)勞動歌
勞動作為生活的一部分,它也是創作的來源。西北地區因為地處的環境較為惡劣,所以人們的勞動生活也變得困難,工作的強度也很大,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人們創作出了一首首花兒,用以“鼓舞士氣”。例如:
手拿上鐮刀者割麻柳,麻柳倆編了個背斗;
唱少年不光是維連手,高興上提者個興頭。
(三)頌歌
隨著國家政策優惠越來越好,當地人民的生活也在國家政府的幫助下過的越來越豐富多彩,精神文化上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進而產生了一大批贊頌國家,贊頌黨英明領導人民的花兒歌曲。例如:
花花的鳥兒綠翅膀,它落在花椒的樹上;
毛主席好比紅太陽,照亮了全國的地方。
(四)本子歌
本子歌是指一部完整地、連貫故事。一般以歷史故事居多,但也不乏有很多的愛情故事、神話故事、民間故事,內容十分的精彩有趣,一般是歌手在花兒會上拿來比賽的歌曲。例如《白蛇傳》、《西游記》、《三國演義》、《八仙》等等。
三、瞿曇寺“花兒”中的詞匯特征
(一)“風攪雪”
1、詞匯方面:借詞應用
“風攪雪”是少數民族在用漢語演唱“花兒”歌曲的時候結合自己本民族的語言、語調的特點融入了一些準確、有趣的本民族詞匯和音調,這種形式的“花兒”使得各民族之間的變得更加親密無間。例如:
抓下的麻雀兒飛掉了。老鴉峽里下了;
朵羅(哈)搖成個法拉了,尕刀子心上系上了撣。
此首“花兒”第三句中的“朵羅”是蒙古語中的“頭”的意思;“法拉”,蒙古語,指的是專職做迷信活動的巫師在通神之后則會渾身顫抖、搖晃,不停的講話,但一般旁人都聽不懂,以示陳述神靈的想法與要求,結束后巫師一般不清楚自己剛剛所說過的神靈的指示。
2、語法方面:改變句法結構
受到當地方言的影響,“花兒”歌詞上的創作也區別于其他地區。例如,我們正常的漢語語序為主、謂、賓結構,而青海方言中的語序結構則為主、賓、謂,尤其是在青海方言中藏語的主、賓、謂語法結構更為根深蒂固,使得當地的“花兒”句法結構無法改變,反之這也成就了青海“花兒”不同于其他“花兒”的一大特色。例如:
七寸的碟子里拾饃饃,菊花的碗里茶倒;
饃饃不吃茶不喝,你把你心里的話說。
“茶倒”、“話說”正常應該為動、賓結構的“倒茶”、“說話”,可這里卻受方言的影響變成了賓、動的句式結構,不過這樣的句式結構也使得各民族語言之間的交流更為方便,各民族人民之間也更為的親密友善。
(二)網絡詞匯和外語在“花兒”中的應用
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和互聯網的普及,“花兒”的用詞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突破與創新,如唱詞中出現了常用的英文“Bye”“Ok”等等,還有網絡用語例如“網站”“發帖”等詞匯。例如:
白天晚夕地泡網站,為聽個歌花兒和少年;
這個網站是鬧稀罕,花兒是聽給著舒坦。
(三)襯詞的運用
在“花兒”的唱詞之中增加了很多的襯詞。如我們常見的“呀”、“哎”、“喲”、“啊就”、“么就”等詞。襯詞在絕大部分都只是一個語氣虛詞,沒有什么實際的意義,但是在“花兒”的演義中,這些襯詞則像是一則調味劑,演唱者通過自己對歌曲的理解演唱襯詞,讓原有的歌曲更加靈活生動。可以說這些襯詞是“花兒”歌曲的點睛之筆。
1、句首呼喚性襯詞
“花兒”歌曲的一開頭就用到的襯詞如“哎”,一般情況下這些開頭的襯詞音調都較為高亢,演唱者根據不同的歌曲情景演繹著不同的情緒。例如《山丹花》
2、句中的襯詞
瞿曇寺花兒的語言中有著很多西北地區特有的方言中的襯詞,例如“啊就”、“么就”等詞,加上旋律之后,當地的鄉土特色更加呼之欲出。例如《白牡丹白者嬈人了哩》。
3、句尾的襯詞
句尾的襯詞一般是對樂句的不斷擴充,使得曲中的形象更加豐富飽滿,蘊含的力量是不容輕視的。例如《水紅花令》
(四)虛詞結構
“花兒”中虛詞的使用是十分常見的,但其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視的,正因為有了這些虛詞的出現和運用,不僅使得我們的“花兒”更加具有濃厚當地特色,還推動了整首歌曲的感情走向,顯得歌曲變得輕松、風趣,而且視覺上也讓我么的唱詞更加的工整,這些虛詞一般都出現在句尾。想要更好地去體會“花兒”中的韻味就必須去理解它的虛詞,下面我對常用幾個的虛詞做一些解釋:
“請給我拿一瓶維生素C。”柜員手腳麻利地從上層拿了一瓶酷似“成長快樂”的花罐子擺在我面前。“這是純天然提取的,果味的維生素C咀嚼片,一天嚼六粒,這瓶68……”
1、“了”字的運用
打馬的鞭子哈閃折(了),走馬的腳步兒亂(了);
妹妹不像個從前(了),如今的心思兒變了(了)。
當“了”字出現在句尾時一般表示的是動作的完成與終結。
2、“哩”字的運用
這一朵云彩里有雨(哩),地下的青草們長(哩);
睡夢里夢見哈還想(哩),清眼淚不由的淌里(哩)。
“哩”字一般出現在句尾,是表示感嘆的一種語氣詞,并沒有特別的實際意義。
3、“兒”字的運用
大石頭根里的石榴(兒),白牡丹根里的兔(兒);
心肝花想成了三綹(兒),路遠者沒聽上信(兒)。
“兒”字也是出現在句尾偏多,是北方的一種特有的兒化音,也無特別的實際意義。
4、“來”字的運用
麥子里拔了個豆兒里(來),手巾里包了個肉(來);
大門里嫑來了房上倆(來),尕妹的熱懷里溜(來)。
“來”字常出現在句尾,意為“來到”,讓除自己之外的人、物過來。
四、瞿曇寺“花兒”唱詞中的韻腳特點
(一)通韻
通韻是指句句押韻,句句在韻。除了與一般通韻相同之外青海瞿曇寺花兒的通韻還有其自己的特點,例如句尾的韻腳采用同一個字。例如:
宋江投奔大到滄州了,城門上掛了個刀了;
阿哥想你著心碎了,越碎和越想頭大了!
(二)交韻
交韻是指一、三句用用一個韻腳,二、四句用用一個韻腳。交錯押韻,也是花兒押韻的典型之一。例如
上去個高山了射一箭,箭落著莊子里了;
把我的尕妹妹見一面,心放到腔子里了。
(三)隨韻
隨韻的押韻較為自由,一般是指一、二句為同一韻腳,三、四句可以變化韻腳,例如:
天下的黃河往南淌,水大著淹了個享堂;
遠路上有我的好心腸,看去是沒有個落腳的地方!
五、瞿曇寺“花兒”唱詞中的基本修辭手法
我國古代的詩論中,把賦、比、興三個字概括為詩創作的三種表現手法。所謂賦,就是寫實,平鋪直敘,直言其事;所謂比,就是比喻,比擬;所謂興,就是開頭先寫別的事物。
(一)賦
賦,即“直接”,直接陳述、直抒胸臆。“花兒”中的賦是指那些極力鋪排、描寫細致、反復詠唱的語言處理方式。例如:
三股子麻繩背扎下,大堂的金柱上綁下;
鋼刀拿來頭割下,不死了就這個鬧法。
短短四句,就將一個癡情男子的形象描寫的鮮活動人,感情表達非常強烈。
(二)比
明喻。也就是打比方。在“花兒”中運用的較多,通常以明喻、暗喻、對偶、對稱等防方式演繹出來,直接、形象。例如:
阿哥好像路邊的草,越活時越孽障了;
尕妹好像清泉的水,越活時越清亮了。
運用比喻和對比的手法將歌者阿哥和戀人尕妹的精神面貌形成對比,修辭上也主要采用了比喻。
(三)興
作為藝術手法,主要用來渲染氣氛,觸景生情,往往表達的是“由xx想到了xx”。在花兒中大量的運用到了“興”這種修辭方法,可見“花兒”在體現民眾生活與藝術之間的聯系上承擔了重要作用。例如:
天邊里的紅云彩,這個妹妹好人才,
俊的好像牡丹開。
此曲表達出了對女性的贊美,用紅云彩來襯托出女性。
作為一種歷史悠久、有明顯地域性、音樂風格獨特的曲歌,“花兒”隨著時代的發展,它也終將會不斷的向前進吧,使得自己變得更具魅力、更具生命力。但是方言的退化、視覺審美的改變等眾多緣由也使這一傳統的民歌在語言、演唱、創作等方面迎來了巨大的考驗,我們既不能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來哀嘆“無可奈何花落去”,也不能一味的在“弘揚民族音樂文化”的大旗下止步不前,而應該拿出“刀刀拿來頭割下,不死時就這個唱法”的魄力與動力,讓“花兒”文化不斷地創新發展,讓更多的人想要去了解、想要去學習。■